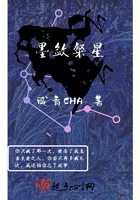夏格格带着有毒的笑容,等待着,低垂着头,长发披散在脸上。
汪雪穿着超市的制服,头发还湿湿地搭在额前。雨水密密地轻落在伞上,她站在夏格格家门口,房门大开着,整座楼黑乎乎一片,看不到一点光。
“夏格格!”她叫一声,没有回答。
她的心格登一下,收好伞,她小心地拿着东西走进屋子,伸手去按开关,灯没亮。但是在楼梯的顶端,她隐隐看到一丝光,好象是刚刚才亮的。她抬脚走上楼梯,那光开始移动了,当她走到二楼时,那光便消失在夏格格的房间里。
“夏格格!”她再叫,还是没有回答。
光却在屋里忽闪了一下。
她站在房间门口,伸手去按开关,灯还是没亮。但她知道屋里坐着个人,背对着她,低垂着头。
“格格,我看见你了。”她说。
那个身影慢慢转过身来,机械的,一点一点地转动。当她完全面对她的时候,她一下呆住了――她又看到了那些草!在她的嘴里,还有鼻子耳朵里,有许许多多的草从里面长出来,触角一般的叶子柔软地伏在她脸上,然后不断地长长向脑后延伸,再从另一边绕回来。它们灵活地缠绕在一起,如同给她下半个脸戴上了有生命的面具,并且缓缓挤压着,又象是在咀嚼。而在这个面具的上面,她看到了一张苍白如雪的脸,两个黑洞一样的眼睛,无神地瞪着。就在这时,“嚓”的一声,她身后的电视机突然亮了,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她看到一张鬼脸猛然出现在屏幕上,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唇边流着血。屋子里一下亮了很多。
“啊!”汪雪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伞和烟都掉到地上。
“嘿嘿嘿嘿……”夏格格剪影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得意地笑了,“好玩吗?”她问。
“啪”的一声,她打燃了手里的火机,然后又熄灭。火苗照一下她的脸,苍白如雪,但是那些草却不见了。在她的身边,散落着好几个大小规格不同的灯泡,她拿起其中一个把玩着。
“帮我把它们装上吧。”她散漫地说。
汪雪没有说话,慢慢走上前蹲下身子跪到她旁边,伸手到她脸上摸了一下,只有还没干透的面膜。屏幕依然定格在那张鬼脸上,痴呆地张着嘴。
“怎么没有了?”她轻声说。
“什么?”夏格格一阵茫然。
“那些草。”她依然盯着她的脸。
“你在说什么?”她完全愣住了。
“我刚才看见你嘴里长了草,以前我在王伯儿子的耳朵里也看见过。”
“什么意思?”夏格格只感到一阵寒气侵上心头。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汪雪说,“能把电视关上让我再看一下吗?”
“你想干什么?”她紧张起来。
“只是想再看一下,只有在黑暗里我才能看到这种东西。”
夏格格没有动,过会儿突然不住地冷笑起来,“汪雪,你以为我会怕吗?”
“是我怕。”汪雪站起身认真的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夏格格瞪圆了一双眼,面膜敷在脸上使她苍白得如同一个鬼。突然,她大笑起来,而且无法止住似地越笑越厉害,肩膀剧烈颤抖着,人渐渐缩成一团。过了很久,她终于不笑了,声音突然变得极冷,“你想吓我,没门!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很过瘾,我已经很久没有象今天这么刺激了。谢谢你啊好同学,我已经知道该怎么玩这场游戏了。”
汪雪没说话,到门口捡起那条烟递到她面前,夏格格没接,只是仰头看着她。
从她家出来时,她站在门口往二楼看了很久。重新撑起伞,腋下夹着那条烟,她知道客人拒绝付钱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她心里想的,却是那些诡异的草。夏格格的房间依然只有电视亮着,她面对电视坐着,一直盯着屏幕上那个凝固的鬼脸,一支烟在她手指上燃烧着,如同一星鬼火。
杨阿姨终于旅游回来了,何涛然立刻去医院找她。
从科室出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依然迷惑不解。因为按照她的分析,他应该和夏格格之间有过约定,只是被他刻意遗忘了,后来因为某种刺激才从梦里表现出来。这是一种逃避行为,叫作选择性遗忘。和夏格格在一起时他会忘记柳叶,而和柳叶在一起时他又会忘记夏格格。她说得很委婉,但还是听得出来责备之意,而且为了唤起他的记忆,她建议他再做几次暗示治疗。
他心里乱极了,原来分析来分析去好象是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是夏格格,当这些怪事一经解释变得不再神秘时,他却陷入了新的烦恼。这个结论,他无法对柳叶说,而且他还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跟夏格格有过约定,约定内容又这么荒唐,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同时让他奇怪的是,那个饮品店的女孩为什么也说看到自己差点被车子撞上呢,这是他在梦里的经历啊,难道也是有其事而在梦里反应出来的吗?这样说来,自己的问题岂不是很大?明明是一个人去的饮品店,却以为是和夏格格一起,还叫了两份饮料。
他感到一种没由来的沮丧,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他就不会来了。既然想不起来,他也不想想了,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而且虽说杨阿姨是很出色的心理医生,也会有误诊的时候吧。想到这里,他觉得心里轻松了一些。但是夏格格前两天晚上打来的电话又让他不安,听口气不象是开玩笑,因此这两天在学校见到她虽然还是那样笑着,却让他怎么看怎么不正常。怎么办怎么办,当自己迫于无奈接受她爸爸关于那个约定的请求吗,他摇摇头,他做不出来。那么就只有让自己想起来?他抬头看看天,还是决定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不管是那个约定,还是来找过杨阿姨。
出杨阿姨办公室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进去,也没预约就进了里间,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总算出了趟长差回来,李俊找了个时间真奔附属一院心理门诊而来,今天是杨严君大夫坐诊,正是他要找的人。如果不是这趟差耽误了,他早就来找她了。上次汪雪在电话里说到魄,而且还拿了个黑瓶子出来告诉他里面有魄的阴气,是它借用那个叫柳叶的同学的名字出来后留下的痕迹。看到她那么认真的神情,他突然有种要把这件事探究下去的想法。在他眼里这个奇怪的孩子一直以两种形象交替存在着,病人或者通灵者。他需要一个科学专业的解释。从档案里查到,从四年前开始她就一直由这个叫杨严君的大夫治疗,一年后成功控制住病情,近年来没有复发,只在进了高中后,才再次出现症状。现在杨大夫就坐在他对面,把汪雪四年前的病历记录递到他手里,因为他是警察,事情就好办多了。
“应该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心理问题,她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叫‘幻觉妄想综合症’,而且是以少见的幻视为主。如果症状再严重复杂一点,可以诊断成‘精神分裂症’,但她的发病年龄太早了,她爸爸第一次带她来的时候,我很吃惊。”杨大夫说。
“幻觉妄想综合症是怎么回事?”李俊边翻记录边问。
杨大夫笑了一下,“‘幻觉妄想综合症’简单地说就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并伴发与其相关联的妄想及恐惧焦虑的情绪反应。其实这些东西或者声音气味触觉味觉等都是他主观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就象汪雪,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个通灵的人,能看到刚死的人的灵魂,到了夜晚,世界在她眼里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她常常觉得受到这些东西困扰,有时很痛苦,会焦虑不安。”
“但她看起来很正常,学习成绩也很好。”
“是的,这也是我一直没把她诊断成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之一。除了有相信她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是真的之外,其它方面还是跟正常人一样,不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思维正常,思路也很清晰。”
“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总能出现在凶杀或交通事故现场,并且准确无误地指证出凶手呢?”
“以前我也有你一样的疑惑,后来仔细看了案件资料,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凶案,都发生在晚上,而且有记录的两起凶案均发生在室外。而她有夜游的习惯,总是偏执地出现在一些街口或巷口,如果那里出现凶杀或交通事故,有被她碰见的机率肯定会升高。如果整个过程都被她目击了,指证凶手应该不是难事。但说实话,这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李俊点点头,“去年她的病又复发了,您知道吗?”
“我有知道,从给她治疗开始我就一直在对她进行跟踪观察,她爸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这里来住的,没想到还是复发了。”杨大夫起身去找病历,“记得是去年市二中的车棚凶杀案,当时还是她报的案。但事情发生后我只对她进行过一次治疗,以后她就再也没来过了。对,只有一次,是去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杨大夫把找到的病历翻开来递到他手里。
果然,病历上只有那一天的治疗记录。李俊猛然记起,就是那一天晚上实验室发生了那起离奇的失窃案。
“那后来她为什么没来治疗呢?”
“不知道,以前都是她爸爸主动带她来的,我无法联系到他们。”
“对了,我听汪雪的爸爸说你给汪雪的治疗是免费的。”
杨大夫微笑了,“其实开始时还是有收费的,只是后来才免了。主要是他家太穷了,再说象汪雪这样的病例很少见。”
李俊点点头,一边道谢一边把病历还给她。进门时就看到她桌上有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现在不免恭维一句道:“杨大夫,照片上的人是您女儿吧,又漂亮又有气质,一定很像您年轻时的样子。”
“哪里有,可比我漂亮!”杨大夫拿起相框,深情又慈爱地凝视着,照片上的女孩有着和妈妈一样温婉的浅笑。
有病人进来了,李俊不便再打扰她,起身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