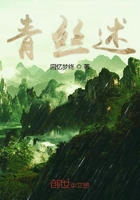“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齐王一扬稠质宽袖于身侧,朝后仰靠于狐绒软枕上,半是慵懒半是疲倦后的闲逸,那轻薄而顺滑的衣料像浸湿了水便吸贴合着他阳刚俊美的身躯,不用故作**,便有有种雄性荷尔蒙散发最原始的诱惑感。
陈白起暗叹,也难怪这群宫姝面对她时如此春心荡漾。
她撩袍跽坐,与齐王面对面,她详细地讲了一遍五氲玉的来历,又道:“此玉有蛊惑人心之力,狄国被灭,历经三届,虽非全部之因,却也皆由它所控之故。”
一听此话,齐王眸光一下便冷冽下来,他挺直身子。
“何人如此歹毒用心!”
陈白起摇头,只道:“此事只怕不简单,焕仙打算利用那商人白起顺藤摸瓜将幕后之人寻出,此事倒是得多费些周折,此事若交由别人办到底不放心,唯有亲自出马。”
“你认为还有幕后之人?”齐王偏过头,挥手让大监送上一桶燕酒与一鼎炙烤后炖烂的红肉。
陈白起眸转深意,嘴角含笑道:“若那人为主谋又何必冒险亲自出马,再者这五氲玉如此神奇只怕得来不易,凭他一介商人如何运转得走这盘大棋?”
齐王闻言挑了下眉,深以为然。
大监这时托着一个祥云铜盘过来,跪于案前将盘中东西一一摆好,当他揭开鼎盖盛红肉时,陈白起伸手道:“由我来吧。”
大监愕然抬头,见陈白起朝着他温和友善地微笑着,便又犹豫地看了一眼齐王,见齐王心情甚好地朝他颔首,大监方露出腼腆的笑,道:“那便有劳大谏大人了,奴告退。”
这名大监是新最提拔上来暂代,乃前一任大监的义子,年岁不大,摸约二十来岁,平日行事稳重老成,话不多却十分懂得省时度事,因此年纪轻轻便能伺候君王。
但今日他行事却谨慎胆颤,老实说他十分惧怕单独应对行事阴晴不定的齐王,但当大谏大人来时,他却又觉他所认识的那个“齐王”其实是假的,真实的他其实是一个正直又贤明的君主。
这样两面矛盾又奇怪的现象令大监不解,但他的内心却清晰地了解一件事情,那便是朝中上下讲陈大人深得君心一事的确名符其实。
等人走后,陈白起问:“此人用得如何?”
齐王田文随意道:“不过如此,比不得陈卿啊。”
他说完,便又拿眼神钩着她,像是玩笑又像是试探。
陈白起不觉其意,只当他在调侃自己,笑着摇头,她拈起一根细长弯曲的银勺从小木桶内取酒,如一柱银丝浇入铜爵之中,又从鼎中盛起方肉奉于齐王的面前。
“早膳乃一日最重要的一餐,主公切勿忽略,请食。”
齐王见她举止优美流畅,全神贯注地替他铺食时,那神态动作如度蒙了一层神圣的光泽,似山遥水远遗墨间,彼岸花开般令人心醉。
齐王凝注得有几分入神。
他见她抬眸,鸦羽般的睫毛栩栩如生,她的眼神、嘴唇、指尖,如同水中笔触缓缓地盛开,在他的视野中凝固成形,那样活色生香。
陈白起见他一直盯着她瞧,目不转睛,那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但又并非令人讨厌的锋利,便不由得轻唤了声:“主公?”
齐王听到她的声音,瞳仁一窒,顿时有几分狼狈地清醒了过来。
他抄手举爵仰头一口饮尽,然后没什么技巧地转移着话题:“听说你府中的姜大与姬铭准备出城?”
“姜大”是姒姜的化名,而“姬铭”则是姒韫的化名,因为两人在楚国还算有知名度,自然不可用原名。
陈白起听齐王提起两人的行踪倒也不奇怪,她知道田文虽信任她,可为君者不可能不对底下的朝廷重臣布下眼线,即便他不想知道的事情,亦有人会如实汇报上去的。
陈白起道:“此事焕仙正要禀报,焕仙遣他们出城是为焕仙去办些私事……”
她还没讲完,齐王便颦眉打断了她:“孤并非那意思……你身边离了这一文一武,那便暂让魏腌为你护卫吧。”
陈白起一怔,杏眸睁得有几分圆溜溜地,倒显几分憨呆可爱。(齐王视觉)
他弯起嘴角,道:“你身边总归需要留一个能保护你的人,你与魏腌关系不错,便暂让他住在你府中替你护院罢。”
陈白起见齐王是认真的,便“噗嗤”一笑:“主公让一个大将军来替焕仙护院看家着实太大材小用了。”
“反正他近来无事可做,若是为护你,孤相信他定是乐意的。”齐王抚爵轻笑道。
陈白起这时想起一事,便道:“正巧苏丞相近来也打算来我府上借住一段时日,若魏腌来了,倒也热闹。”
齐王玩似抚爵身凹凸的指尖一顿,抬眸,笑意加深古怪道:“你说……苏放要住你府上?”
陈白起一时不解他眼底的笑中深意,含词半句,只道:“是。”
“哦……”他意味不明地拖长一声,便举玉著夹了块红肉于口中,漫不经心道:“孤近来常觉朝政晦涩疲倦,夜亦难眠,与焕仙谈话总觉能宽郁心舒些,不如……今夜你便歇在宫中,与孤好好夜话长谈一番。”
陈白起脸上的笑意一滞,略诧异地看向齐王,他的这个要求对她可谓是有几分为难了,她捂嘴迟疑道:“可焕仙幼弟在家……”
齐王忽然撑案凑近她几分,笑得有几分危险道:“不过一夜,你便要拒绝孤?那苏放住你家中可不见你有何意思。”
这话听着总觉哪里不对劲,陈白起抬眼看他,见他随意而流转加深泛紫的眸子威盛逼近,其态度明显已不容拒绝。
这便是为君者吧,君无戏言。
他都这样讲了,陈白起自不能不识抬举。
“喏。”
齐王这才笑意盈盈地仰身坐回原位,他垂眸盯着盘中剩下的一块红肉,眼神一黯,然后故作随意将盘推至陈白起的面前:“此肉炖烂得恰到好处,你用一口试试。”
他将玉著亦一并递予她。
陈白起见他将用过的盘、玉著交给她用,态度随意而自然,不似别有用心,或许在他眼中这是一种宠信的表现,可陈白起却有种难以下咽的感受。
“谢主公赏赐,可焕仙近来腹中纠涩,医嘱不可用太油腻之食方可调养将好……”她下意识地讲到一半,便顿了一下,似怕齐王因她的拒绝生气,她立即口风一转,便伸手接过其玉著,勉强笑道:“不过少食一块亦无大碍吧。”
可她没有拿到玉著,因为齐王将玉著收回了。
他望着她,似笑非笑道:“太狡猾了,你这样讲孤哪还敢逼迫你食肉啊。”
陈白起无辜地眨了一下眼睛,似不解他这话的含义。
因为今夜在留宿于宫中,陈白起便事先派人回府中讲明情况,姒姜与姬韫听说此事都脸色难看,而陈牧则默默地低下头。
——
天刚蒙蒙亮,陈白起便忽然睁开眼睛。
醒来后只觉腰酸背痛,太阳穴亦是一涨一涨地,她看见这陌生又奢华的环境时怔忡了半晌。
这并非是她的房中,她立即翻身而起。
却不想一条粗壮沉重的手臂将她给压住,另一条则搁在她腰间,她顿时表情十分魔幻地侧脸一看,只见一张鬼斧神工般俊脸近在咫尺。
他挨得很近,近得连皮肤上的毛孔与细白绒毛都看得清楚,轻薄的一层亵衣因豪迈的睡姿敞开了一大截,可观由胸至腰间的肌肤线条一览无余,他盖着一张薄被,墨色长发披枕,漆黑的睫毛笔直垂落,不似幼生动物柔软的翎毛,反似丰挺的翼羽。
她感觉到他的脉搏、心跳,连喷酒的温热呼吸,顿时尴尬又无奈地保持着僵直的姿势一动不动,十分头痛地开始回忆起昨夜的情形。
他们俩好似谈论政事至到很晚,并一直在喝酒助兴,还是最烈的那种酒,这一喝便是喝到半夜,所以她便醉熏熏地,完全忘记了为何她不曾睡在自己的卧榻上,反而怎么躺到了主公的睡榻之上……
即便是喝断片了,可如此荒唐之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陈白起完全想不起了,她颦着眉头,瞥眼看着齐王,见他仍旧熟睡着,便小心翼翼地挪开了他的两条手臂,然后慢慢坐起来。
这时她发现身上的衣服也是乱七八糟,外袍不见了,她抚额。
天啊,昨夜到底是喝了多少酒啊,应该没发生其它什么事情吧。
她将衣襟理了理,于是准备翻榻而过,却不料底下传来低沉又嘶哑的声音。
“爱卿,这么早是打算去哪儿呢?”
陈白起本就心虚,忽然听见说话声音,便脚底一打滑,险些从侧摔跌落地,所幸有人及时拉了她一把。
齐王将她重新拉回床榻之上,惺松的神色,支颐勾唇笑着。
“不再躺一会儿,今日沐休,并不用早朝。”
陈白起的心脏猛地跳动一下,她方才的慌乱只维持了一瞬,见已撞个正着,躲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她撑起身子,侧过头看着齐王。
今日必是晴空万里,从窗棂射入的阳光透过殿室内垂落的幕帘薄纱落在了他身上,他正对阳光,清澈动的人光线将他眉眼光虚化了一般,轮廓朦胧,袒胸露臂,结实而平滑的腹肌线条流畅完美,他躺在那儿便像希腊神话故事中俊美的神祗一般。
“主公……”
本书由潇湘书院首发,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