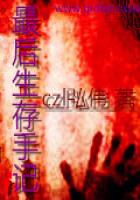微风阵阵,卷起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花瓣,倾洒到碧绿的池塘上,点点黄花游荡,空隙中映出一旁粗壮的古树,一只黑白相间的鸟安静的站在树梢,犀利的眼睛注视着院中那个小小人儿。
稚童学着大人的模样,反背了双手,一步一步踩上台阶,向长廊里面走过去。
咔嚓一声,屋门推开,稚童哼着小曲进来,熟门熟路走到藏在黑暗中的架子前面,一手握住架边,双脚踏在架子的底层,伸直了腰背,探手欲要去取上面的物件。
那物件似乎不在原处,稚童探了半晌,什么都没有寻到,略一生气,踢了一脚架子,却忘记自己正踩在架子上,身子失了平衡,往地上倒去。
稚童咬牙站起来,摸了摸摔痛的后背,欲要再试一次,脚上好像踩到了什么。
他捡起来,原来是一本书,撇撇嘴,没有兴趣,随手扔到一边。
刚要踩上架子,一边冒出的绿色光芒将他吸引了过去。
是那本书发出来的。
好奇心使然,稚童歪了歪脑袋,慢慢放下了脚,走向前去,只见那本书敞开着,一连串的文字从书里窜到空中,在暗中显得分外耀眼。
稚童长大了嘴巴,他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景象,霎时间,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促使着他将手伸了过去。
手刚探进到那束光中,耳边仿佛有无数的人声兽鸣,两眼所见,那些个文字不停变幻,最终幻化成一只怪兽,从光芒中伸出头来,低吼一声,将稚童撞到地上。
再一次躺在地上的他,眼瞧着一只硕大的兽脚朝着自己的胸口踩了过来。
没有痛,只有一丝微凉的舒适。
不知什么时辰了,不过从那略微开着的窗户看出去肯定是晚上。
司危用手揉了揉有些模糊的双眼,桌上摇曳着的一支火烛能让他勉强看清屋里。
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只记得闭眼前,小知了的手在澡盆里不停的旋转,留下一圈圈的水纹。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人搬到了床上,他坐起来,胸口好像没有那么痛了。
上身仍然是光着,但被缠了一条白布带,好像是将什么膏药绑敷在了胸前,清凉的感觉从伤口沁入身体里,向着各处气脉缓缓传去。
他闭眼晃了晃脑袋,感觉眼前满是绿色,充满生机的绿。
刚刚好像梦到了自己小时候,司危靠在床壁,回想起来,祖父的屋子里,那个架子边上,那一道绿光,那只怪兽。
地兽!
司危猛的睁开眼睛,他这才想起来,为什么之前梦里那只怪兽如此亲切,原来自己早就见过,在那本墨绿色书的封面上。
那个异兽的印记!
他记得早晨小知了闯进来的时候,自己应该是塞进了胸口的,那么现在去哪里了?
连忙从床上下来,点着了所有的烛台,屋里渐渐变的明亮,小知了不在,估计回屋休息去了。
到处看了一眼,目光聚焦到角落那张凳上,上面摆着一堆暗红色的破衣衫,原本应该是青白色的,只是如今沾满了血迹。
拎起衣服,果然底下有一本书,看来是小知了放在这里的。
这书沾了血,变成了黑黑的一本,早已看不清封面上的印记,中间破了一个剑洞,不知道里面如何,司危暗暗求天保佑。
看来老天不管这事,他坐在桌前,看着眼前翻开的书,撇嘴想到。
血将这书浸泡的彻底,不仅是书面上,里面除了红黑一片,再也看不到半个字。
司危望着那个黑漆漆的剑洞发呆,自己做的那两个梦,绝对不是无来由的,梦里的感觉太过真实。那个地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自称五千岁的童子,究竟是谁?
隐隐感觉这一切或许都和眼前的书有关联,答案应该就记载在这本书里,偏偏如今变成了这个模样,自己再想知道,也无从下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书本恢复原样,从而知道里面原来写了些什么呢?书应该是放在父亲那里的,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
还是算了,司危立刻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本来就是偷溜出来,父亲没过来将自己揪回去已经算好了,再说,如果被父亲知道梁福偷偷拿了这书,那小子也定要受罚的。
陷在沉思中的司危,没有感觉到门被打开,也没有感觉到有一个人站到了他的旁边。
“看来这药还真有点效果。”
司危被话惊醒,抬头看去,愕然道:“你是?”
那是个挎着个小箱子的中年男人,头顶纶巾,穿着一身素色宽袍,见司危问起,笑了一下,抱拳道:“我是尤尚书派来的郎中,叫我老孙好了。”
“尤尚书?”司危更加疑惑了,“那我的伤是你医的?”
孙郎中微微点头,坐在一旁,给了个手势,让司危将手抬到桌上,边搭脉边说道:“尤尚书知道你受了伤,便叫我到客栈来寻你,在楼下刚好碰到你在马上被一位姑娘牵来。”
闭眼感受了一下脉搏,继续道:“你这伤势,着实有些严重,流血太多,强烈的剑气又从胸口震向了全身的气脉,中途耽搁的太久,我只好先将你泡在药中,勉强治着试试。”
“那我现在?”司危知道,习武之人修孕内力,由丹田生出,如同一颗种子一般,逐渐的生根发芽,顺着血液充满全身的气脉。
心胸受损,气血不足,很容易造成枝芽枯萎,内力尽散。而自己胸口所中的那一剑,剑气震动,流血不止,损伤气脉,稍微晚些,就有可能丧命,即使不死,几乎也会变成一个废人。
自己醒来这么久,一直心思都在那本书上,也没有去注意自己身上的气脉状况,现在想来,隐隐担心,赶紧深呼一口气,就要运转内力。
“你若想成废人,就运转内力吧。”郎中已经搭好了脉,这会看到司危的模样,明白他想做什么,出口拦住他,“放心,显然你生命无虞,也没有变成废人。”
司危被郎中这句话一吓,差点追悔莫及,好在后面的话又让他稳定了情绪。
那郎中继续说道:“你现在没有瘫痪在床上,也多亏了尤尚书给的这药。”
司危听到这话,指了指自己胸口绑着的白布条,郎中点了点头。
“替我多谢尚书,自然,也要谢谢孙郎中。”
郎中摆了摆手:“我和尤尚书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了,才用这药试试看的,而且,只此一副,再也没有了,不过我刚刚探了你的情况,好在一副药已经够了,我再替你开些恢复的药方就好。”
“只有一副是什么意思,不能制了?”
“不能。”郎中摇头,“听说这是尤尚书的故人相赠,只有一副,曾经他也让我尝试过分辨其中的药材,试了许多年,其实分辨倒也不难,难就难在里面有些东西我没有见过。”
“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那有没有找其他人试过,或许别人知道呢。”司危犯着嘀咕,心想你不知道,不代表别人不知道啊,这药似乎疗效甚佳,虽然用在自己身上,但想到以后没有了,也不免有些可惜。
郎中哈哈一笑:“不是我自夸,我都没有见过的药材,这天底下就再也不会有人见过了。”
司危偷偷翻了白眼。
“不过,这药也只是疗伤的功效,若你气息没了,仙丹也没用,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居然能硬生生的将你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我有些好奇。”郎中斜坐在桌前,盯着司危看。
“怎么说?”
“其实,以你那时的情况,根本应该救不回来的,我想,你自己是习武之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内力尽散,气脉枯竭,却还能活着。”郎中笑了一声,感觉这事非常不可思议,“说实在的,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基本无望了,弄药泡着,只不过是医者心态。谁知等我再取药过来,却发现你浑身笼罩了一层生气来,好像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司危心里咯噔一下,他想到了梦里童子的那句话。
“你快死了,所以它带你来这里。”
莫非自己真的去了那个绿汪汪的山洞里,并不是梦,本来的自己是要去地府了,却因为被地兽带去了童子那里,才能够回来?
对了!小知了不是一直在自己身边吗?那自己又是什么时候去的,不会真是自己的魂魄吧,这事情也太邪乎了,司危不信这些,这是说不通的道理。
郎中不知道司危在想些什么,低头写了个方子,递过来道:“这药每日一副,吃满十日,应该能痊愈,不过这期间内,最好不要动用内力,你体内的气脉现在还是有些脆弱。”
“这怎么行?我还要去参加武会的,五年才有一次啊。”司危震惊于这个消息。
“那我没有办法,我是个郎中,不是神仙,不能立刻让你痊愈。”
郎中收拾好了他的东西,站起来笑道:“别想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是尤尚书让我转告你的。”
“对了,尤尚书接到圣上旨意,已经连夜赶回京城去了,他还让我转告你将来你若是去京城,一定要去找他。我明早也要回去,你如果不想变成废人,就不要动内力,那副药如今是彻底没了。”
丢下正因为明日武会懊恼的司危,郎中说完话便走了。
翻转了一夜,根本睡不好觉,越想越难受,直到外面传来鸟鸣声,一缕亮光透进了屋里。司危还是打定了主意,先去再说。
昨夜身体就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这会不去看那伤口,更是察觉不到异样,只是不能用内力,拳打脚踢总行吧。
可等他急匆匆赶到位于登陵城正中央的武场时,他才知道尤尚书那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也明白了为什么尤尚书这个因为登陵武会来的人,会在武会前一夜被召回京了。
武场四周都贴出了告示,因南边蛮国大将占旭屡屡屯兵边境,恐有不轨,圣上下了旨意,朝中大臣要随时在京待命,各州府官兵也要加紧戒备,以防奸细流入。
武会因各官员皆有要事,延后一月举行。
这蛮国不是每年都找个机会骚扰骚扰边境吗,而且以那种小国的兵力,镇南将军岂不是轻易收拾,需要如此大做文章?
司危想着,总感觉里面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对于自己倒是好事,一个月后,伤势早就好了,武会又能参加了。
心里美美的朝着客栈走去,一路上感觉城里的景色美不胜收,嘈杂的叫卖声也是如此悦耳。
但奇怪的事情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