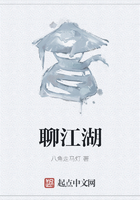进了镇子,陈车夫就带着他的马和车,和纪筠等人先行别过了。他要把自己的车赶去车马行市做个登记。
临走的时候,陈车夫还握住纪筠的手,一个劲儿的感叹。
“以后再有这样的车,我一定不跑了,一定不跑了,百来十文的钱,险些把命折在路上。”
纪筠听了,唯有苦笑。
当下,他、朱笃还有朱笃的叔父朱长安三个人,一起就向朱家的屠户铺子走过去。
朱家的屠宰铺子,前半截是店面,后半截就是朱家人住的里屋。虽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可能是因为杀猪太多,常年都有一股猪骚味。
朱笃进去的时候,他爹朱十三正光着膀子,大冬天的一身热汗,在一块黑黝黝的磨刀石上磨着一把寒光闪烁的锋利杀猪刀。
这一幕,吓得纪筠不知道为什么一阵恶寒。朱十三背对着三人,好似浑然没有察觉有人进了屋。直到朱笃带着哭腔叫了一声爹,朱十三的身体猛然一僵。
他霍地站起来,手里的杀猪刀呛啷一声,就这么掉在了地上。
朱十三慢慢回转头来,生怕听到的是幻觉,却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双目含泪站在门口,不是朱笃又是谁呢?
朱十三嚎叫了一声,哭着奔跑过来,一把就将朱笃抱进了他肌肉坚实的胸膛里。朱笃早就习惯他爹这粗豪的表达对自己爱意的方式,两只小手轻轻拍了拍他爹的后背,示意可以把自己放下来了,再不放,自己这小小的身躯,就要在他爹一双可以按住山猪的强健臂膀中憋死了。朱长安站在一旁,看他父子相见的感人画面,眼眶一酸,情不自禁的又涌下泪来。
正是慈父更胜严母,小别牵动父心。
等到朱十三的情绪稍微平稳了下来,朱长安才抢上前,一边招呼着朱笃去里屋休息,桌子上给他备好了山楂呀,苹果这类的甜食,一边又向他哥细细的说明了这事件的原委。
关于带猪肚暂时离开吉安镇的这几天的经历,纪筠早就想好了一套还算说得过去的说辞,只盼能瞒过朱家哥俩。实在是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太过玄奇难名,普通人知道了,不过是陡增惊扰罢了。
只是有一节,就是在五枝镇办事的周郎中可是知道,纪筠和朱笃根本就没有去找过他。如果后来朱家哥俩想向周郎中表达谢意,露了馅儿,纪筠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本着能瞒一时是一时,能混一天是一天的想法,纪筠只管用这番话把朱家哥俩儿哄来。
他把路鬼上身,推说是朱笃得了一种极罕见极险恶的疾病,若是拖延了治疗时间,朱笃年纪轻轻身子骨弱,免不了就有失去性命的危险。
这番话说的朱家哥俩头上的冷汗又是涔涔而下,当下这两人千恩万谢,把纪筠送出去,并许诺明日还要备上一份厚礼送到纪筠那里去。
纪筠摇摇手只说不用,朱笃在里屋对继军招了招手,纪筠知道,这次的经历,可能在余生就要完全烂在朱笃,他还有陈车夫三人的肚子里了。
想到这里,纪筠莫名的反而有些畅快,他背着双手,慢慢悠悠地走出朱家大宅,就往自己的陋居走过去。
此时雪已经停了,是白天,天上的日光有些暖呵呵的意思。纪筠紧了紧自己的棉袄子,鼻中闻着淡淡的冰雪气味儿,只觉得闲适非常。
等到了家,一切陈设和他离开时的全无二致。房门仍是半掩着的,再看桌子上的书信,显然是被朱家哥俩拆开看过的。厨房里的灶上,那小半锅肉菜还冷着,纪筠这时候也恰好饿了,便把这肉菜热了,拿了一文钱出门,在永宁巷街怀安县转角的地方,看到了卖炊饼的武大郎。
武大郎平日里赚的钱多,他也知道冬天没有什么客户上门,于是就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袄里面,掂着一双脚翘着二郎腿,砸吧砸吧旱烟锅,缩在角落里,烧饼摊子就在旁边,一点儿也不急,神态很悠然自得的样子。
他的心境倒是与现在的纪筠如出一辙。纪筠不禁失笑,远远叫了一声:“武大!”武大看是纪筠来了,也笑着站了起来,道了声“季先生好啊!”
这武大,脾性跟朱笃相似,平时也是个爱听故事的。平日里卖炊饼之余得闲了,就把自己那千娇百媚的媳妇扔在家里,自己换上一身青袍马褂,跑到茶馆里,找一个小地方坐着泡一壶茶,装的跟个富商员外似的,老神在在的听故事。一边听一边眼睛还眯着,看起来十分陶醉,以至于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有时候看到他这副样子都不禁笑出来。
“纪先生,您是来买炊饼的?”
纪筠含笑应是,把那枚铜板递给了他,武大揭开蒸笼,从里面取出了热腾腾的两只炊饼,拿油布纸包好了,塞进纪筠怀里。
“纪先生,快回去快回去!这炊饼啊,还是热的时候最好吃!”
纪筠道了声谢,回到家点火,把之前的酸菜猪肉热了一番。幸好寒冬腊月,这菜不容易坏,要不然现在纪筠还要担心自己吃什么呢。
肉菜热好之后鲜香美味,再加上纪筠饿得很了,他几乎是狼吞虎咽,把那两只烧饼连同一大碗肉菜给吞下肚去,这才觉得稍微舒服起来。
茶楼现在是去不了了,当初和茶馆老板说好,自己连讲七天,但是第三天晚上就发生了大鼠闯进来,斗杀了五个恶贼的事情。
尸体全留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茶楼老板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可别把自己当作了杀人凶手便是。
想到两天前那场在茶楼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凶杀,纪筠也熄了现在就出门说书挣钱的念头。
在小驿站里那个老板给的封口费,就是那一摊碎银子,现在全在他的怀里。纪筠在路上也细细把这些银子数来,都是碎的,零的,总数不多,但是加起来也能有二两重。
二两银子,就是两千文铜板,精打细算是够他过两三个月的,纪筠也不急了,这就叫腰缠千文呐。
左右无事,纪筠推门进入书堂,坐到自己平时写作的书桌前,摊开纸,研好墨。
大冷的天,墨汁都冻硬了,他又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小瓶白酒,这白酒他是从来不喝的,专门防着冬天这个时候化墨用。
滴几滴白酒入墨汁,酒香四溢,纪筠眼睁睁的就看着墨慢慢的软了,能化开了,他就用毛笔满满的蘸了墨。
拄着笔杆,他就在那里寻思呢,写什么好呢?其实如果是说写什么,对目前的纪筠来说完全不是问题。这一路上跌宕起伏,遇到的那些神鬼,可是足够一个说书人写出好几篇故事,甚至写出一个章回体的全套折子。
可是纪筠心下清楚,自己今后要想再碰到这样神异的事情,那可是千难万难,这一段宝贵的经历,如果不把它好好写出来,那真是对不起评书行的祖师爷爷。
纪筠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把这一段经历先放上一放,等日后自己笔力强了,更有经验了,赶到三四十岁,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编排成书,老辣地说上那么一两折,是定能博得满堂喝彩的。
念及于此,他才会冥思苦想,自己究竟该写些什么新的故事出来,其时,评书行已经十分发达,什么山精湖魅,蛟龙出海,那都是有的。甚至什么女驸马,凤求凰,书生夜宿山庄遇鬼,美女蛇趴在墙头看人,都是有人早就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想要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对每一个说书人来说都是千难万难。
纪筠咬着笔杆子,墨慢慢的又冷了,于是他又去拿白酒瓶往里面滴了白酒。他一边滴一边想事,谁料这一次白酒瓶晃了几晃,无论如何也滴不出来一滴了。
他这时才发现,原来自己老是忘补充白酒,这个酒壶已经空了。
纪筠摇头叹息着站了起来,心想要不先缓两天休息休息,最近实在太累,自己若说本有三分才思,现在也一滴也不剩了。
想着自己的柜子里或许还能留着一瓶白酒,纪筠就往橱柜那里走去。打开橱柜,瓶瓶罐罐的,纪筠翻来找去,白酒半点影子都没有。
他悻悻然叹了口气,刚打算把柜门关上,突然,他的注意力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咦?这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