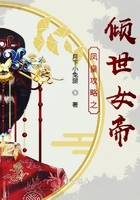南荣瑰在收到陈季之的回信时,还心存疑惑。
怎会如此之快?
但当她看到信中所说的内容后,便笑了。
原是要面谈。
南荣瑰明晓了陈季之的意思后,便也琢磨了一下日子,定下时日后,她倒也没写回信。
一则是传来传去的麻烦不说,还极其令人怀疑;二则她想当面与陈季之讲。
于是,翌日下值后,南荣瑰便开了口:
“季之啊,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日罢?”
陈季之挑眉,调侃道:“南荣,你讲真的?我们着这一身去?”
南荣瑰当下便开怀笑道:“季之,你怎得如此心急?自然不是啊,待回府后换身衣衫再去。戌时邀月楼静候季之兄。”
说罢,南荣瑰朝陈季之揖了一礼便上了自家的马车。
身后,陈季之哭笑不得,但却突觉身旁似有阴风瑟瑟。
不对啊,虽是冬日,但今日阳光甚好,怎会有寒风呢?
陈季之正迷惑间,一道清凉至极的声音从他身旁传来:
“陈守备与朝阳的关系倒是令人艳羡。”
陈季之平日里豁达惯了,但此时倒也觉得这句话听得不甚对劲。
一个守备,一个朝阳,这分别太大了些吧。就算是封号而已,可也不必喊得如此亲密罢?
蓦地,陈季之被脑中出现的“亲密”二人惊了一惊,顿时清醒了些,从那冥想之中回过神来。
“大学士说笑了,不过志同道合罢了。”
迟隐迎着陈季之坦坦荡荡的眼神,终是放下心来,但还是被方才二人熟稔的言行举止激了一番,由此甚是“正直”地劝解:“志同道合甚好,但就是怕有心之人看了去,陈守备还是注意一下。我就先行一步了。”
说罢,迟隐便利落转身离去,独留满面迷惑的陈季之一人在原处。
彼时,通身风流的颜锦绣从陈季之身旁走过,不禁骂道:“啧,有心之人,也不知有人之人是谁?可真不要脸,人面兽心。”
陈季之听到颜锦绣的话后,更是惊悚。
他方才听到了什么?颜锦绣当众辱骂迟大学士?
世道变了。
陈季之也不敢上前询问,连方才的疑惑也不继续想下去了,他只想早些回家。
戌时邀月楼。
“季之和温先生来了,快请坐。”南荣瑰起身迎道。
陈季之已没有一个时辰前的心惊胆战了,现下正是往日里那个豁达至极的陈公子。
温晋依旧是一袭青衫,温文儒雅的模样。
“南荣客气了,两日前我给先生看了信,奈何他不与我讲他的想法,还是南荣你的面子大啊。”陈季之先是打趣了一番。
闻言,南荣瑰笑言:“如此这般,季之兄更要珍惜了。”
三人同时笑了。
笑声渐止,温晋方开口问道:“郡主修书于我二人,想必是探查中遇到了些阻碍?”
南荣瑰回:“先生说得极是。我派遣我的两名属下去那处宅院蹲守,没想到一人重伤,另一人则是有去无回。”
温晋依旧是转着他那手心里的两枚棋子——一枚白子,一枚黑子。
随后,他开口道:“既然如此,那倒不如来一招釜底抽薪。”
南荣瑰与陈季之相视一眼,随后南荣瑰又笑:“先生啊,我这里倒也是有一则趣闻,您二位可要听?”
陈季之与温晋看着满面春风的南荣瑰,总是有些心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