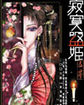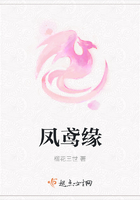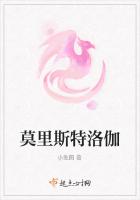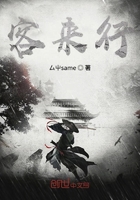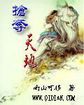树胶般,缓缓流下的泪,粘和了心的碎片。使我们相恋的,是共同的痛苦,而不是狂欢。
——顾城《悟》
她第一次看见襁褓之中的婴孩,头脑中便浮现出终年不散的大雾,还有未知山脉的一处森林,郁郁葱葱,泛着幽蓝的光,而森林的尽头有一棵傲然耸立的大树,她知道那是杉。仿佛有一道神圣的曙光照耀着这片大地,她在无穷的黑暗中穿梭,企图到达杉树之下。
她轻轻地抚摸自己孩子粉嫩的脸颊,然后唤他。她想叫这个孩子林尽杉,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名字,跟他如齿轮咬合一般完美。
十点左右,窗外下着绵绵细雨,这是春日长久的征兆。灰蒙蒙的天,看不到一丝月光。
刘舒康撑着伞站在医院外面,他不习惯医院里弥漫的消毒水与酒精的味道。
林尽杉姗姗来迟,看见刘舒康的一瞬间,有些惊讶和疑惑,他向老师问好,正准备进去,刘舒康拉住他,说:“你母亲还在抢救之中。”
他们走到台阶上,雨从林尽杉的额头滑落,灌进衬衣和运动鞋里,刘舒康说:“我去找医生拿块毛巾给你擦擦……”
林尽杉摇头制止了他,“不用了。”
林尽杉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刘舒康,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黑夜中塞钱给母亲的那个男子的身影。
仿佛一个隐世的咒语被揭开,林尽杉恍然顿悟,感觉像是被刺狠狠扎进了心里,他略显颤抖的声音问着,“是……刘老师把我妈妈送来的?”
刘舒康点点头。
林尽杉慢慢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摇摇头,然后咬住嘴唇,眼前这个成熟的男子是自己最为尊敬的老师,而他同样也是在深夜与母亲幽会,企图拆散自己家庭的男人,这样的认知让林尽杉感觉自己的气管里塞满了棉絮,无法顺畅地呼吸。
雨渐渐变小,刘舒康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或许你早就知道了,我与你母亲的事情……”
此事在林尽杉的心中就像是不可触及的雷区,他感到一阵晕眩,脑袋嗡嗡作响,“刘……”原本的称呼在此刻却叫不出口,“你应该知道她是有家室的人,你们这样让我觉得恶心。”
刘舒康弹了弹烟灰,“不,小杉,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你,但你不该这样对你母亲。”
他有些激动,烟头的火星差点烧到他的手指。
这时,有医生从抢救室走出来,眉头紧锁,看起来并不乐观,“你们谁是她的家属,麻烦跟我来一下……”
林尽杉跟在医生的后面,刘舒康则目不转睛地看着急救室的大门。
医生看着面带稚气的林尽杉说:“你是她儿子?”
林尽杉点点头,医生微微叹气,“你爸爸呢,怎么没来?”
林尽杉撒谎说:“他……很忙,来不了,有什么你和我说吧。”
医生再次叹气,然后从抽屉里抽出一支笔,“现在马上下病危通知书,你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你知道她有心脏病吗?”
林尽杉睁大眼睛摇头,医生用笔点了点纸,“很严重,而且她长期劳累,再加上刚才剧烈运动,血液供应不足……现在她还没有醒过来,还处于危险期。”
林尽杉抓着医生的手,带着哭腔,“医生你救救她好吗,我求求你!”
医生连忙安慰道:“你别激动,有些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现在你母亲病入膏肓,只有看她自己的造化,一切还得等她醒过来才知道。”
那一夜林尽杉和刘舒康安静地坐在医院走廊的木椅子上,医生护士来来往往,只有他们是静止而独特的。
刘舒康将外套脱下搭在林尽杉的身上,这一刻,他仿佛感觉到一种类似父爱的浓烈情感,但他又很快就打消了头脑中虚妄的念头。
刘舒康放平双脚,多次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望着医院走廊的尽头,咽了一口唾沫,“大概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你母亲还没有嫁给你父亲的时候,我曾与你母亲相恋。”
刘舒康感觉到身边这个孱弱的少年微微一震,他知道这孩子受惊了,他深深地吸气,开始将一个庞大而冗长的故事讲述给少年听。
在异乡的土地上,清冷的月光总是让人惘然。
二十五岁的刘舒康时常想起那个身着红衣裳的大辫子姑娘,她笑容清淡,常常站在高大的梧桐树下看他,一直看到他们都双双长大。
那是迁徙的年月,不断有人家脱离那座古老的小城背井离乡,在暴雨来临之前离开。
刘舒康的家住在街的东面,沿着青石铺砌的道路一直走到尽头,风化的石墙缝里长着小花,孩子们拉着风筝在街道上奔跑,大雨之后的树木显出格外青翠,空气中弥漫着清香。
每月初三是古城的赶集日,因为父亲生病,而母亲需要照顾父亲,刘舒康便帮父母到古城南边的市场贩卖一些商品,他在人流中看见了她,她慢慢地走着,不时东张西望,为热闹的气氛所感染,还穿着平日最喜欢的红衣裳。
她随父亲在刘舒康的摊位前停下,清秀的脸上带着少女独有的狡黠。年长的父亲说家里的簸箕该换了,于是弯下身子挑选,而刘舒康神不守舍地看着站在摊前的女孩儿,当少女父亲询问价格时,他竟出神地忘记了回答。
父女俩走的时候,他听见了那个女孩儿的名字,李清。
在那个封闭的时代,像刘舒康这样在校念书的学生是不能随便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情的,他默默压抑着,在破旧的阁楼里偷偷写下送给心爱姑娘的情诗,并在心里念诵。他天真地期盼着一份隽永的情感,却又不敢诉说,只能在相遇的时刻深深凝望。
李清家不算富裕,初中毕业后,她就经父亲介绍到煤厂挑煤。父亲长年在外,母亲以帮人理发为生。李清每天早早起床前往煤厂,在路上她会遇到那个在集市上见过面的少年刘舒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挎着菜绿色的布书包往学校赶。
他们匆匆相遇,又匆匆离散。
好几次,刘舒康都准备将深夜伏案书写的情诗交给她,但是又觉得难为情。他们的情感充满了含蓄与尊重,进展缓慢,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的姓名。
李清的工作是往复而劳累的,她穿着一件为工作准备的脏衣服,挑着一百斤左右的煤炭,她在黑色的土地上行走。夜晚睡觉的时候,两肩像撕裂一般疼痛,但是为了生计,她从不抱怨。
她有时候想,自己的一生必将在这个土地上碌碌无为地度过,安稳平淡也是一种美。
然而刘舒康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静态的平衡。
刘舒康知道李清的工作后,便常常出现在煤厂的空地上,他挽起衬衣的袖子,对李清说,“让我帮你吧……”
即使把感情隐藏得再深,女子也总是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李清自然懂得刘舒康的出现并非偶然。
李清看着刘舒康一人挑着两百斤的煤,那根担子就直接压在他的肩上,他冲着李清笑,咝咝地喘着气。累了,李清便用毛巾给他擦擦汗。晚餐分得饭票,李清就多买给刘舒康一个馒头。
初恋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再美好不过的,陷入情感之中的男女总是幻想着未来的某一天有着和现在不一样的境况。所有的人都会憧憬着成长之后的美好,却不知道成长的残酷和未来的虚妄。
刘舒康很快升入高三,父母要求他考上师专,那时候,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最大的光荣。
然而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小县城能考上专科的人屈指可数,希望如此渺茫,如同大海寻针。
刘舒康常常在夜里与李清见面,他们暗暗体会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意,又羞涩得不敢牵对方的手,只是安静地走着。
月高远而澄亮,晚风拂面,刘舒康为李清背诵一段文章,然后告诉她其中的含义。那时候的李清非常喜欢听刘舒康为自己讲解,她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生倾听师长的教诲。
有一夜,李清说:“舒康,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老师。”
语罢,两人沉默无语,刘舒康有些暗自神伤,他从书包里抽出那封写好多时的情诗,塞到李清的手上,纸张因反复揉捏而满是褶皱,他想了很久,开口说道:“李清,如果我考上大学,就要离开这里了,你会等我吗?”
李清望着古城的朔月,良久,她说:“舒康,我愿意等,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回来。”
刘舒康伸手,第一次触摸她的脸颊,李清微微颤抖,试图躲避,但最终还是正视了他的双眸。
那是一双真诚的眼睛,好像一片恬静的乐土。李清生在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而家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又注定了她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传奇,但是,她知道刘舒康不同,他是知识分子,他要走到更高的地方去。
李清不敢再往下想,她收敛了心中的期盼,然后说:“舒康,你会回来吗?当你走出这个破败简陋的小城之后,你还会回来吗?”
她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但那时的刘舒康已经懂得,男人不能随便给予承诺,一旦承诺便意味着立下坚贞崇高、不可动摇的誓言。
刘舒康无力地摇头,并非对于李清询问的否定,而是不确定自己的未来到底会走到哪里。
青葱岁月中一场悲伤的约会,双方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何去何从,缄默的夜空下,他们在路口告别,李清手里还握着刘舒康递来的情诗。
如果丛林葱郁,
我愿意做潺潺而过的小溪,
在你的心间,
刻下深渠的痕迹。
如果天空碧蓝,
我愿意做展翅翱翔的雄鹰,
在你的眼前,
深深将你拥抱。
如果你站在岸的那头,
我愿意唱一支百转千回的夜曲,
如果你乘着河上小舟,
我愿意执一支桨带你游荡。
愿你将我深深铭记,
哪怕我只是苍茫夜空中平凡的一颗星。
至此,李清与刘舒康再也没有见过面,她常常倚着窗户,就着月光读那首诗。刘舒康的字刚劲有力,却又整齐匀称,就像他的诗一样,像流水亦像雄鹰。
她偶尔也会在那棵梧桐树下驻足,想着刘舒康会不会突然走过,但是她没有再看见他。李清继续挑煤干活,刘舒康继续为学业奋斗,他们再次成为了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在各自的世界生活着。
七月流火,刘舒康拿到了师专的通知书,父母喜出望外,传得整个小城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消息传到李清耳中的时候,她还在煤厂挑着煤,一听之下百感交集、无语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