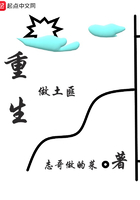“该当的,司徒大人本就是国舅,乃小王之长辈,又兼德高望重,小王以师礼相侍,乃理所当然之事。”李恪一边说着,一边坚持要拜,长孙无忌自是不肯依,这老少二人就这么你推我不让地纠缠在了一起,煞是有趣得紧,生生让诸遂良与崔泽二人都看傻了眼,到了末了,还是崔泽反应快,强忍着笑意,大步走上前去,帮着长孙无忌扶住了李恪的身子,口中却道:“殿下拳拳之心可感日月,然此事却实草率不得,纵要拜师,也须寻个良辰吉日方好,殿下且请安坐,一切从长计议如何?”
一听崔泽如此说法,李恪立马借势站直了身子,笑着拱手道:“不错,崔博士此言有理,是小王孟浪了些,还请司徒大人海涵,若能蒙司徒大人收于门下,乃小王三生之幸也。”
长孙无忌一听便知李恪的算计何在,这是要拉拢自己来着——虽说长孙无忌早前也有心要扶李恪上位,然则如今时移世易,李贞的根基已深,绝非轻易能动摇得了的,长孙无忌这份心思早就泯灭了,若不是此番李贞来势太汹,长孙无忌压根儿就不想跟李恪套近乎的,毕竟此时尚未到必须与李贞生死相搏的地步,长孙无忌又怎肯轻易地跟李恪拉拉扯扯地纠缠在一起,不过么,长孙无忌乃心机深沉之辈,却也不愿轻易得罪了李恪,万一将来李贞真要对自己动手,说不得还真要李恪这么个人物来扎起,故此,面对着李恪诚恳已极的表情,长孙无忌也只是笑呵呵地道:“好说,好说,一切从长计议,从长计议罢。”
听话听音,以李恪的智商,自是听得懂长孙无忌话里的潜台词,那就是说一切走着瞧,将来或许有可能联手,而这对于李恪来说,却已经算是勉强达到目的了,自是不会再故作姿态地纠缠此事,这便笑着道:“司徒大人所言甚是,小王受教了,您请安坐。”
见李恪如此识趣,长孙无忌心头一松之余,也甚是欣赏李恪的机灵,哈哈一笑,拱手为礼道:“殿下请坐。”待得见李恪落了座,这才走回自己的主位上端坐了下来,笑眯眯地看着李恪,等着李恪将底牌亮将出来。
见今日已经不可能再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李恪虽心中略有不甘,可也没辙,此时见众人都笑咪咪地看着自己,自也清楚是到了该交出底牌的时候了,这便沉吟了一下,笑着道:“司徒大人,诸相,这几日雪大天冷,极易伤风,若是一不留神病倒了却是不好,恐有贻误朝议之虞也,还请千万小心方好。”
李恪这话说得蹊跷,长孙无忌及诸遂良一听之下都愣住了,一时间也闹不明白李恪话中的含义何在,倒是崔泽灵醒,心头猛地咯噔了一下,有心不想解释,可一见长孙无忌探询的目光扫了过来,无奈之下,也只能笑着道:“殿下所言甚是,这天气还真是糟得很,众臣工若是不留神,只怕还真会全都病倒了,若如此,朝议之事恐难以为继也。”
长孙无忌这回可就全听懂了,眼珠子转了转,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鼓了下掌道:“是极,是极,老朽倒是忘了此事,哎,本该提醒一下诸臣工的,回头就紧赶着去办上一办罢,不过……”长孙无忌话说到这儿,却又停了下来,露出一副忧虑的样子,看着李恪,一派欲言又止状。
李恪乃是有备而来,自是清楚光使出拖延战术并不足以阻止《移民疏》的通过,此时见长孙无忌如此做派,不问亦知长孙无忌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却并不以为意,笑呵呵地接着道:“洛阳乃是数朝古都,好地方啊,更难得的是如今地广人稀,若是按我朝体制授田,当可延续数代而无缺田之窘境,当然了,若是广移民以实之,那可就不好说了,呵呵,若真如此,却不知洛阳之民众会做何想,小王倒是期待得很呢。”
李恪此言一出,长孙无忌等人全都倒吸了口凉气,瞪大了眼,惊疑不定地看着李恪,一时间竟无人出言询问个究竟,可心里头却都被李恪的胆大妄为所震骇——民变向来是历朝历代最害怕的事情,处理上稍稍一个不小心,便会摧垮一个皇朝的根基,似李恪这个主意乃是杀鸡取卵的办法,真要是强盛的大唐因此事而陷入崩溃,那么,参与其事之人可就全是十恶不赦之辈了。
长孙无忌虽不满李贞的《移民疏》,可为的仅仅只是关陇诸门阀的利益罢了,他可不打算做葬送了大唐基业的罪人,毕竟大唐之强盛乃是长孙无忌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愿望,岂能因着私怨而坐看大唐乱起,故此,李恪话音一落,长孙无忌立马收起了笑脸,也不开口问话,只是一味冷冷地盯着李恪,一副李恪不解释清楚此事,便要下令逐客之状。
李恪敢出这么个主意,自然有着他的把握在,此时见长孙无忌变了脸,却依旧浑然不以为意,淡然地笑了笑,随口解释道:“父皇向来信奉圣人之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是民意所向,父皇向来从善如流,今若真有移民之事,既累了关中之民有迁徙之苦,又害关东之民无授田之福,弊政也,以父皇之英明,又岂能坐看此事发生?”
李恪虽说得风轻云淡,可长孙无忌却依旧板着脸,丝毫没有就此放松下来的意思在内,倒是坐在一旁的诸遂良皱着眉头问了一句:“《国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今若民心变易,何如之哉?”
“诸相问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自古不易之真理也,然,若是移民伊始,百姓积怨必深,莫非便不会有怨言乎?小王诚不信也,既然如此,与其事后补救,不若事先制止,与百姓剖析利弊,由百姓自择之,岂不更佳,若控制得宜,更是安抚人心之良方也,诸相不可不察。”面对着长孙无忌的冷脸以及诸遂良的诘问,李恪潇洒地拈了拈胸前的长须,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这个……”诸遂良依旧觉得李恪此策有着不妥之处,却又无法从李恪的言语中找出破绽来,一时间尴尬地不知说啥才好了。
“却不知殿下所言的‘控制得宜’又是如何个控制法,下官愚昧,还请殿下指点迷津。”一见诸遂良被驳得无话可说,崔泽立马接口追问了一句道。
李恪饶有深意地看了崔泽一眼,哈哈一笑道:“自古以来,所谓民变有二:其一为有小人作祟,并操纵,乃为民乱,乃大忌,当绝之;其二为民愤不可遏,乃是对朝廷之举措有所不满,自发签名以为请愿,乃是出自对朝中奸佞之不满,非针对朝廷社稷,此等变对于开明之朝廷当是好事,实不能以变乱而视之,不知崔博士以为然否?”
崔泽学富五车,自是知晓民乱不可倡之理,哪怕李恪说得天花乱坠,他自也不信,刚要出言反驳,却见长孙无忌一扬手道:“殿下请见谅,老朽偶感了风寒,恐难支撑矣,所有诸事概无法参预,身子骨乏了,得早些歇了,殿下请自珍重罢。”
李恪见长孙无忌虽是下了逐客令,可话里却暗示他会称病不去朝议,但绝不会参与到李恪鼓动民间的事情中去,这原本就是李恪的策划,只消长孙无忌肯配合着让一众关陇权贵们称病不朝,李恪也不担心将来无法将长孙无忌拉拢上船,这便笑呵呵地起了身道:“司徒大人请留步,小王先告辞了。”话音一落,潇洒地拱手为礼之后,一转身,缓步行出了厅堂,由在门外侍候着的长孙冲陪同着出了长孙府,径自回自家王府去了,只留下长孙无忌等人面色凝重地在厅堂里默默地沉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