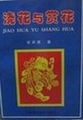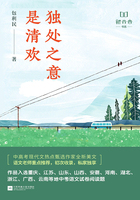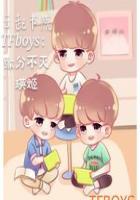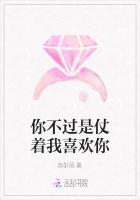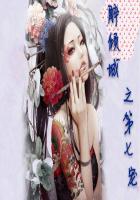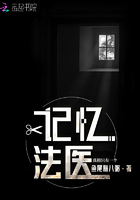新词也好、俚语口头禅也罢,只要有助于表情达意,但用无妨。至于不喜欢它们的前辈,也尽可以坚守着纯洁而又纯粹的汉语,如“精明上进”之类,写他的文章、骂他的山门,还可以编些个《写作指南》,教教文学青年。
未卜
据《北京晨报》报道,2000年9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爱滋病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已达成共识——爱滋病病毒是从非洲一种黑猩猩身上传染到人体内的。有的专家甚至推论,它可能是五十年代在非洲进行小儿麻痹症疫苗试验时,从猩猩身上传给人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犯错误、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历史。我们曾在动物界“除暴安良”,却引发了生态失衡物种灭绝;我们信奉过人多力量大,却吃够了人口爆炸的苦头;我们笃信过人定胜天,大面积地毁林开荒,得到的是河水断流、洪水泛滥的报复。为了延年益寿,我们喝过红茶菌、打过鸡血针。今天,喝什么水的争论,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为商业问题甚至社会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喝着花了大钱买来的“纯净水矿泉水”,谁能有绝对的把握,说他们的健康不会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若干年后,他们会不会又要花更多的钱买各式各样的药片药丸,以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当我们背靠丰富多彩的已知世界,笑谈前人的无知和无奈时,却忘了在浩瀚的未知世界面前,我们也是同样的无知和无奈。在已知的世界面前,人类是强大的;在未知的世界面前,人类又是渺小的。为了和平与发展,为了生活得更好,人类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实际上,我们最信赖的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难以预见的灾难。可悲的是,为了发财、为了享受,新的研究和发明总是迫不及待地被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它们的副作用常常被发明者、销售者、使用者忽略不计。比如风靡全球的“伟哥”、比如敌敌畏、比如洗衣粉、比如汽油柴油……
我们必须花多大的代价多长的时间去弥补这类损害?何况有些损害是无法补救的。那些中了敌敌畏的毒而灭绝的鸟儿,再也不会飞翔在蓝天下。可怕的不仅是这种损害,还有我们对损害的一无所知和无能为力。已经有报道说,重病缠身的伊拉克强人萨达姆,正准备克隆100个小萨达姆,为了他的永生和不灭。对于多利羊的制造者来说,这算不算绝妙的讽刺?人类能够探索科学、发展科学,却无法阻止它助纣为虐。
面对不断涌现出来的发明创造,我们的选择是盲目而无助的。时下崭露头角的转基因动植物,最终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又有谁能够预料呢?在“是”与“否”的答案面前,我们的前人也一样地盲目过、无助过。很多次,他们选择了“是”。 不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健康乃至生命,但人类的总体生存质量得到了改善。就像小儿麻痹症疫苗试验可能造成了爱滋病的滋生,它毕竟是科学的过失,不是罪行。
为了后人,在不断涌现出来的科学发明面前,我们仍然必须作出选择。尽管我们迷茫不安、痛苦无助,尽管利弊难测、吉凶难料、生死未卜。未卜,只是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侧面,就像阳光下的树木,总有阴影。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努力。但愿某项重大发明投入实用之前,科学家和他们的赞助商能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克制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欲。而要使科学只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这又不是科学本身所能解决的事了。
轮回
时下,做一个都市中人,似乎烦恼多于快乐。我们经常因工作压力、房屋还贷、子女升学而紧张,时时被交通堵塞、热岛效应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所困扰。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质匮乏,在食品供应充裕的今天,我们又要为食品的洁净与安全担心。蔬菜水果上有多少残留的农药和激素?猪肉猪肝是否含有瘦肉精与荷尔蒙?粗壮的鳝鱼有没有喂过避孕药?……
曾经不无向往地对朋友说,真想有一片自己的土地,种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的庄稼,养不关在笼子里、不吃饲料粉的禽畜,自给自足、悠闲自在。朋友笑我,你的想法很好,可惜太奢侈。
前不久,出现了“有机蔬菜”热卖的报道。“有机蔬菜”是“一种生长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绝不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防腐剂和添加剂,也不采用基因技术的安全环保生态食品”。倘若我们在地下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知道这些,他们会不会哈哈大笑,笑歪了嘴?这种不用农药化肥,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和基因技术的“安全环保生态食品”,不就是他们靠农家肥和锄头铁搭种出来的庄稼么?工业化地生产农作物畜产品的后果,必定导致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时的不择手段。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孩子们的发育期普遍提前,当脂肪肝糖尿病之类的富贵病和癌症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中间,当欧洲的畜牧业饱受疯牛病和口蹄疫的打击……人类终于醒悟到,工业化不是万能的。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终将引来无情的报复。近几年,纯自然性的生态农产品开始在欧美大受欢迎,生态农业悄然崛起。然而,我很怀疑,在大气、地表和水系全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污染的今天,人类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还清集约化农业所欠下的债?
荷兰的一些城市居民,在农村拥有一小片靠近高速公路的土地和小屋。地约五六分,或买或租;屋仅一小间,简单质朴。每逢假日,他们就驱车前往,种菜松土、浇水施肥(当然是农家肥),小住几日。在工业社会住久了的人们,在一幢高楼与另一幢高楼之间出入太久的人们,来到静谧的农田里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心情,亲近一回土地,增进一点对大自然的理解,无疑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国的都市也会兴起假日耕作,我的梦想,也能实现一二。从疏离土地到重回土地,从轻视自然到重新敬畏自然,人们的认识又经历了一次轮回。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正是这样螺旋形地上升发展的吧?
时尚与垃圾
前不久,贝克汉姆剃了一个莫西干式的头发,有点像印第安武士,又有点像报晓的公鸡。原本想标新立异,想不到模仿者甚众。上至八旬老妪,下至黄口小儿,闹得乌烟瘴气、不亦乐乎。有的学校为此专门制订了校规,不准学生剃莫西干头。小贝说声不好意思,又变回平头。
曾经以为时尚是一种很值得尊敬的东西,看得多了,才知道它不过是商家和设计师联手玩的把戏,将消费者的荷包尽可能掏空的把戏。它不断地花样百出、标新立异,它不懈地改弦更张、制造流行。比如穿的时尚,肩垫加了又撤、裤管小了又大、裙子长长短短、色调忽冷忽暖、松糕鞋平底鞋、西装旗袍马夹肚兜……反正,不让爱美的姑娘时髦的小伙血本无归决不罢休。
有人说,妈妈的衣裳老土,祖母的衣服新潮。童年的夏天,我的外婆常常系着一方肚兜操持家务。今天,肚兜果然成了时尚。只不过料子好了一点点,价钱贵了许许多。
今天的时尚是品味、是新潮,昨天的时尚就是陈货和垃圾。时尚总是很忙,忙着淘汰垃圾,让自身变成垃圾。明天的时尚会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它总能养活很多人。时尚更新的频率总是与社会的富足成正比,有时尚总比没时尚好。而不喜欢追赶时尚的人,比如我,尽可以站在岸上,远远地欣赏那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时尚潮流。
古典
1977年秋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这一届即将毕业的中学生,接到了再读一年、复习迎考的通知。父母问我打算报考什么专业,我老老实实地说,想学古典文学或是植物学,引来一片哂笑。古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看作过时、陈旧、落伍的代名词,无人问津。
多少年过去,当文化这面酒幡在商业的门面上飘得破烂不堪、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古典,也被人从故纸堆里拽了出来,从积满灰尘的香案上抬了下来,巍巍然、峨峨然,在一夜之间成了高贵典雅、高品味高身价的代名词——“亲水园林、古典情怀”,“古典的微笑、温柔的浪漫”……。在眼球经济的炮制者看来,所有能把眼球骗过来把钱包挖开来的陈芝麻烂谷子以及废铜烂铁都是古典,比如残破的古罗马圆柱和翻铸过N次的西洋人体雕像。
真正的古典是一种文化的氛围和气息、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和特质,绝不是几件长袍马褂、几处亭台楼阁所能冒充的,也不是雕花铁栏杆和红木太师椅所能够复原的。可笑可叹的是,我们一边购买绿色食品,一边污染着环境;我们一边呼吁保护古老的文化遗址,一边大量开放残存的古迹。几乎没有一处古典建筑、没有一片原始森林,能逃过商人和准商人的目光和嗅觉——鹰隼一样锐利的目光、猎犬一样灵敏的嗅觉。我不知道若干年以后,我们还能有多少古迹可供游览、可供凭吊、可供赚钱。
物质的古典末日已至,精神的古典便无所附丽。当善良、真诚、责任和宽容也日渐沦为古典,当虚伪、浮夸、张扬和无需掩饰的倾轧成为时尚的时候,古典便不可救药地死了。我们还能指望在喧嚣街市上昂首阔步的摩登女郎绽出古典的微笑么?我们还能指望唇红齿白玉腿纤纤的她们从眼神里流淌出“斜晖脉脉水悠悠”的惆怅么?那些明亮如星的眼眸里,除了冷漠、放纵以及对名利的渴求还会有什么?如今的淑女,只是些温柔到牙齿的、等着俘获成功男士的藤蔓。如今的绅士,也不过是些垂涎美色的食客。遵守规则的男人被认为是蠢货,坚守感情的女人被看作是傻瓜。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我们虽然不会怀旧了,但总算学会了装旧。让我们在那些泛滥着怀旧情调的咖啡馆里款款坐下,点一杯温热的咖啡,看一看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听一听留声机转出来的爵士乐,翻一翻那时候的电影海报,把自己想象成当年的影迷,作一次深沉的古典秀。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年以后,今天的伊妹儿和深海鱼油,也会成为古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