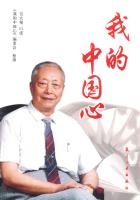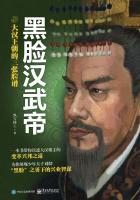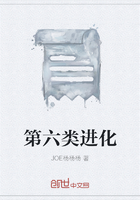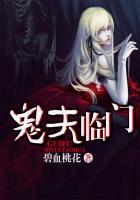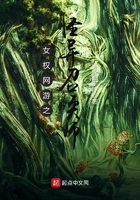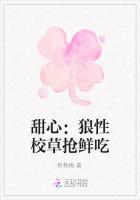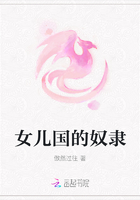这位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由中国》半月刊编委在“雷震案”初审判决之后,将自己的生命危险置之度外,先后于1960年9月28日和10月12日在《公论报》上发表两篇有关“雷震案”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顽强地抗争。《公论报》在编者按中说:“雷案究竟是‘政治事件’还是‘法律事件’,各方因此颇多争论。殷海光先生应本刊之请,特就这个论争的中心实质所在,为文加以阐明,是令人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殷海光与雷震相交十多年,对这位前国民党高官有着本质的认识。当有人对他说“雷震是一个失意的官僚政客,你是一个读书人,跟他在一起搞什么?”殷海光反唇相讥:“照我看来,雷震先生不只是一个‘官僚政客’,而且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殷海光这样写道:
在他人生的历程中,摆着两条可以任意选择的道路:第一条,照美国《时代周刊》和台湾《时代潮》杂志上所载的,雷震先生从二十岁开始就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连络四方。在中国政局动荡之秋,他曾尽力之所及,为在朝党立过功劳。来台以后,如果他利用他这个历史、“人事关系”,和他与政治当道的渊源,那么,顺理成章,他不难也和目前若干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做起特字号的官儿,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扬扬自得。他用不着这么大一把年纪,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往于木栅乡和台北之间。有一次,他的夫人宋英女士很幽默地对我说:“自从雷先生办《自由中国》以后,我们的房子是愈住愈小,车子倒是愈坐愈大哩!”第二条,雷震先生坚持他的“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这件事那件事,而且硬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崇高的官爵,而遭治安机构看守大门,而被阻挠印刷,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这两条道路,前一条坦易畅达,对自身有利;后一条险恶不堪,对自身不利。雷震先生偏偏选择了后一条。……雷震不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又是什么?
殷海光这段文字,道出了多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复杂而隐微的心路历程。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中,读书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理性抉择,尤其是在专制与民主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中,知识分子的“知与行”往往意味着其个体生命的沉沉浮浮,有时也真是“难与君说”了。雷震毅然决然地与曾给他带来荣华富贵的体制相决裂,依殷海光的看法:他是一位十足的“顽固而坚持的宪政主义者”,而且“很有毅力,胆识超人,威武不能屈,……能抱定一个理想,并且不避艰危地为这一理想献身。这都是他的特别长处,同时也是此地的知识分子特别缺乏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雷震提倡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有许多人士尚不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只当作耳边风。
经过这一个多月来‘雷案’的演变经过和若干表演,许多人士可以在脑筋里打打转,体会到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不是空谈,而是与一个人的祸福安危攸关的事。这次雷震先生个人之牺牲,至少可以促使许许多多人有这种认识。这种认识之加深和扩大,对于自由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有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雷震被捕的真正原因,殷海光一针见血地指出:“雷震先生之失去身体自由与新党之创建有关。显然得很,1960年9月4日上午若干人对雷震先生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对新党‘打蛇打头’的行动。我怎么也想不出这项行动有什么必要。我怎么也想不出雷震等人创建新党有什么‘危险’可言。”对于有着同样民主政治理念的殷海光来说,雷震等人组建新党不但对执政党毫无危险,相反还可起到监督、制约、平衡,乃至竞争的作用,这本来就是民主宪政中的应有之义。然而,蒋介石绝然不会这样想。所以,雷震被捕一如殷海光后来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一样,同样也是“事有毕至”。
雷震被捕,台湾社会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事件”,绝不是当局所说的这是一宗“法律事件”。对此,殷海光以《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为题,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以为“法律是公正的”。其实,法律本身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只有公正的人才会把法律用得公正。大家必须知道,法律是人为的东西。法律不会说话。法律不能自动的应用于任何人头上,应用法律的,是那些站在法律背后的人。在非民主的地区,同样是站在法律背后的人,谁最有力量,谁便能取得行使法律的决定权。所以,归根究底的说来,行使法律之事还是操之在人。既然如此,于是乎平日德行素习,宅心仁厚,尊重人权,服从众意,以天下为公且真以国家为重的人,如果握有行使法律的决定权,那么我们较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公正地在行使法律;我们也较有理由要相信他不会玩弄法律——拿法律作达到私图的工具。……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圣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拿国家法律作达到一人一党私图之工具的动机。但是,民主政治这种制度的本身,正足以防制这种危险的事件。所以,我们简直不能想象,美国现在执政的共和党如何利用国家法律作为打击、削弱,甚至消灭民主党的工具。推广来看,自美国立国一百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任何在朝党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来打击在野党派之事。
殷海光表示“法律是不会说话”的,并非不认同法律之于国家、社会及每一个自由生命个体的重要性,而是批评台湾当局利用手中的强权,将法律视为一党统治进而制裁政治敌手的党派工具。他这样说:……极权暴政之下有否法律呢?有的。而且似乎很多,他们也有民法、刑法种种等等名目。这些法律,恐怕比民主国家的法律更苛细而且也有“公理”、“正义”等等好听的字样。但我们能否因此就说,在极权暴政之下,人民的人权更有保障呢?社会有更多的正义和公理呢?显然没有。谁都应该明白,在这样的一些地区,所谓法律也者,只是维持政权和扩张“党势”的一种手段而已。
……在这种地区,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一个权力之摆布,哪里有“独立的法律”之可言呢?因此,所谓“法律事件”,不过是“政治事件之法律的表现”而已 。殷海光这篇文章,强调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在回应台湾立法委员、原台大法学院院长萨孟武“雷震案”只是一个“法律事件”这一说法。9月9日,萨孟武撰文称对胡适所说“雷震是一个爱国的人”这句话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并称《自由中国》半月刊诸多言论,“似是不妥当的”,也不相信雷震被捕与鼓吹新党有关。萨孟武是雷震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时的校友,比雷震早两年毕业。1924年萨孟武毕业返国时,雷震到东京车站为其送行,“并赠水果一篓”(雷震语)。萨孟武的这个说法随即遭到了雷夫人宋英女士的驳斥,殷海光的文章多少受此而引发,旨在论证“雷震案”完全是一起莫须有的“政治构陷”(或政治事件之法律的表现)。
判决之后引起的震撼
监察院“纠正案”石沉大海
据2002年9月4日台湾《联合报》披露,雷震被捕后,监察院曾三度展开调查,并责成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实、陈庆华五位监委组成“雷震案项目小组”。但调查一直遭到当局百般阻挠。军事法庭只允许调查马之骕、傅正、刘子英三人的案情,“主犯”雷震不在其列。尽管后来监察院调查小组调查结果表明:警总等机关在处理雷案时有“诸多不合”及“失当之处”,建议将其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可是“纠正案”递交之后,一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据悉,警总政治部有关人士建议对监察院的报告“以不理为宜”。陶百川等人欲从法律层面以挽救雷震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陶慨然发出“深知政府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自非监察院所能挽回”之叹。
《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报告》刊发在1961年3月10日台湾《联合报》上,党报、官报则一字未登。这时雷震已在安坑乡台湾军人监狱(今新店监狱)服刑。据报载,调查小组的监察委员至土城洗脑所调查傅正、马之骕后,第二天就来到军人监狱对刘子英展开调查,“并希望能够调查雷震”。雷震这时仍是“国大代表”,在狱中享受“将军级”单间待遇,即所谓“分居监”。1961年1月25日,雷震发现“军人监狱的分居监的小小院落,头一天就打扫得十分干净。惟时值冬季,风吹仍有落叶,第二天晨又令外役将地上昨晚落下的每片枯叶都捡得干干净净”。
雷震问:“何以要扫得如此干净?”狱吏说“今天有人来参观”。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有人(一位钟姓负责照料雷震的人)跑来对雷震说,监察委员要来调查你了。一个小时后,那人又跑过来说,监察委员不来调查了。因为“总参谋长彭孟缉打电话来,说是奉蒋总统命令不准监察委员面晤雷震,因为军人监狱是属于总参谋长主管也,林监狱长还在那里敷衍监察委员,并留他们吃午饭,说他再去请示,这明明是托辞,监察委员拒绝了,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询问,下午再来好了。” 雷震始终未能见到监察院调查小组的任何人,《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报告》也未提及“面晤雷震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