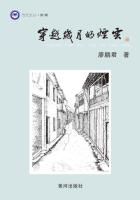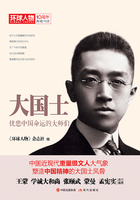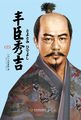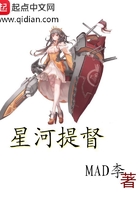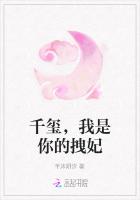雷震的反应也开始变得强烈起来,他认为“这不仅是加帽子,而有谋害之意”、“以言论对言论,本是可喜的现象,不过他们的方式错了” 。1957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答辩》一文,大意是《自由中国》从未认为自己的主张与言论,“是惟一的、终极的真理,所以欢迎批评与讨论,但刊物发现其面临陷构与诬蔑,却无法沉默”。同期还刊发了成舍我 以笔名范度才(谐音反奴才)撰写的《〈中华日报〉鼓吹暴动》一文,以回应《中华日报》上《蛇口里的玫瑰》一文对《自由中国》的诬蔑攻击。之后,军方刊物《国魂》以全册篇幅继续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甚至说这毒素思想的渊源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1月18日,成舍我在立法院见到陶希圣,陶对成舍我说:《自由中国》的言论太过激烈了。成舍我坦言:雷震过去与“老先生”(指蒋介石)有相当的关系,且为政府做过许多事情,你们现在逼人太甚,开除其党籍、国策顾问,最后连吃力不讨好的中日文化经济干事长也不让做了,何怪乎人家要反对你们 。雷震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未免太私人化了。
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自己曾给黄宇人去信,劝其“不可消极,自由是争取来的”,又说“吾人立于社会,只问良心安不安,不能畏惧权威,不然民主自由真无前途了” 。2月5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召开编辑会议,决定再写一篇社论《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以作出回应。王世杰则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 ,他甚至担心有人会谋害雷震。2月18日,雷震赴许孝炎 处,许对他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批评蒋介石个人;二,不批评国民党;三,态度温和。雷震表示,第一、第三两点均可同意,但第二点不能接受。雷震这样说:“国民党必须取消优越感,国民党员再不能有做皇帝观念”。
许又提出不“随便批评”,雷震认为“《自由中国》从未随便批评”,“对方可以批评,但不能加帽子,如对方说我们是匪,我则一齐取销”,许孝炎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几个月来,军中政治部门对《自由中国》的围剿始终没有停止,他们在军中散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而在国民党内部《工作通讯》上,也有《从毒素思想谈到党的思想教育》之类的文章,“二者均以自由主义者为假想敌,后者认为《自由中国》系危害反共复国与国家民族的思想敌人。诸现象反映党方、军方已有以权威心态对抗自由主义的态势,而公开对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抨击,则显示当局预备对自由主义进行思想压制。
” 不过,马之骕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垂死的哀鸣”而已,“国民党一发动围剿《自由中国》言论,一些靠津贴生存的报刊,莫不摇旗呐喊,不分青红皂白,乱箭齐发,假想造成一种‘强势舆论’,误导民众错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各报刊都说《自由中国》的言论错误,他们就应该俯首认罪’,其实不然,恰好弄巧成拙,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台湾民众。” 自出版“祝寿专号”后,《自由中国》“在编辑作业方面,只要一发稿,就有特务们到印刷厂要求看稿,必要时还要拿出去照相,再将原稿送回;出版后,只要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政府或是批评国民党的,就要受到数家国民党办的报刊的‘围攻’,不过久而久之,大家自然的就养成接受检查的习惯了,否则又将奈何呢?”不过《自由中国》也从此“豁出去了,俗话说‘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我和你拼了” ,即埋下了不久的将来雷震等人遭至政治构陷而锒铛入狱的因果。若干年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在评价这一期“祝寿专号”时说,“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并称“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
《自由中国》印刷受阻
《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受到当局公开压制后,印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从1949年11月20日创刊起,至1960年9月4日被迫停刊,近十一年的时间里,《自由中国》半月刊先后换过七家印刷厂,此事让雷震“大伤脑筋”。《自由中国》最初印刷是在“上海印刷厂”和“台北印刷厂”,这只是对外的名称,实际上前者系“情报局”所经营,后者为“国防部”经营。这两家印刷厂在原则上以其机关业务为主,常常耽误《自由中国》的出版。后来改换到“新生印刷厂”去印刷,这是《台湾新生报》自己开办的一所印刷机构。当时,雷震在政治上仍属显赫人物,《台湾新生报》副社长赵君豪为雷震旧识,愿意承印《自由中国》半月刊。自《自由中国》半月刊与当局发生言论冲突之后,该厂以“业务繁忙”为由不再继续承印,实际上是因为情治人员随时去印刷厂检查,他们不愿给自己在政治上带来更多的麻烦。
之后,雷震将《自由中国》的印刷业务转向台湾一些民营企业,第一家是“精华印书馆”。就其设备和排版技术而言,“精华印书馆”不亚于以上公营印刷厂,就是价格要贵了许多。“老板的名字叫陈太山,中等身材,胖胖的,方面大耳,看上去颇有福像,忠厚老实,处事稳重” ,雷震是经由立法委员陈纪滢的介绍与之相识的。从1952年12月,至1957年3月止,前后近五年多时间,《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都是在这里印刷。在第三年,陈老板突然提出不想印了,因为特务来得过于频繁,随时都要检查《自由中国》的稿件,“真是不胜其扰”。雷震特意去了一趟“精华”拜访陈太山,给他打气,再三拜托继续印下去,之后又坚持了两年。其间,马之骕作为经营部经理,与陈老板多有交道,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因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京剧。每当马之骕去印刷厂时,陈老板常会对他大发牢骚。他对马之骕说:
……“马先生,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印了,前天有一个特务来,一来就是坐半天,他还给我看相,说我好好做生意会发财,千万不要跟着雷先生搞政治,搞政治会倒霉的哟!”又有一次他说:“马先生你来了很好,我要和你讲,昨天有一个警备总部的特务来,硬要看稿子,我不给他看不行,他拿出警备总部的服务证给我看,就闯进排字房,还把一篇稿子拿走了,他说照个相马上送回来,不准我告诉你们……”我说,“不要紧,稿子送回来没有?”“有送来!”“那就好,雷先生已给行政院黄少谷秘书长打了电话,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他将信将疑地说:“我的血压太高,他们一来我就紧张!心跳!这样下去实在受不了。我知道,我不印别人家也不敢印,我看惟一的办法,就是你们自己办一个印刷厂。”
对于陈老板的这个建议,雷震曾仔细研究过,最终还是不敢下决心开办一所印刷厂,资金固然是一个问题,在管理上也一窍不通,又惟恐特务买通工人,弄不好麻烦会更大。尤其是“祝寿专号”之后,当局对《自由中国》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处境更加艰难。最后连介绍人陈纪滢也感到有点害怕,托人带信给陈太山,叫“精华”不能再印《自由中国》了,以免麻烦。陈老板果然表示,说这次宁可关门,也不能再印了。雷震很生气,说:“这件事陈纪滢不够朋友,不仅不出来帮忙,反来扯腿。”于是雷震又联系到“尚德印刷厂”,但只印了一期,“尚德”老板李文显也以书面形式通知《自由中国》社,声明今后绝不再印了。
无奈之下,雷震只好打破情面,亲自给新闻局局长沈锜写信,“精华印刷厂因受外界压迫,拒绝继续承印,……而尚德印刷厂商订承印合同约,该厂并已接受本社之订金三千元,但该厂在订约数日后,忽提出:‘如厂方受到外力干扰,即不便代印’之口头声明,随复通知本社,竟欲即时取消合同,当经本社再三与其交涉,始允代印一期,以后不再承印……”与此同时,雷震还致函“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因黄亦办过报纸(1942年曾任《扫荡报》总社长,作者注),懂得言论自由之可贵,而且他亦同情《自由中国》,所以请他出面设法解决印刷问题,应当不成问题” 。
印刷问题始终困扰着雷震,由于心情不好,失眠也越来越严重。过去他吃的是一种叫做Seunul的安眠药,一两颗就行,现在吃三颗也不见收效。他在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 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如再这样,我只有公开其事,一面决心停办,不然天天为印刷苦恼也不是办法……依照目前看法,他们表面上松懈下去,刊物上不再骂我们是共匪同路人,但是暗地里并未放松,因此有许多地方不卖本刊。”后来雷震又与“荣泰印刷厂”签了约。不幸“荣泰”在印了三期之后也以书面通知予以解约。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又想到了“精华印书馆”的陈老板,并认为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马之骕说:
“荣泰”既然不续印了,当然就要再找其它印刷厂。惟在此期间雷先生一直都在透过私人管道与官方、党方高层人士谈判、抗争,尽管被从四面八方来的围攻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仍然拼着老命也要把《自由中国》办下去。谈来谈去,结果经由行政院新闻局出面协助,加之《自由中国》同仁与“精华”陈太山老板的感情关系,认为还是由“精华”承印较为妥当。因为大家都知道“尚德”、“荣泰”两家厂不愿意继续承印的原因,主要是特务们每次来厂检查稿子时,全厂员工都很紧张,惟恐稍一不慎就被“抓起来”,再找一家新厂,恐怕仍有这种心态;而“精华”因承印《自由中国》久了,特务们时常来厂查稿已成习惯,在排字工人的心理上认为“你要看,就给你看,你要拿走,就给你拿走,反正有老板负责嘛!”因此他们看到特务来时,并没有什么“恐惧感”,只是耽误一些排版时间而已。基于这个前提,各方面均希望由“精华”继续承印。
陈老板在另一种压力之下,终于同意再次承印《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次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情治单位来查稿时均可随便,将原稿拿去照相也行,若因此而耽误了出版时间,“精华”不负全责,也不能因此而罚款;二,印刷费按一般较高的标准计算,并以结付现金为原则。为了能够确保《自由中国》的印刷,雷震只有接受这两个要求。就这样,《自由中国》从创刊到停刊,总共十年又十个月,“精华”前后承印了七年又七个月,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而且正在政治敏感度的尖端时刻,若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看,‘精华’老板陈太山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惜他活了六十多岁就过世了”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印刷问题,曾多次给黄少谷打电话,“一再请他出来帮忙”。由此可见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争取言论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当事人马之骕后来总结道:“……所述事实,证明‘印刷问题’,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当然若单从商业行为来看,就不成为‘问题’,因为买卖成交与否,是两相情愿的事;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独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看——印刷问题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