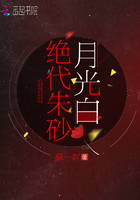终于,往日那个温和儒雅的吕阿帅又回魂了,只见他放下手里的论文,摆摆手冲我道:“母亲生病了是吗?这个课也没什么任务要做了,回去也可以,你明天就把结课论文还有请假条拿来吧。”
我霎时就松了一口气。
吕阿帅总算还没被气糊涂,紧接着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喜笑颜开的抱上姓名:“颜梓。木辛梓。就是学号07242117那个。”
吕阿帅翻出名单来用红笔在我的名字旁边做了个触目惊心的记号,然后摆手叫我退下。我刚才的强势都不知道跑到了那片九霄云外,谄媚道:“谢谢吕老师。”退出门去。
当然,临走前我还没忘记用刀子样的目光剜了那名嘲笑我的男人一眼。
回去的时候正碰上赵曼莲从主楼的广播站里出来。我同她打了招呼就往附近的火车售票点走。赵曼莲同学最后都没忘记关心一下我的精神状态。在她们看来,我失恋之后不说不动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是憋屈了自己,保不齐就要闹一个郁积于心,量变产生质变整出抑郁症来。
事实上,我是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人。
以往我见过以非常激烈的方式祭奠那已死的爱情的,比如说深夜的时候坐在宿舍楼的厕所里边吸烟边哭泣,或者搬了十几瓶啤酒在阳台上喝完一瓶朝街上扔一瓶,又或者蒙头大睡终日不起饭也不吃课也不上……如此种种,均对自身伤害太大,每次遇到我都觉得十分痛心。
所以,我采用的一般是比较健康的发泄方式。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干净利落的把他送我的东西扔掉,他写给我的情书都撕烂扔到厕所里冲掉,他的电话给放到黑名单里,他的QQ也做同样处理……然后在窗台上干坐着发呆两个小时,再然后,就去自习室找宿舍里的女人们,拉着她们在操场上绕圈走,边走边放声大哭。哭完就回去睡觉。
再醒来的时候,眼泪也干了,视线所及的物体都没有了那人的痕迹,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的干净。
此种处理方法,我甚觉有效。
至于处理过后的副作用,譬如说,在操场上绕圈的时候易皓安慰我说在J大找个男朋友随意的很,她声音很大,**场上有个正踢球的运动男听到了,便带球过来大剌剌询问:“是谁要找男朋友啊?看能不能考虑考虑我?
这就是我们宿舍女人的共同死党严由,一个身量中等,长相中等,学习中等,工作中等,运动中等的性别模糊人士。另外还有守门的黑人留学生来凑热闹,那便是大龄非洲男青年克莱克,中文名字叫做马岩。
严由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没得折。”
由于马岩经常跟着严由一起混,于是他也有了一句名言,叫做:“Ifthereisaflower,justpickit.”
每次想起这个,我都免不了要叹息一回。真真是近墨者黑啊。
副作用还有,又譬如说,我回家找我妈妈倾诉,我那无良的母亲为了参加初中同学的几场舞会,生生把我撇下,指派了老颜手底下打工的一名男青年带我四处走走解闷,闷倒是解了不少,只是没想到会引发新一轮的更大的闷。
因为这名男青年就是林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