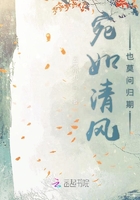她一直在做一个梦,今天也不例外。
灰暗飘雪的夜,不朽堡垒寂静如坟,只剩下能把骨头冻散架的寒风肆意妄为地掠过每一条街道。城市中央的红顶大礼堂静静地矗立着,犹如准备招待一位绝世的舞姬。
瑞站在大礼堂舞台的正中央,点上摆好成一个矩形的蜡烛。微薄的亮光团在一起,温暖不了什么,但是足够照亮她的周围一小圈地方。
红的地毯布透出一股油腻的黑,瑞只是分神地凝视了一会便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断撕扯她的精神,吸引她的全部。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
瑞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不仅仅局限于大礼堂的艺术家。她的脑海里正在以幕布为夜空,以脑海中添加的闪光为星星,以脚下的一片漆黑为墨绿色的草坪来构筑一个野外舞池...等等,这还不够,还要再下一场美得可以被画出来的雪,雪会重重地落在地上铺成被子一样,让人舒服地想窝在里面。
头一次,瑞隐约觉得自己不该加上雪,但来不及了。
如此盛大的场景不应该只有孤单的景色。瑞此时身穿连体的白裙,没有牌子,没有价格,没有过多的复杂的、让她感到烦躁的附加东西,只有洁白的裙子,恰好地贴身。柔软的织物贴在她温润的背部,舒服的暖意瞬间拥向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
她的膝盖微微弯曲,提起裙子的一角作为谢幕的动作——明明她什么也没跳,但是回过神来却只记住结束舞蹈的这一幕动作。
脑海里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呢?瑞压根没有这个概念,她更在乎此刻自己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模样是否完美地无可挑剔。
她微微低头,维持提起裙角的姿势不变,开始漫无目的地琢磨怎么让自己的眼角诱人而凶狠,把自己表现得像个绝世舞姬,而丝毫不在乎观众的目光。
暖意消失了,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功夫,她身上织物带来的温暖感便不复存在。冷风从四面八方灌入她的身体里,她感到自己似变得如一扇窗般完全通透,身上的织物被暴躁地剥走,只留下通体洁白、空无一物的胴体。
不,它不能称之为胴体了。瑞诧异地发现她正在变得透明,直至动弹不得,静静地站在原地。她就像一面镜子,镜子上呈现的画面是一个绝美的人正在训练她的舞姿,那不是瑞·安罗尔图,而是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再过一会,她清楚地听到了碎裂声,然后她躺在地上,能看到的地方尽是玻璃碎渣和血渍。
她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最后睁开。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穹顶式的圆形天花板,设计师们按照她的要求,使棕黑色和白色的长条纹装饰石板相间,像是一抹长发般顺滑地直落到落地窗的顶部。
半掩的窗帘捂得并不严实,透过缝隙她能看见阴沉的白色,单调的云层相较于昨天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已经多久没放晴了?”瑞躺在床上想。她睁着两只眼睛,正在感受被窝里的温暖。
这个梦对她来说逐渐从一开始的发人深省变成现如今的无聊透顶。但每次回想起自己在梦中那副矫揉造作的模样,瑞还是感到脸红发燥,心跳不止。尤其是梦中幻想那一段,再到梦见自己变成镜子并碎裂——这是什么鬼扯的梦?又想起自己当初还觉得梦是提醒自己的警钟,瑞突然感到很无语。
“烦心事太多了。”她踹了一下被子。
瑞慢吞吞地起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放在床的一角,挽头发的时候顺手拉紧了窗帘,最后坐在桌前。
桌子上简单地摆着几样化妆用具,镜子前的瑞边准备洗漱边打量现在的自己:野狼般的眼神,精巧的鼻子和嘴巴,齐肩的短发,温润的颈部下是干练地恰到好处的身材,配上大麦色的肤色。
瑞是个标准的诺克萨斯式美人——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比不过那个人。
她很快收拾好自己,给自己的头发随意地打个结,因为她很不习惯披头散发。她也没有忘记换回平时穿的衣服:一套恩德式的米黄色套裙,它有着宽松的袖口和束紧的腰身,让人看起来像个慵懒的家庭女仆或者雇工。
时钟告诉她现在的时间并不早,但也不是很晚,窗外依然寂静无声,偶尔有几只麻雀停在灰银色的地面上,随后静悄悄地飞离。
瑞摊开自己的日记本,准备把昨晚的份给补上,对她来说这可是项大工程,因为她要写得实在是太多了,还要尽可能地保持优雅的字体与全面详细的叙述,硬要说原因的话,瑞一定会回答说这是强迫症,而且丝毫不会引人怀疑。
“要从哪写起呢?”瑞自言自语道。她咬着笔头,回忆着昨晚的一切。
浮现在她记忆的边缘的,不是吵吵闹闹的琐事,是一场盛大到无以复加的宴会。她和一位堪称公主般尊贵而美丽的少女牵手共舞,两人的手都贴在对方的腰间,随着轻柔的音乐在舞池陶醉。
瑞穿的是少女为她挑选的白裙,就跟梦中的那款一模一样。她精心打扮了很久,就算如此,和少女面对面的时候她还是感到自卑。
仅仅是这样想着,瑞一只手托着下把,也忍不住情不自禁地用脚轻点着地板。
等到一曲终了,她依依不舍地和少女松开手,老实说,这种眷恋的感觉瑞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但是很快她还能体会到另一种感觉:名为嫉妒,这种感觉是她一直以来深有体会的老朋友。
一个模样高大的男孩无礼地闯入舞池,身后跟着三个跟他差不多样子的跟班。自以为完美登场的男孩打着响指,眼睛锐利地扫过整个舞池,盯上了她们。公主般柔美的少女面如冰霜地盯着他们,瑞则是差点没能按耐住自己教训他们一顿的冲动。
音乐变得舒缓而富有情调,这是两场舞曲之间的缓和。其他人都在一旁休憩聊天,不过靠近入场口的一些人都敏锐地发觉了这个在瑞看起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
有几个人都站起来向他们走过去,那时瑞都要高兴地以为男孩们要吃苦头了,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少女一直冷眼看着他们。
情节很快出现了反转,靠近的人们与其说是和男孩们普通地寒暄,在瑞看起来更像是低眉顺眼地打招呼。周围的人们撇过头悄声交谈,瑞仔细一听才明白男孩们的来头。
诺威尔家族,首都已经迎来了最新的权贵。
当权者们争势逐利尔虞我诈,每次的交锋总会诞生一批所谓的“权贵家族”,不过是一群如子凭母贵一样的小丑们。瑞当时不屑地想道。
接下来的事情让她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想法,男孩带着朋友贴近她们,自顾自地打起招呼自我介绍起来。语言堪称粗鲁无礼,瑞有时候觉得他们还带着改不掉的地方口音。
领头的男孩的名字是斯诺,左边两个人是男孩的弟弟,三个人都是诺克萨斯指挥部统帅贝顿·诺威尔的孩子,也是诺威尔家族的三个少爷。
另一边叫费蒙的那个男孩则一刻不停地盯着瑞旁边的少女发呆,就像个被美女迷住的小孩。
“我身边的朋友想跟你的朋友跳一曲,只是不知道她愿意是否给他这个荣幸。”斯诺对瑞说。
瑞很诧异,原本她以为这些人会直接略过她邀请身边的少女,毕竟他们似乎很是目中无人。这样的话瑞还有机会出来教训他们一下,让这些搞不清楚情况的孩子们知道黑色玫瑰里“执月”少女和基西拉家族的地位。
但是男孩突然绅士地向瑞发问打乱了她原本的设想。
瑞只记得费蒙的脸颊通红,自己正要装作委婉拒绝一样的架势,没想到还未开口说明,一旁的少女已经抢先一步作出回答。
少女转过头,她的眼神如冰霜般寒冷,用很久没用过的命令式语气让瑞先行离开,去外边休息。瑞觉得自己应该反驳几句,但是那个叫斯诺的少年面色平静地盯着她,一瞬间她明白了,反抗对她来说只能带来更难以接受的耻辱。
瑞被抛弃了,她只能这么认为。明明只隔了一晚,她除了记得自己拿起放在圆桌上的大衣孤独地离开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她一瞬间回过神来,面前的日记本还是空空如也,手上拿住的一支笔还悬在半空。瑞的眼神飘向落地窗外,门缝里涌进来的凉风撩动着肉色的窗帘,宛如拉开剧场里的大幕。
不对,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过令人震惊,而让她不得不忽视那时的事情。
她的眼睛里似乎腾起一团火,还有漫天的硝烟,瑞甚至还能闻到那股火药弥漫的刺激性味道。灾难爆发之快让瑞都难以反应,等到发现漫天的火光时人们已经如一团蚂蚁般了。
美丽的仙境变成了人间炼狱,地毯上翻滚的火焰沿着由洒落在地的花瓣铺成的路蔓延着。人们大吼大叫地奔跑,直到门口的木板着火倒在地上,撒在地上的酒也就成了最好的导火物。
讽刺啊,原来衣冠楚楚地宾客们乌压压一片从门口逃出,就像是慌张的逃犯。另一边休息的车夫们没有想到大火如此迅速,连控制受惊的马匹和龙蜥的时间都没有。所有人都在奔跑,瑞连挤进去都是靠蛮横的武力。
因为少女没有跑出来,这是瑞偶然察觉到的,或者说是直觉。按道理来说她本应该随着人流一起跑出去,而且有人曾在今早告诉她,在关键时刻并不需要保护少女的安危。
硬要说的话,还是强迫症。
再往后的事情就属于不该被记录的范畴了。瑞安静地合上笔记本,撩了撩耳边的头发。
她脑海里的回想匆匆掠过以后的场景,最终停留在崔法利士兵们配合着军队法师们进入宅邸的画面。那时火已经被扑灭,士兵们全副武装,胸前印有三个凹坑的黑铁铠甲在未散的烟雾里依然闪烁着寒光。
瑞在拐角偷偷注视着他们,至于他们逮捕了谁,处理了什么,瑞不得而知,也毫不关心。
遐想还在继续,但敲门声让瑞不得不放下托着下巴的手。
她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轻微拍了拍身上的衣服,最后才打开门。
艾尔莎站在门口,她看起来依然是那么地美丽,和公主一样,用她那红宝石般清澈明亮的双眼看着瑞。
“我还以为你还没有起床呢。”艾尔莎嘟起嘴说道。
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瑞能百分百确定这一事实。既然她们还能在这个地方重逢,在一起随意地生活着,那么一切都还未改变。
“只有德雷坎最懒的懒狗才会赖床。”瑞笑着回答说。这个笑话她此前讲过无数次,没有任何一次让她能像这次一样感到真正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