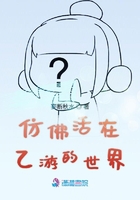车队避开了燕山,继续向北行驶。
草原上不再是一望无际的碧绿,有了平缓的山坡,间或有着零星的沙地,甚至黑岩和石块。
众人好好休息了一夜,再次启程时已经恢复了精神,走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也变得惬意起来。
“骨朵,熟悉前面的地形吗?”郢国公薛崇简问道。
“没有来过燕山。我曾跟随可汗东征西战,曾去过北面的室韦,却没有机会来过这里。”骨朵自豪说道。
望着极远之处的山峰,薛崇简听到了涓涓流水的声音。
沿着溪水逆流而上望去,那是一条从山峰流淌下来的小溪,清澈见底。
已经无需薛崇简安排,众人开始围着溪水畅饮了起来,拿出水囊灌满清水,拴在了自己的马背上。
工作量最大的是徐老翁,身边跟着十二三岁的孙子徐长明,一起用木桶盛满清水,以备做饭时用。
这些天,长檐车一直行驶在草原之上,没有道路的草原之上,特别费车轮,接连坏了数辆,不少的轻伤伤员只能骑马而行,舍弃了长檐车。
拉载着帐篷和粮食的工具车需要优先保障,因此,近百人的火兵反而是没有伤亡的保存最全的兵种。
守真、魏广宗、张皋凑在一起,一边灌满水囊,一边聊着。
“本是酒囊,却变成了水囊。”魏广宗叹道。
“多谢大哥舍了心爱之物,用酒水为我洗了伤口。”张皋歉意道。
守真知晓魏广宗最是贪杯,喜爱饮酒,说道:“等我们绕过契丹部落,到了室韦,那里就有西域商人带过去的葡萄酒。”
“无妨。兄弟的伤口最重要,我也就是心里痒痒而已,等到了室韦,一定抱着酒坛睡上一觉。”魏广宗数日没有打理脸面,络腮胡子渐起。
“我们绕道安东都护府回去,比之前的计划又要晚了数月。数月之后,回到神都洛阳,先给你准备一坛剑南烧春。”守真低声道。
张皋诧异道:“数月?需要绕道这么久?”
“到了室韦,我们需要向东穿越鲜卑山,穿山便需月余时间。”守真说道。
张皋听后,沉默不语,只是捂着自己骨折的胳膊,不知想些什么。
“广宗,你把这水囊给清风和明月送去,不能让突厥公主一直照顾他俩。”
魏广宗灌满水,嘿嘿笑道:“他俩才七八岁,不照顾他们,难道要他俩照顾公主?”
守真也露出奸笑。
这一路上,因为突厥公主的身份会受到特殊的待遇,这是必然的,因为公主才是两国和亲的关键。
也因此,清风和明月跟着混的伙食待遇要好一些。
并且,还省得守真费心一路上的照看。
魏广宗去送水囊。
守真看到武天姬等几位公主身边的侍女开始在溪水里洗脸,他也跟着洗了两把。
“要不,咱们等他们都上路出发后,在这里沐浴一下再走?”守真笑道。
数天奔波,他没有时间沐浴,如今清闲下来,觉得身体发痒,该休整一番了。
尤其是他的莲冠和发髻已经松松垮垮的歪了下来。
张皋附和道:“车队走得太慢,我们快马加鞭肯定能追上他们。”
两个人商议下来。
正在这时,充作扫尾殿后斥候的武延秀和亲兵纵马狂奔而来,并且大呼道:“快走!契丹人追上来了!快走!契丹人追上来了!”
离着二里地就听到了武延秀的呼喊声。
所有人都愣住。
守真大喊一声:“快上车!上马!”
顿时,每个人反应过来,一顿慌乱,各自上车上马。
他拉起张皋,将张皋扶上马,又将水囊放进马背上的包袱里,说道:“跟着广宗一起走,即便跑丢了,也有个伴相互照应。”
张皋持缰问道:“道长,你呢?”
“我也跟着你们一起走。你先去找广宗,我去问个明白。”守真拍了一下马背,让张皋先走。
慌乱之间,也没有了阵型,薛崇简和骨朵费了好半天的功夫才清点清楚车队里的每一个人。
这时,武延秀已经追了上来,来到跟前,勒马呼道:“契丹人追上来了,他们刚刚转过了山坡。”
“有多少人?”
“估算两千余骑兵。”
薛崇简急道:“还有多远?”
“如果没有发现我们,可能还有两个时辰追上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们,可能一个时辰就能追上来。”武延秀回道。
“我们走!”
“车队的速度太慢!想要逃命,可能需要都上马。”武延秀看了一眼走在最后面的工具车。
“那可是咱们的粮车。”薛崇简说道。
守真说道:“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粮食?”
薛崇简自知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叹道:“双马长檐车一律放弃,全都上马奔袭。”
薛风眠得令之后,马上纵马去通知车队,全部换骑战马。
来不及做出选择,车队再次扔下部分装备,轻装上阵,每个人一匹战马,策马而去。
为了不给契丹人留下战马,众人将富裕出来的战马也带走,一起上路。
阿史那果儿的马背上是明月,而清风则去了魏广宗的马背上。
徐老翁和孙子徐长明看着刚刚灌满的木桶,长吁短叹。
“不要哭!”徐老翁教训着孙子。
徐长明紧紧握着拳头,望着后方,眼里充满了恨意和泪水。
守真从工具车里挑出两个水囊,扔给徐老翁和徐长明,说道:“先上马,以后找机会报仇。”
爷孙二人只能装上水囊,纵马奔腾。
近五百人的车队变成了马队,每个人都会骑马,特别是从小长在马背上的突厥人,不论男女。
只是苦了那些受伤的勇士们,忍受着疾驰的颠簸和伤口的疼痛。
守真右臂有疾,左手持缰,跟随在魏广宗等人之后,一脸的汗水。
两个时辰后。
马队遇到一处水源。
薛崇简挥手勒马,说道:“这么赶路也不是办法,必须让战马有充足的体力。”
骨朵说道:“我们能坚持,战马也坚持不了太久,不如让它们休整一番。”
“人和马都休整,我就不信契丹人的马比咱们的马跑得还快。”武延秀说道。
“咱们骑得就是契丹的战马。”
守真叮嘱道:“先休息再说。这个时候,一匹战马也不能丢下,或许,它们就是我们逃命时的口粮。”
一席话说得众人沉默,即便从契丹骑兵的追杀之下逃脱,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么多人的吃喝,绝非是一匹战马能解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