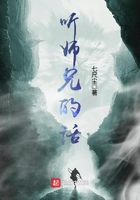“什么孽缘,大过年,兜头被泼一盆狗血,真是太让人伤感了。”我笑眯眯地拉着他的手抚了抚,“你醋了的样子挺好看的,再给朕醋一个呗。”
沈凤卓瞅了瞅搭在一起的爪子,火速把他自个儿的给抽回去了,咳嗽两声,道:“今天的书都念完了么?”
“那是自然。”我点了点头。
昭和元年春闱之后,朝局基本上初步安稳了,沈醉告老之后,我想着沈凤卓也要上殿听政,不如就让他代右相之职,也免得重新选人日后生出事端来。
我爹原先布下的暗棋,果然都很出色,除却方清颜从未踏出过雍京,其他的都是有学识有见识有阅历,性格干脆,办事利落,把个摇摇欲坠的朝堂扶得稳稳当当的。
我原本是觉着,上位者嘛,能兜得住下头的人便成了,学问什么的,真没必要跟新科状元比高下。
沈凤卓为此好生教育了我一顿,说眼下臣子们都忠心着,皇上偷些懒儿,倒也没什么。但以后呢,这些个臣子在任上年岁久了,难保不是第二个洛太师。不管哪朝新开,新帝提拔上来的臣子都是忠厚老实的,过不多久臣子们油滑了,皇上若还是老样子,还能拿捏地住么?
我一琢磨,觉得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朝堂上的事儿,跟滟澜湖其实挺像的,我娘当初也确实是有着手底下的人胡闹,但她罗刹之名早年就传遍江湖,手中妖刀更是让人闻风丧胆,再如何,她都兜得住。
我若一直是这般半桶水晃荡着,估摸着很快就要兜不住了。
于是听了沈凤卓的话,收了懒散的小心思,准备念书。
眼下教我念书的,已经是第三个师傅了。来教我念书的,都是大隐隐于市的鸿儒,那姿态都是清雅的,那气质都是孤冷的,那学问都是深不可测的。沈凤卓为了请他们出山,很是花了些心思,珍奇的书画送了,茅庐也顾了三四回,还将朕求知若渴的心情转达了,磨磨蹭蹭耗了许久。
那时候我看着沈凤卓,觉得在内心深处,对于他的情感,十分别致。
他在劝我念书这事儿上,比我娘我爹都要坚持得多,比请来的师傅对我期许还要多。
我知道他是好心。
立在皇权之巅,万民的生杀,尽在掌中。若是我昏蒙一分,江山社稷便多一分不稳。他是我爹的暗棋之中,唯一一个与我亲近的辅棋。
我虽然仍是每日睡到自然醒,但白日念书,饭后练武,倒比之前在滟澜湖之时,长进了无数倍。
沈凤卓笑了笑,眼中颇多欣慰,“今日先生与我说,他没什么可以教你了。”
“这算是夸奖么?”我歪了歪头,“你还要再去请另一个先生么?”
“不必了。”沈凤卓笑道,“皇上,年后开朝,你可以亲政了。”
我挠了挠头,有些不解:“朕不是一直在亲政么?”
“臣的意思是。”沈凤卓摇了摇头,淡淡道,“臣可以退回后宫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皱了皱眉,“你虽是中宫皇夫,却也是朕的臣子,你既有能力任右相,又何必要退回后宫?”
沈凤卓笑了一下,握住我的手道:“这不是北狄的战神要来了嘛,总要有人陪他解闷儿吧?”
“那你也不能陪他解闷啊。”我郁郁道。
“若是只有云战神,那自然不必专门陪着。”沈凤卓悠悠叹了口气,“就怕,不止这一个啊。”
我眨了眨眼睛,愣了:“你是说……”
“没错。”沈凤卓点了点头,“皇上还是早作准备吧。”
“皇夫。”我淡定道,“你说朕现在逊位还来得及么?”
沈凤卓眉眼轻挑:“嗯?皇上说什么,臣没听清楚。”
“朕什么都没说!”我坚定地摇头。
西夷,粹取宫。
殿内烛光摇曳,一大一小两个身影,静静坐在桌边,一人一把小刀,正在雕萝卜。
杜清洄偶一抬头,看一眼对面的小人儿,只见那孩子眉眼间透着少见的认真,一刀一刀落得十分稳健。
这孩子,怎么就爱好了这个呢,真愁人。杜清洄心思轻轻一动,手上的萝卜就扭扭一歪。
明黄衣衫的孩子毫无察觉,仍是专注地忙碌着。
杜清洄瞧在眼里,默默在心里掀了一通桌子。据说摄政王前阵子学那些小年轻去郊外骑马,结果那马不知道怎的就惊着了,把人摔了。
就那会儿,摄政王摔着的不是腿,而是脑袋吧?
知不知道什么叫玩物丧志?天子年幼,本就心性不定,你还惯着他由着他,那不是坏事儿么?琴棋书画你随便选一样,哪怕学得不成样子,好歹也能陶冶情操啊。
这雕萝卜有什么意思啊?
少年天子忙活一阵,终于完成了手中的物件,欢天喜地地抬起头来:“呼,小皇叔,你雕的是什么呀?”
杜清洄默默地将手中的萝卜递过去。
“哎呀。”少年天子惊喜道,“是个小兔子啊,雕的很好呀。”
杜清洄嘴角抽了抽,默默地坐着没有说话。这必须得好呀,跟在师父身边儿的时候,见着最多的就是兔子啊。
这萝卜显不出手艺来,本王出师的时候用石头雕给师父的那个,才叫栩栩如生呢。
杜清洄沉默少言,小皇帝也知道他的脾性,自顾自兴高采烈道:“小皇叔,这个可以送给侄儿么?”
小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纯良的跟小兔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