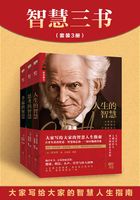清晨,雾霭萦绕酉水河面。河水、渔船在雾中时隐时现,不时有淡淡的炊烟从渔船的篷盖缝隙窜出,随风向远处天空弥漫。
粟麦登上一条船。昨天快擦黑儿的时候,她在窗口看见二茨的尸体被人抬上了这条船,随后往两岔溪方向驶去。
这是一条老机船,柴油机漏油还是怎么的,老远便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粟麦认得船的主人,她喊了一声:“棚伯。”
棚伯从机舱钻出来,应声道:“麦子啊,何事这么早?”粟麦裹紧大衣,声音瑟瑟发抖地说:“送我去一个地方。”
“么子地方?”
“你昨夜去过的地方。”
“哦嗬,我昨夜去过很多地方,还到过我年轻时到过的汉口。不晓得你讲的是哪里。”
“那是你梦里去的地方,我不去。我要去的地方是你昨天最后一趟生意去的地方,夜里9点多钟回来你就再没动过,记得起啵?”
“原来你一直都在监视我?麦子,你怎么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心机忒重,喜欢盯人。”
“你说去还是不去?”
“去哪里?”
“去你昨天送死人的地方。”
“呸呸呸,妹娃子口无遮拦,大清早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是你逼我说的。我不信这些,要不吉利,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
“越发胡说。再等两个人,我去就是。”
“别等,我包了你的船,单送我一个人,我要赶那里的出殡。”
“麦子,那人跟你家沾亲?”
“……”粟麦没有作声,只催促道,“快开船吧。”
棚伯开船了,发动机“突突突”尖叫了一阵之后,船到了河中间,深水隔音,发动机声音小了一些,但却将声音传送得更远了,惊起了栖息在两岸的许多白鹭,三三两两飞到河里来,打两三个转,又飞回温暖的巢洞中去了。
粟麦立在船头,凛冽的河风裹挟、抽打着她虚弱的身体。很厚的大衣也挡不住寒冷刺骨,痛到了心窝里,心窝痛呛鼻子,粟麦的鼻子酸溜溜的,一会儿,眼泪和鼻涕便迎风流了下来。
棚伯在机舱里看不见粟麦在迎风流泪,他在想,这妹娃子看完出殡还会原路回来的,干脆等她下船,就在两岔溪生火做早饭,慢慢地等她。这一来二去,看她给多少包船钱,别开口问她要,随她自己吧,一定比自己开口要的数更多。
粟麦流了一会儿泪就适应了。起初心窝子里和骨头里面的生猛锐痛这会子也起了变化,像喝了一口老酒,五脏六腑从里到外都热辣辣的刺痛,这种痛和刚才的痛完全不一样,正所谓物极必反,痛过了头才会觉得舒服,冷极了反而觉得温暖。以风洗心洗面洗肉洗骨的感受,粟麦还是头次体验,这种锋利和痛快使她觉得心里积压的郁闷去了许多,于是,她向空中送去一声呐喊:“你干吗要死蔼—”
粟麦从渡口上了公路,再穿过公路便到了棚伯讲的八家村寨。八家村过去是一个上百户的大寨子,寨子里的狗是出名的凶。寨子此刻还拢着浓浓的晨雾,很少有人走动。粟麦不敢大模大样进寨,只在外围探头探脑。村头的小卖部开门着,粟麦闪身进去。
守店的小伙子叫山囤,听说来人买鞭炮,便没心没肺地说,是去二茨家吊丧吗?粟麦这才知道死者真叫二茨。她的脸很快被真实的阴影笼罩,赶紧点了点头。
她掏出一张百元票子,说尽着钱买。山囤很意外,没想到她出手这么大方,心想,100元,大炮都买得起五六饼,炸起来要响二十分钟,真过瘾,二茨死得真值。
山囤一边拿货一边对粟麦说:“先讲在头里,你要是公家报销,我可没有发票。”
粟麦说:“不要发票。不过我想请你帮个忙。”
山囤说:“你说。”
粟麦说:“你看我是一女的,胆子也小,不敢点这鞭炮,求你随我到主人家,帮我把炮点了,行吗?”
“嗨,这有什么不行,我巴不得把这些炮都点了,过一把足足的瘾。”山囤嘿嘿笑,领头提着鞭炮就往二茨家走去。粟麦悄悄嘘了一口气,心想再不用担心找不到路、招架不了村里的恶狗了。一会儿,山囤来到一家院场,将鞭炮点着,等到主人家迎出来,粟麦早闪身在篱笆外面的柚子树后,山囤只顾过瘾,早忘了她,而主人家只当是商店老板发慈悲,前来吊唁放许多鞭炮。
粟麦站的这个地方最是隐蔽,她能看清院场里的一切,而外人却看不到她。
她看见二茨被人从镇上抬回来之后,没有被放进堂屋,而是放在堂屋门外,两根高板凳横搁的一块门板上,门板靠里的一头,凳子底下点了一盏长明灯,说明那是二茨的头,长明灯放在一个大瓦罐里,以防被风扑灭。据说像二茨这样的凶死者,又没过三十六岁,属少年亡,是凶上加凶,除了尸体不能进宅,还要以白布裹尸,犁头压胸,草纸盖面。由于不能当天入殓,又恐亡人迟迟不入殓会躺在灵床上数屋顶上的椽子,于家宅不利,于是将其头朝北,脚朝南停放,以免他看见房檐屋顶。
抬二茨回来的几个农民工是工程队派来的,但他们只负责送二茨遗体,不能给二茨家里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没得到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村里人谁也不愿帮忙料理丧事,二茨父母年老,不能做主,哭巴巴地求村干部帮忙到镇上找包工头协商赔偿金和丧葬费的事宜,谁知回来告知,包工头早就逃跑了,建筑队也作鸟兽散,根本不知道找谁解决这件事。二茨有一个姐姐一个哥,但姐夫和哥都在外面打工,一时三刻赶不回来,姐姐和嫂子商量,想在村里找一帮人上镇上闹闹去,无奈村里总共凑不足二三十个人,而且还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些人如今被称作留守人员,平日连农活都很少干,山地和田园都荒芜了,人心也早就荒芜了,谁还愿意凑这个热闹,出这个头?干脆都关了门,闭了户,一任死者家属哭天抢地,哭天抹泪。
二茨媳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张特别典型的瘦脸和一双十分精明的眼睛,听到门外鞭炮响时,她赶紧披麻戴孝地起身出来迎接,起初她以为是二茨做工的工程老板来吊唁,拿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希望通过撒泼寻死的手段,讨到一笔抚恤金,看清是商店的老板山囤,想起一场如意算盘落空,双脚就地一顿,立即倒身在地,长声短喊地哭得死去活来,如同泪人一般,叫人看了好不伤心。
粟麦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刚才也忘了问山囤,只见她头上戴着一朵雪白的棉花,便在心里叫她棉花。棉花的哭声很大,盖过鞭炮声,不像粟麦天生中气不足,高声喊一嗓子也会气喘吁吁。 鞭炮声一直响了二十多分钟,她也就哭了二十多分钟,真难为她哭得又大声又持久。 鞭炮一停,棉花立刻爬起身来,飞快地抹抹眼泪,擦擦鼻子,上前对商店小伙子说:“哎呀,劳驾老弟,放了这么多鞭炮,让你破费,帮我二茨绷面子,快,快到隔壁坐坐,喝碗米酒暖暖身子。”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山囤就走,全然没了方才号啕大哭带来的抽泣,甚至连呼吸也很均匀,语调亲切,态度极自然。粟麦一见她这模样,竟惊得张口无法合拢了。
安排好客人坐下,棉花拎来酒壶,给山囤斟满酒:“大清早的,辛苦,你慢慢喝呀。”说完,回头看见娘家帮忙合匣子的人来了,想起没钱,请不动村里人,只好央求娘屋人来帮忙埋二茨,心里那叫一个苦,转过身,一声长且高响的呼喊“二茨我可怜的夫呀——”又扯开喉咙放声痛哭起来。看得粟麦目瞪口呆,心想,她怎么说哭就哭,说停就停,感情的起伏变化也太快太夸张了吧。粟麦有些纳闷,难道她的哭是装模作样?虚情假意?这样一想,粟麦再看一眼躺在门板上的二茨,心里的感觉大不一样了,想着他的悲惨命运,望着眼前凄凉景象,心头一酸,眼泪哗地流淌下来。
几个帮忙料理丧事的娘舅和亲戚,搬了梯子出来,架在房前,准备抽堂屋楼板给二茨合匣子。楼板一寸厚,两尺宽,七尺长,一共抽了九块下来,整个堂屋的楼板便差不多抽空了。这种情形是非常凄凉的,因此,这个时候,死者亲人都要回避,给二茨合匣子的只能是娘家外姓人。只见棉花一人跪在地上,边哭边诉边唱,音调时起时伏,抑扬顿挫,极富韵律。哭诉的全是一些凄惨悲凉之词:“二茨呀我的郎,一见你睡在屋檐下我就血奔心,任我骂你打你千呼万唤你都不做声。有你在外撑着我不离堂屋火坑,如今你一撒手好比是挖断大树根。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抽空了房楼砧,风吹雨打你看不见我们受苦,我们只见寒冬不见春。以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来如何撑?明朝你的儿女喊谁一声爹呀?来年谁送他们上学谁帮他们盘亲?你一走家里没了主心骨,就像这房梁断了哪来的四两钉子钉。二茨呀你不能走,你得把话给我说明白,你究竟为何要走,你的心怎么这么狠——”
这词明显是她临时现编的,但却编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她这是哭给娘家人听的,哭得泪流满脸,情真意切,哀声怜人。于是,在她的哭声中,那边院场响起了钉锤声,一听那下力的“当当”响,就知道是四寸长的铁钉在钉匣子。哭声,响音,高音、低音、沙哑的、尖锐的,此起彼伏,交融汇合,听起来尤为悲凉。
粟麦站在离院不远的一棵老柚子树下,像中了魔法似的,两眼直瞪着被棉花哭红的天空,这天上的红霞预示着一个好天气,却不能预示一个人的好命运。棉花哭着哭着开始用一双手掌拍地,青石板铺的院场坪被她拍得“啪啪”响,如声声鼓点敲打着人心,敲打着寂静的村寨,向群山包围的空间四处扩散。
粟麦渐渐不能自控地浑身发抖,她终于明白棉花这是纯粹的伤心,为着伤心而歌,称之为挽歌,是世界上最凄凉最动听的声音。
粟麦继续听她唱下去,她接着唱的是《哭四季》,歌词照样是现编的,只是唱腔变了,变成了花花腔,高音,悲戚,直抒胸臆,苍凉无比。
春日里来妹送郎,
一送送到大路旁。
打工挣钱养家小,
口口声声叮嘱郎。
夏日里来妹想郎,
想郎想得情意长。
只望七七鹊桥通,
好比织女盼牛郎。
粟麦根据她所唱的歌词,想象出一幅幅活动的画面,那些画面令人无比伤感,却又无比美丽。
棉花,你太了不起了,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聪明绝伦的女子,我也没想到你和你的二茨有着这样忧伤的爱情……我今日穿云渡水而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听你唱歌,唱挽歌,面对你的美丽,我的心情十分忧伤,人也变得无比憔悴,今生今世,我欠下你的血债无法偿还……
粟麦的喉咙哽咽。她湿润的眼眶流出一颗泪,一颗较大明亮的泪。泪沿着她深陷的眼窝,苍白的脸颊,流到她挺直的鼻翼,再往下,就像流星划过长空,倏地一闪掉进万丈深渊。她跪在冰冷的地上,浑身筋酸骨痛,难受得很。可是更难受的是她的心,她心窝里被刺进了一把刀,握刀的人就是棉花,棉花用她的摧心辣手转动着刀把,每转一圈,粟麦就死了一回。棉花坚持那样固执地转动下去,粟麦最后连身子都腐烂在土里,一动不动,成为一棵斑斓的蘑菇。
棉花以十分投入的情感唱出无比忧伤、凄凉的曲调。
冬日里来妹看郎,
我郎停尸门板上。
几块楼板合匣子,
一块白布做衣裳。
我郎年纪三十二,
人人骂你少年亡。
合口匣子把你埋,
草草葬在乱坟岗。
人家夫妻爱到老,
我俩孤影守空房。
井里有水缸里空,
缺你这根房顶梁。
儿多母苦日子长,
身上寒冷少衣裳。
家中缺柴又无米,
三个娃娃哭断肠……
棉花其实是在哭自己,想自己人生中的苦楚,还有未来一生中的难处,这是借哭丧宣泄自己的悲苦,既哭了二茨,也哭了自己,是实实在在的感情流露。棉花哭到令人伤心惨目,摧人肺腑地步,她的手掌拍出了鲜血,一个个血手印重叠在一起,所有钉匣子的男人听着看着都哭了,有的号啕大哭,有的泣不成声。
按照由来以久的民风民俗习惯,未亡人哭亡者,是不兴劝慰的,必须由着她哭,或有事打断她的哭声。看看时辰到了,匣子也合好了,领头的娘屋人大声问棉花:“买井水了没有?”
棉花正哭着,忽听得人问话,哭声戛然而止,连忙大声答应:“买了。”
“谢土地公公没有?”
“也谢了。”
“那,烧买路钱了没?”
“还没呢。”
“那还不快去。许多的事情没料理,哪个帮你?由得你哭?”
这是一种变相的劝慰,是作为娘家人于心不忍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了支走亡者亲人,打发亡者上路的一个借口。
棉花连忙起身到村里各路口烧纸去了,这里帮忙的人连忙每人含一口烧酒,这酒不能咽下,是避邪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含了烧酒的人不用说话,一切只要听老司的吩咐就行。
老司道法高深,他含一口烧酒,照着二茨面门喷去,大喊一声“起”,四个青壮年便抓起二茨身下的千金带(亡人衾褥下的白布带)和垫褥四只角,抬起二茨往合好的匣子里先脚后头地放进去,匣子里也撒了雄黄喷了酒,就在青壮年闪开的时候。
二茨终于入殓了。老司拿袍子一角扇风,扇去盖在二茨脸上的草纸,以防草纸盖脸,来生变成瞎子。老司喊:“盖棺——”早有准备的人马上将盖子合上,与此同时,老司将一些属于金木水火土之类的镇邪之物丢进匣子内,动作之快犹如闪电。镇物放妥后,给亡人去掉绊脚丝,以便让亡人在阴间走路,同时棺内空隙用灰包填严实,以防尸体在出殡时移位。做完这一切,抡锤的人便将四寸铁钉照着匣子四角钉下去。
“走——起——亡人上路,生人心安,合宅平安——”
老司一声喊走,抬丧的飞快抬动匣子,拔腿就走,生怕误了时辰。一人抱着长明灯在前面引路,只见他脚步如飞,灯却不会被风扇灭,一步一步都是力道,而且灯芯越跳越闪,越闪越亮,预示亡者的阴间路也将越走越亮堂。
这时,棉花烧完买路钱回来,发现出殡的人已经翻过山垭,只见她一脚踹开厢房门,将一大两小仨孩子从房里扯将出来,顾不得什么忌讳不忌讳,牵起一对双胞胎儿子的手,高声喊着:“儿啊,快跟娘走,送送你爹——”
两个儿子才四岁,还不懂得悲伤,看见七岁的姐姐在哭,也就哭,娘儿四个一路跌跌撞撞追着赶着,哭着喊着一路上了坡垭。
二茨的墓在乱葬岗。棺木入土之前,老司命人把纸钱、树枝、杂草统统拢来丢在墓中烧,接着,将一只活公鸡杀伤一刀,丢进墓中,让它在火中蹦跳至气绝取出,然后在墓的四角和正中放上雄黄朱砂,最后撒下五谷,预备沉棺于墓中埋葬。
“慢着——”
随着一声声嘶力竭的高喊,棉花带着三个儿女冲上垭来。
“让我儿来摔瓦罐,挖动灵前三锄土!”
看到仨孩子和只晓得哭的女人,老司没说什么,提起那个装灯盏的瓦罐子看着两个男孩说:“哪个是老大?”
棉花将左手边的儿子往前一推,这个比弟弟早出世几分钟的男孩接过瓦罐,紧紧抱在身上。
“别抱着呀,摔了它!”老司喊。
“儿啊,听师傅的话,把罐子摔烂起来。”
棉花抓着儿子的左手,替他高高举起瓦罐子,一摔甩在泥地上,不料那罐结实,竟然没摔破。老二见哥哥没本事,他几步走上前,想捡起那罐再摔一次,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抬丧的人见状,赶紧就近上前一脚踩烂了那只瓦罐。好险,老司刚才心里一阵发虚,真怕那孩子捡起罐再摔一次。大家伙儿也松了一口气。乡里风俗,瓦罐子是不能摔两次的,摔两次是兆头,预示家里接着还有人死。
老司凝视那罐片刻,表面是一种漠然,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一声不响地走到罗盘指定的位置,施展空手道法力,凌空劈下一根树枝,以枝代剑将事先备好的符咒、草结穿在剑刃,定在墓中心位置。他宣布:“赶紧落井。”
他说:“小辈可以放声大哭,下葬后就不能再哭了。”
于是,由棉花带头儿,跪着呼天抢地,三个孩子也跟着大哭,一时间悲声惊天,哀痛动地,让人不忍卒听。
要盖土时,旁人谁也不肯掩这第一捧土。老司唱到:人死了,入匣了,埋土了,孝子快来挖动灵前三锄土吧。
“来,孝子跪在这里来。”老司吩咐,抬丧的人便过来提起刚才摔罐的孝子,令其跪在匣子盖上,教他冲着其父亲的头部喊三声爹,挖三锄土。喊一声,挖一锄,将土盖在匣子上。随着孝子的哭喊声,老司也咿咿呀呀地唱道:“棺材入井了,孝子挖土了,亡者真去了,不能回阳了,挖一锄,一声喊,挖两锄,两声悲,挖三锄,三声嚎……这三锄,一锄代表天,一锄代表地,还有一锄代表孝子心。”突然,老司大声问道:“是个什么心?”这时,口里含着烧酒的人,都把一口热酒喷到井里,异口同声答道:“是孝心!”老司又唱:“这三声,一声惊破天,一声震动地,还有一声感肺腑,人人听了泪淋淋。孝子喊了这三声,心裂了,手软了,无力了……帮忙的人说怎么办?”
“孝子请起——”
众人又是异口同声。大家一拥而上,由两个人将孝子拉开,其余人拿起工具,挖的挖,刨的刨,都争着为孝子代劳,很快将坟堆好。
二茨的丧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真正的白丧事,仪式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