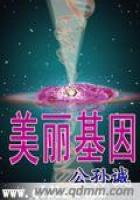那还用说,她师父自然是个通透的人,柳寅月哧他一声,再不理他。
行风也不说话了,两人沉默间,只见他突然将手中的长剑抽了出来,轻轻朝它哈了哈气,好似在照顾一个宝贝一样,掀起一片衣角便开始擦拭。
柳寅月顾自喝着茶水,又啃了几口白面馒头,偶尔看着行风低头试剑的模样,她有些纠结,对于昨晚的事情,她可是有好多问题想问,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不多时,她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许是终于下定了决心,她试探问道:“行风,你认识殷长云吗?”
行风抬眼:“你说卧梁公子殷长云?这谁不认识?”
柳寅月又道:“我是说……你和他认识吗?”
……
“不认识啊。”行风手中动作一滞,他抬头一笑,又继续擦拭起那把已经锃亮的剑,反问道:“他不是应该是你师兄吗?怎么了,突然问这个?”
不认识?
柳寅月眼神复杂,她真是看不透眼前的这个少年。如果他真不认识殷长云,那玉佩是哪里来的?但若是他认识,那他为何要谎称自己与殷长云素不相识?
行风道:“怎么了吗?”
“无事,只是想打听一下师兄当年下山之后的消息罢了。”
行风“哦”一声,嘴角带着笑意,他终于将剑放回了剑鞘中,正了正衣襟,“那你可问对人了,这事儿我可了解得不少。”
柳寅月朝他投去疑惑的眼光,“此话怎讲?”
话落,她眼神落在了行风脖颈处的一道红痕上,那红痕印记极为细浅,不像是指甲所划,亦不像利剑所伤,倒像是什么小而锋利的暗器,应当是昨晚与他交手之人所致。
若不是方才她留心看了一眼,这伤口,绝不会被人轻易发现。
行风丝毫没注意到少女在他脖颈处一扫而过的目光,他顾自拿了个大白面馒头,又替自己倒了一杯水,待做好了这些,他好似终于要开始讲了……
“卧梁公子殷长云么,惊才风逸,文武双全,当得上举世无双。”
“为什么呢?”
“因为……”
行风一顿,看着柳寅月一脸不知所谓的模样,他不禁扶额,倒是忘了,这姑娘对山下的消息可谓是闭目塞听,能听懂才怪了。
柳寅月不解道:“为何……你们要叫我师兄"卧梁公子"?”
“这个么……”行风想了想继续道,“传言殷长云轻功了得,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额,十人之中,八人皆曾与他于屋檐相逢,遂,卧梁这个称号就这么来了。”
柳寅月点了点头,他师兄曾在山上时确实是专习轻功的,下了山,常卧梁上,不甚奇怪。
行风又道:“不过呢,一般来说,卧梁之人吧,多半是盗,干的是见不得光的勾当。但殷长云不是,可他又确实是总歇在梁上,于是又被冠以了"公子"一称。”
说罢,他咬了一口馒头,看了看柳寅月一脸呆滞的模样,也不继续说了,正等着她半知未解的下一个问题。
“我师兄还活着吗?”
“什么?”行风咳了一咳,他瞪大着眼睛正看着柳寅月,这姑娘怎的一问就是如此刁钻的问题,殷长云死没死,他怎么会知道。
柳寅月眼神坚定,她又问:“我师兄,他还活着吗?”
行风勾了勾嘴角,只见他又为自己倒了一杯茶,他神秘道:“你若信他没死,他便没死。”
!
闻言,柳寅月本还激动了一下,她以为是行风知道些什么消息,还欲再追问他此话何意,一声戏谑的男声便传了来:
“这位兄台可别说笑了,卧梁公子不是早在三年前就死在"起云剑"手中了么。”
来者书生装扮,着一袭蓝色长袍,围有白色狐裘。极为亮眼的是他脖颈处挂着的一枚镶玉铜钱,应当是护身符之类的物件。少年生得唇红齿白,容貌是极好,立在这满是武者的驿站中,显得格格不入。
身后的小厮身材矮小,带着一顶土色貂帽,他颔着首,时不时抬起的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望着二人,显得有些“精”。
柳寅月眼神闪了闪,她不语,朝着那书生只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行风丝毫不给人家面子,他突然一个仰身,往身后的墙面一靠,两腿往桌上一搁,双手环着,撇了撇那书生道:“你怎的知道,殷长云就一定死了呢?”
书生闻言,丝毫不怒行风无礼,他依然含着笑,与他对视道:“难道兄台你不知道吗?”
柳寅月不发一言,她望着这二人,不禁有些怀疑他们是不是相识,怎的感觉空气里好似弥漫着杀气。
“启程吧,今日还要翻越东夷山呢。”
柳寅月见气氛不对,拿起弯刀便准备要走,她算是看清楚了,师兄究竟有没有死,根本没人知道。
至于行风,尽管他身上有许多秘密,但也无法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管他昨晚与谁打斗,她也不想再耽误时间,总之,无论如何,当下去到庐州城是首要的,等过了东夷山,她自会去寻找答案。
“姑娘,你也要上东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