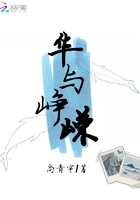木头碎片、桌子角、酒壶、撕裂的窗户纸,随着一个锦衣公子一起哗啦啦从酒楼二层的窗口灌入满是往来行人的巷子。
尖叫声顷刻间此起彼伏,摔在路中央的人块头还挺大的,身高腿长,二十出头的样子,在一堆破烂间挣扎了几下,几欲起身。
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破坏就此结束时,围在废木堆周围的人头顶一凉,感觉有风从天而降。
最先抬头的人看到那个坏掉的窗口处又飞下来一个红直?白裤子黑长靴的幻影,最后那些反应过来的人看到的是又一个狠角色挥着拳头从上头扑下来,朝着地上的年轻人脸上揍。
“魏公子!”这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又抬起头,看到窗前站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握着手绢哭哭啼啼地往下喊。
大家又都觉得自己好像听懂了什么,再一低头看着那位先飞出来的公子,确实是他们太康城内说出“宁可天下美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美人”的风流之最,魏国公老来嫡子——魏承文。
魏国公子息不厚,早年有一女,便是如今后宫之主,魏贵妃。本来无望香火的魏国公,没想到老来得子,国公府上下欢喜了整整一年,散了不少钱财,为这孩子积德。
这孩子就是小了姐姐二十一岁的魏承文。
世家里自幼习文弄武长大的魏承文也不是好欺负的,咬着牙,忍痛平地打了一个滚,避开了那一生风拳。手掌触地,接力翻身还未站稳,红袍人又一腿自上而下劈来。
娘的,腿真长。
魏承文转了转肩膀,后背生疼,只是对手从来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只能硬着头皮抬高了胳膊十字挡挡下。
红袍没有魏承文高,却也不矮,一腿劈下去,魏承文没撑住又跪了下去。
红袍下盘稳当,立在地上纹丝不动,这时大家才看清了这生风虎一般的角色竟然是个女子,空中飞扬的马尾落下,搭在她的肩上,露出了一张生动的怒容。
众人心里了然,就说嘛,这城里敢这么打魏公子的也没有几个人,原来是康念公主以前的那个女护卫——解蔷。
其中恩怨说起来,还与当年的后宫有关。
康念是邱家的皇后所出,魏承文的家教里,从来都是教养他与邱家为敌的观念,两个孩子年纪差了三岁,不多不少,刚好踩在同龄人的边缘。
当年带头欺负康念的人,便是魏承文。
而后,解蔷成了康念的护卫,长大后的公主开始翻起了旧账,简直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二人配合的天衣无缝,魏承文这些年吃了不少瘪。
如今解蔷继任北旗禁军统领已经两年了,已经很少这般接地气的出现在百姓的视野里了,一个两个看着热闹,再危险都不舍得走开,眼睛擦得雪亮,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了与这两人相关的,一星半点的好戏。
只可惜有人捧场,场不愿开了。
魏承文借解蔷收腿之势,手臂一推,自己后跳三步开外,轻车熟路的翻上了酒楼对面的一面矮墙,消失在大家眼中。
而解蔷也不负众望,跟着翻了过去,乘胜追击。
“魏小公子怎么又惹着公主了?”看过不少好戏的太康城老油条提了一嘴。
旁人也唏嘘:“这都打了多少年了,解蔷小护卫都打成北旗大统领了,还没完没了的。”
一场注定要惊动天子的冲突就这样匆匆落幕,后续如何,还得靠坊间的似真似假的传闻来填补了。
八月初一。
解府的大门前,围观者们热热闹闹指指点点。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北旗禁军统领解蔷,于禁中鞠躬尽瘁,治军有方......”
高大的女郎穿着淡淡棕绿色圆领常服,衣袍撂至膝盖,露出灰色骑兵长裤,马鞭挂在腰胯的皮带上,脚踩着黑皮马靴,一副准备跑马的装束。
单膝跪在宣旨太监身前,垂首听旨。
“于闺中恪守孝悌,纯良贤淑,太后与朕躬闻之甚悦。明王青年才俊,已到适婚之龄,二人郎才女貌,桃花双树......”
这一段,没有一个词是描述她的,解蔷心里活跃得很,却没法说出来。说出来,只一个“惨”字而已,没想到上个月和魏承文的那一场巷陌追击引发了皇上、贵妃、太后三人的大怒。
本就看不惯邱家的魏贵妃,正好出手,替弟弟出了一口气,又一连打压了公主和明王府。
最毒不过宫里妇,封喉一线叩还恩。
“钦天监得佳日八月初十,七杀破军,二星宫中独坐......朕愿成人之美,赐予良缘。钦此。”
宣旨太监将那一张纹着神龙的帛布卷轴缓缓合上,微微弯下腰,重地转交到解蔷的手上。
解蔷长臂抬过头顶,白钢鎏金绑缚小臂袖口,解蔷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接过这一道御赐皇婚。
朗声道:“臣解蔷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似排练过许多次一样,解府人人沉着自持,正门大开着,所有人各司其职,一切过程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老内监扬手,雕龙画凤的喜棍搭着大红宝箱流水般涌进府内。
下一刻旁观众人哗然一片,再之后,满城皆知。
.
各个大小茶楼里五花八门的论调皆围绕着这一场意想不到的皇家婚礼——
“说实话,想娶解蔷的人肯定不少,只不过不敢说出口罢了......”
“想娶是一码,敢娶是一码,能娶是一码,咱一码归一码。”
三五街坊邻里聚在一桌,互相聊着当下的热门话题,引得旁人也忍不住侧耳探听。
“这真疼女儿的,也不会为了这泼天富贵,把人嫁那明王府去!”
别看市井里谁都看不上这明王府,正得圣眷呢,一般人还真就高攀不起。
“这都多少年了?当初一个个等着当明王妃的大家闺秀,现在孩子都有了呢。”
“七年了呢,明王今年也有二十五了——谁家乐意让姑娘陪他耗?今早出门我看见那一位位大人,那笑得啊,还以为他家女儿得了一门好亲事似的!”
“不用嫁给明王了,好亲事可不就成了一半了么!”
有人问:“明王府怎么了?”
“新来的吧?”最开始提明王府的那个汉子接话,“明王府那位,这儿有问题的。”
说罢,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那个新来的吃惊极了:“啊——”
汉子又说:“以前街头巷陌都不敢谈的,生怕被他听去了,又发病,那不是得上头找上门来?”
“说,说都说不得?”
“现在能说了,你呀,赶上好时候了。”
另一个老茶客还是有些后怕,转开了话题:“要不是皇上把他家红得发紫的大统领嫁给了自家疼爱的皇侄,我还真信了那些坊间谣传。”
“不是都说这里面有贵妃娘娘的手笔吗?没准就是了呢?”
一旁听着的人凑进来插了一句:“什么谣言?”
“哎——不可说了不可说了!”大家忙摆手,说不能传谣,“这个是真的不可说了!”
阴差阳错,对此事议论纷纷的茶楼闲客们,说中了真像的几块碎片。
.
解府送走了宫里的送聘队伍,掩上了该掩上的门。一家三口坐在正厅里,解夫人和解老爷的脸阴沉沉、哀戚戚的。
解蔷靠坐在下位的大椅子上,一只脚踩着就近的椅子脚,一只脚踩在椅子面上曲着膝盖,手上握着一只大梨,靠在膝盖上旁若无人地咬,与接旨时的稳重内敛完全不像。
忽然解蔷下意识偏过头,一只橘子擦脸过去,狠狠地砸在梨花椅扶手上。
伺候的下人们大气不敢出,橘子在地上滚了几圈也没人敢上前收拾。
“我说的什么?你说我跟你说过什么?”解老爷正值壮年,一嗓子吼出来底气特别足,不喘气也不坐下,在堂前站得直挺挺的,父女俩的身形这一打眼还挺像。
“您说再与公主去对付魏承文,魏家迟早会对付我的。”解蔷老老实实回答,不敢多言。
解夫人捂着胸口,躺在椅子里,嘴里呢喃:“报应啊......”
大堂里的氛围有些沉闷,解蔷揣测着父亲的脸色,说得小心翼翼:“咱也不亏不是?您二位的侯爵和诰命就快下来了,现在若悔婚便是抗旨谋逆。反正,过几天你们俩也是皇亲国戚了,看开些吧,都是有地位的人了。”
“别人会怎么说我们?说解老头就是个卖女求荣的老货!”解老爷掩面,手揪着裤腿,“这些天,我跟你娘一宿一宿睡不好。听见过街坊们说,说那个明王爷,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废物。
解蔷在心里默默地给补齐,明王也算是这座太康城里的老牌废物了,说出来也不打紧。
这个明王平日里也低调,没有做什么奇葩事供街坊邻居们茶余饭后唠嗑的,也就这两天解蔷与八竿子打不着的明王突如其来的婚事,才让老两口多打听了些。
可惜与老解家熟识往来的也大多是同一时间进城落脚的,谁知道的也不多。
问明王品行如何?
都说:“明王有腿疾。”
“说去守城,却把城丢了。”
“二十五岁一事无成,好高骛远。”
“脾气很差,自己的问题,拿别人的性命来发泄,挺冷血的。”
再一问:“相貌如何?”
老太康人回忆道:“多年没见,只记得少时俊美无双。”
......
“放心吧爹娘,那坊间还传过我是男人呢,真信的不还是一大堆。”解蔷抱着圣旨吃着梨,一只脚踩在椅子上,说得那是一个苦口婆心,仿佛她是劝嫁的那个。
这话说的也算违心,谁愿意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跟一个不生不熟,名声扫地的人捆一辈子呢?
解蔷是不愿意的,可是她又能怎么办?魏贵妃在大殿上,当着太后、皇上和她的面,哭得梨花带雨的,又拿自己死去的儿子说事。
一提那个去世的皇子,太后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皇上也跟着头疼。
亲事,就这么拍定了。
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解蔷如刀俎间的鱼肉,只有认命的份。
解蔷宽慰自己,反正只是成个亲而已,跟谁拜堂不是拜堂?还能给爹挣个爵位,给娘挣个诰命呢!
不管明王有多可怕,她堂堂一禁军统领,还不至于胆怯。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吧。
平日里,也尽量回避着,不与明王府的人产生交集便可。
皇城禁军分四旗,编制直属皇帝,解蔷统领一面北旗,能管住她的,除了四旗禁军大统领闫亓,只有当今圣上。
怕被王府压一头还不至于,毕竟谁也管不住谁。
“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今天赔上了你成家大事,明儿就该赔上咱一家老小的性命......”解老爷气了好几天了,现在还没消下去。
解蔷捂嘴假咳一声,一边摸着腰间的马鞭一边说:“不会的,爹,娘,您二位放心,皇上为了魏贵妃办了我这一次,后边就没那么严苛了......我这就去好好办事,给你们拿赏回来啊。”
脚底抹油,不等解老爷的教训出口,解蔷就跑没影了。
屋里走了个解蔷,解老爷又重重地叹气,解夫人捂着胸口还不忘劝解他:“好了,别气坏了身子,儿孙自有儿孙福。阿蔷从来都有主见的,她的路让她自己走吧。”
解府坐落在太康城的元贞大街上,往南进宫执勤,往北出城练兵。那是她两年前用护驾之功挣来的落脚之所,地段上佳,皇帝钦赐。
多少钱也买不来,多大的权也不能卖。
以彰荣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