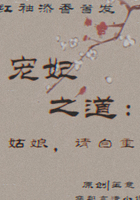翻过自家院墙,云祁就直往自己房间赶,她原没想过会回来那么晚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推开房门,云祁就看见白砚浓坐在正对着门的木桌前喝茶。
“呀,师兄,起那么早!”云祁回回做事一心虚,就会叫白砚浓师兄。
显然,白砚浓也知道她这个习惯:“自己洗干净后,到我房里交待清楚”说完就绕开云祁走了出去。
云祁撇撇嘴,把门关好,心中埋怨:这石头自己有洁癖还要折腾她,但还是乖乖的走向屋内沐浴的那一角。
绕过屏风,发现浴桶中早已准备好了热水,还在冒着股股白烟。
伸手探了一下水温,微微的灼热感,沐浴刚刚好。
还是那个体贴入微的白砚浓。
书房
云祁沐浴后就赶到了书房,可进屋后白砚浓一直在抄写《清心录》,她也不敢打扰。
一旁茶几上还摆放着冒着热气的饭菜,云祁自觉的搬了张小板凳,坐在茶几前吃起早饭。
也不知过了多久,云祁饭都吃完了好一会儿,白砚浓终于放下了笔。
“说吧,去哪儿了?”白砚浓坐在书案后的竹椅上,看着吃完饭老实站在书案前的云祁问。
“都知道了还问”云祁小声地嘟囔。
云祁敢打包票,白砚浓之所以能悠哉的坐在房里等她,一定是知道她去了哪儿。
“满满!”白砚浓对云祁的态度十分不满,呵了一声。
云祁瞬间老实:“我错了,不应该大半夜趁你歇息,去董府调查情况,还回来这么晚,但我……”
话都没说完,便被白砚浓的眼神吓得咽回肚子里。
“行吧,没有理由,我错了”云祁不再狡辩。
云祁总是想不明白,为何一个平时连脾气都没发过的人,有时一个眼神都特别可怕,像狼一样,甚至还要更凶。
“待了一晚上,可是发生了什么?”见云祁主动(被迫)认错,白砚浓收敛了凌厉的眼神,轻声问。
见白砚浓不在追究她半夜乱窜的问题,云祁表示她极有兴趣给白砚浓讲讲昨晚发生的事。
……
“所以,董夫人是你父亲儿时爱慕之人”白砚浓听完后,提出自己的疑问。
云祁一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白砚浓的表情,但还是回答:“可能是,不过瑾姨的态度,好像只认为父亲是朋友,没有别的了。”
“瑾姨?”白砚浓皱着眉头重复了一遍云祁的称呼。
“就是董夫人,昨晚她就让我改了称呼,毕竟是我父母的旧友,这声‘瑾姨’自是当得的”云祁解释说。
见云祁脸上因多了个故人,掩饰不住的笑意,白砚浓并未在多说什么,只想着私下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位董夫人。
“当初遇见我与师父,也不见你如此开心,那么快就接受我们!”白砚浓质问。
云祁走近,蹲下身子,把脸放在书案上,看着对面的白砚浓,极为认真道:“就是因为遇见了你和师父,才会让我再次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对我好的人呀!”
是因为这两个人,才让云祁再次用善良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
白砚浓只看云祁眼睛一下,便移开了视线,沉声转移话题:“一夜没睡,先回屋休息,未时我且带你一同查探炸船案。”
“真的!你带我一起?”
“自然是真的,原先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养伤,如今你都能翻别人家院墙了,想是已经养好了,跟着自是不打紧”
云祁兴奋的跑回自己屋补觉,心想:早知道这样,她也不用在家闷那么多天,早些翻墙不就好了。
——
“你带我来义庄干嘛?”云祁看着头顶上的牌匾问到。
“这几日衙役一直在南溪湖打捞遇害者尸体,今日巳时,却打捞上来了两具男尸,就停放在这义庄”白砚浓讲述来这儿是为何。
“男尸?……对了,你还记得我与你说过,在船上看见过黑衣人吗?会不会他们是一起的?”云祁豁然想到当时她就是因为看到有可疑的人,才会做出捂人嘴这样唐突的事。
“不清楚,但现在需要去检查那两具男尸,看他们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东西”
“行吧,那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云祁说着就推门走进了义庄。
云祁严重怀疑,白砚浓之所以带她出来,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地方,拐她来干活而且。
不过,有意思的活儿,云祁还是挺喜欢的。
走过院子,朝着正对大门的屋子走,一踏进屋,尸体腐烂的恶臭味就熏的云祁想吐,亏得她今天午时起得晚,没赶上白砚浓的饭点,肚中没东西可吐。
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的安置在地上,每具尸体都只草草的盖了张白布,云祁从门口起,开始挨着查看。
云祁查看的尸体,无一例外,全部都被炸的焦黑,又因为在水下泡过,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面貌。
还好身上的衣服虽已焦黑,却也看得出男女样式,有些炸的完全不成型的,云祁也没多留意。
查到一个小角落时,发现了这两具男尸,云祁暗自庆幸。
一番查探后,最吸引云祁注意的,是二人身上的衣服。
虽然衣服已被毁了七八分,但依稀可见这衣服材质样式,不是通幽国的衣服样式,反而更像是凤邑国皇家暗卫的。
除此之外,云祁没找到任何可以证明二人身份的东西。
无从查证,云祁就此作罢,还是找到了关键线索的。
站在屋外给所有尸体鞠了个躬,掩上门朝义庄外的白砚浓走去。
“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东西,但从衣服上看,是凤邑国的暗卫,依你所言,他们果然寻来了”云祁与白砚浓说。
“这反而证明,炸船不是凤邑国君指使的,他还只是怀疑你的身份,并没有证据,所以派人潜在你身边调查。
不过,你如何识得他们的衣服有所不同?”白砚浓分析后疑惑地问。
“我小时候,有位叔叔与我讲过这种独特的衣服样式”
“小时候的叔叔?”
“一时我也不知如何与你说,等闲了再告诉你”云祁觉得她一时半会儿可能与白砚浓说不清。
在云祁的童年记忆里,确实有位叔叔常常夜间翻进她的院里,与她讲凤邑国和凤邑国君身边的一些事。
至于那人的模样,还有那时仍是孩童的她,又为何能如此仔细的记住了他的话,云祁记不起了,就像被人洗过记忆一样。
“奇怪了,那他们身上象征身份的腰牌呢?按理来说该有的,难不成两人的都掉水里了?”云祁摸摸下巴,奇怪道。
“在我们来之前,就已有人来过,给他们收走了”
“收走了!”想想也是,这可是会暴露身份的,凤邑国君不至于蠢到做事如此不干净的地步,只不过这办事效率,云祁自叹不如。
“他们只收走了那些东西,就证明这布料没人能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当什么也没查到,炸船案既已排除了与你的关系,我们明日就出发去长秋城”白砚浓当即决定到,有些事情,要早些解决,免得夜长梦多。
“不行!”云祁第一次反驳了白砚浓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