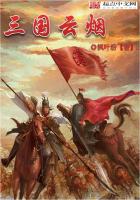夜,十三组石室。
海上月光清亮,透过小窗洒将进来,能清晰看到石室陈列,两排窄床各靠两面墙壁排列,在中间留出一条宽阔的过道,直通石室小门,少女们一人一床,头冲墙壁,脚冲过道。数来,约有三十多个少女,有的已经酣睡,有的默然思索,有的凑在一起小声说话,有的手里有模有样的比划着,像在复习白日所学的招式。
而阳春此刻就在她们当中。
那个瘦小的身躯侧卧着,月光之下,她的双眸如星子般明亮,如泉水般清冽,但此刻,这双眼眸并没有太多的情绪,这张美得不似凡物的脸也没有太多表情,她只是在沉思。
阳春回想着白天拜入夜倾城门下的场景,在众人眼中,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惊天动地地拜入一个怪人的门下,而在她看来,她只是为了活下去,找到一个最有力量的砝码。
这一次,她是真正意义上接受了忘归岛这个现实,也正式成为一位“候选人”。
忘归岛是天罗的秘密训练基地,每七年为天罗输送一批顶尖的刺客,用于执行极重要而隐秘的任务,若其中有身份暴露者,不再适合执行秘密任务,那么进可率天罗黑铠对外征战,退可守夜尊及天罗宫之安危,天罗内部尊称他们为“七选人”。每七年的训练结束,“七选人”一经确定,其地位便今非昔比,从一个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少年,一跃成为天罗的核心,权力地位仅次于夜尊、绿蕊夫人及“风花雪月”四大护法。
“七选人”无疑是一条逆袭之路,七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孩子一跃成为人上人,拥有常人一生无法企及的尊荣和权力,但事实上,更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极其艰辛,往往以生命为代价,它不仅是一场对天赋、毅力、体能、智能的严苛筛选,是一场战斗素质、战斗直觉甚至运气的无情比拼,更是一场对人性的残酷考验。
每七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适龄孩子作为“候选人”来到忘归岛,但经过七年的训练,最终的“七选人”通常不超过十个,真真的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而那些没有成为“七选人”的孩子,只有一个结局——以血肉之躯为强者奠基。
相比死者,那些活下来的“七选人”看似是幸运而成功的,但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简单。七年来的血腥记忆,那些自相残杀的疯狂和煎熬,那些亲近友伴惨死眼前的痛苦和绝望,都将伴随他们一生,如影随形,永不消散。当然,有些“七选人”之所以能成为“七选人”,免不了摈弃良知,扭曲人性,对于这样的“七选人”,那些血腥记忆不再是他们的噩梦,而成了他们的养料,滋养着他们心中的毒蔓,拖拽着他们,在心硬血冷的路上越走越远。而有些“七选人”,在这人间炼狱里,靠着某种信念,小心翼翼地护住了那一点良善,对于这样的“七选人”,那些血腥记忆如同梦魇,在阳光之下,他们和别的“七选人”一样,杀伐果断,坚如磐石,但在那些阴雨连绵的黑夜里,梦魇一次次袭来,那些记忆化作湿冷粘稠的血液,汇入连绵夜雨,一点点沁入他们的梦,一次次刺伤他们心中尚存的柔软之处。
正因如此,大部分人出于自我保护,或早或晚都会摒弃原本的自我,重塑出一个心硬血冷、手段毒辣的自我,去应对这非人的训练和你死我活的选拔,也因此,小岛得名“忘归”,并不是风景让人流连忘返,而是到这的人,唯有忘了归途,方得生存,忘了本心,方得自在。
想要在这样的生存斗争中活下来,成为强者是唯一的选择。
而夜倾城,作为岛上公认的最强,也成为阳春唯一的选择。
“嘿,白天我们一起的,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一个清甜的声音打断了阳春的沉思。
阳春翻了个身,原是白天那个少女,她生得十分白皙清秀,脸颊还带点特有的婴儿肥,笑起来嘴角有一对小小的梨涡,十分娇憨可爱。
阳春也报之以微笑:“我叫阳春。”
少女眨眨眼:“哇,原来你笑起来这般好看!我叫岸芷,程岸芷。”
“好美的名字,”阳春由衷赞叹,“这是我听过最美的名字啦!”
岸芷笑:“我爹爹说取自古文‘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叫岸芷,我还有个妹妹叫汀兰。”
阳春羡慕道:“看来你爹爹很疼爱你们,给你们取了这样美妙的名字。”
“是呀,我爹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他可疼爱我们姐妹了!只可惜,我到了这里……不知爹爹几时能寻到这里,好带我回家去……”
“到了忘归还想回去?快收起你幼稚的想法吧,不然你都活不过明天。”
一个尖刻的女声从近门的床铺传来。
岸芷天真直率:“你!你这姑娘,怎地这般讲话?”
那声音冷哼一声:“新来的,我告诉你,趁早打消回家的念头,到了忘归,那就是到了炼狱,你身边这些个人,个个都是吃人的恶鬼。哦对了,还有你旁边那个叫阳春的,可是被自己亲爹嫌弃的人,这种人最晦气,连最下层的恶鬼都不如,你呀,最好离她远一点,不然最后被吃得骨头都不剩,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众人闻言,一阵骚动,很快又陷入心照不宣的沉寂。
岸芷不忿,坐起身来,冲那少女喊道:“你胡说些什么!”
“我可没胡说,她就是个贱种,连她的亲生父亲都嫌弃她,把她送到忘归来,亲父尚可辱之,我说这几句话,又碍得了什么?”
岸芷愈气:“你怎说出这般难听的话?!若我爹爹知道你这般欺侮我们,定会带上我泉哥哥和府中护卫,好好教训你一番,给阳春出气!”
“你爹爹?你泉哥哥?拜托,这里是忘归岛,就算是天王老子,那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要想活着出去,还得问问夫人同不同意,在这给我装什么千金小姐!”
“你!……”
岸芷愤慨满怀,正想起身过去理论,被阳春轻轻拉住。
月光之下,阳春目如点星,眼神坚定而沉稳,冲着岸芷摇了摇头。
岸芷:“她这般中伤你……难道就这么算了?”
阳春从容道:“无妨。”
她云淡风轻,仿佛那些刀子般的言辞,无关于她。
岸芷不解,腮帮子气鼓鼓的,阳春又道:“她说的也是事实,罢了。”
岸芷愕然,又恍然想起,自己方才提及爹爹和泉哥哥的言辞,难道不也戳中阳春痛处?更觉歉疚:“啊……对不起啊阳春,我不是有意……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阳春心里明镜似的,反倒豁达:“何必说对不起呢,你有爹爹疼爱,还有哥哥为你打抱不平,这是多么温暖的事情啊,你说予我听,倒似我也能感受到温暖,何来对不起呢?”
岸芷点点头,用小小的臂膀环住阳春,就像白日里她握住她的手那般,安抚道:“阳春,倘若有一日我们出去了,我爹爹便是你爹爹,我哥哥便是你哥哥,他们会疼爱你,就像疼爱我和汀兰一般,我保证。”
阳春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心底那块崩塌的地方,好像也没那么疼了……
“哈哈哈,笑死个人,”那个刻薄的女声再次响起,“我说你这千金小姐,是真傻还是装傻啊?你爹是你爹,她爹是她爹,什么你爹能疼爱她,像疼爱你一样?这可能吗?她亲爹都见不得她,还轮得着你和你爹来多管闲事?可别让人笑掉大牙了……”
“红鸢,别说了……”角落里另一个少女看不过意,小声劝阻。
“我偏要说,大家还不知道吧,这贱种染了乌香毒的,大家最好都离她远一点!”
话音刚落,黑暗中有些窃窃私语。
岸芷从小养尊处优,天真不谙世事,大声问:“乌香毒是什么?”
叫红鸢的刻薄少女冷笑一声:“你连乌香毒都不知道,还敢挨着她?”
岸芷听了这话,非但没松开环着阳春的手臂,反而抱她更紧:
“我不管阳春有没有什么香什么毒,自打我见到她,就觉得她好看又亲近,比你这口舌恶毒的家伙,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贱种!”
红鸢怒道:“我呸!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话音刚落,岸芷只觉双臂一空,同时一个黑影掠过。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划破了暗夜。
原是红鸢跋扈,被岸芷的言辞激怒,欲打岸芷耳光,却被阳春先一步挡护,这一耳光,是结结实实落在阳春的脸上。
黑夜中,石室众人开始骚动。
阳春挨了一耳光,也顾不得脸颊异样的疼痛,一跃而起,直接与红鸢扭打起来。
红鸢一愣,显然惊住了,这个新来的,居然还敢挑战她?也动起手来。
众人见状,纷纷起身来观战。
红鸢早几日接受训练,身法招式显然比阳春成熟,一度占了上风。而阳春这边,就像一只从未学过捕猎技巧的小狼,与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狭路相逢,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奇妙的是,阳春虽处处受制,暂无还手之力,但身形灵动,反应敏捷,每每躲过红鸢的杀招。红鸢见久攻不下,只觉脸上挂不住,出手愈发凌厉。
眼看二人缠斗不休,而阳春处境不佳,岸芷急得不得了,几次想冲上去助力,都被红鸢以腿法踢开,最后急得大叫:“别打了!你们别打了!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眼看着她倚强凌弱,你们怎么心安?!”
沉默,可怕的沉默。
半晌——
“红鸢,收手吧……她刚来,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呀……”
唯有角落里那个少女颤声劝道。
“放屁!敢跟我动手,看我不废了她!”
只见红鸢以一套连贯的腿法攻击阳春腹部,而阳春这边,脸颊的疼痛越发剧烈,甚至开始目眩耳鸣,竟一时躲闪不及,生生受了这一套腿击,摔出几步远。
红鸢趁机骑压在上,一手扼住阳春咽喉,一手使出鹰爪式,欲取阳春左目。
被压制的阳春只觉脸颊的疼痛越发难以忍受,脑袋昏昏沉沉,眼前的敌人也出现重影,但求生本能驱使着她,她一手护住咽喉,一手去格挡鹰爪式,额角有细密的汗水沁出。
只见红鸢的鹰爪式杀气毕露,离阳春左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只有分毫距离——
众人观战至此,纷纷屏住呼吸。
千钧一发之际,一枚极细极短的银针自口中吐出。
“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一声惨叫划破夜的寂静,响彻整排石室。
随即只见一人,捂住右眼翻滚在地,嘴里痛苦地呻吟叫喊。
岸芷骤惊,道是阳春,连滚带爬过去搀扶,反被乱脚踢开,才知扶错了人——
原来,方才那一针是从阳春口中吐出,红鸢轻敌,加上夜里视物不清,那枚银针未受任何阻碍,便直取红鸢右眼。
竟是如此出人意料的结局。
与此同时,阳春正无力地躺在一旁,一双清净的眸,涣散而无措:
“她……指甲里有毒……快……快去找……司教……”说完,头一歪陷入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