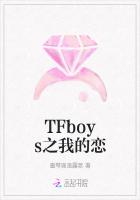忘归岛,训诫室。
门口的侍卫听有脚步声靠近,连忙站直身子:“见过两位司教。”
来二人均着黑色锦袍,袍上用金线银丝绣有不同的图案。
走在前面的男人身形健硕,五官硬挺,手执一根雕花蛇头短杖,有些急不可耐,嘴角带有邪淫的笑意,让人很不舒服;后面的女人一头银发,面容却是姣好,可谓真真的鹤发童颜,却刻意放缓脚步,有意与蛇杖男人保持距离,
二人应了一声,推门而入。
入门闻得一股香气,清而不郁,淡而不腻,似是少女沐浴后花香与肤香的凝合,浅浅的,但香气之中,似乎还有点别的味道——
“乌香?梁逸,是个瘾君子,这一趟你怕是白跑了……”
银发女人第一时间确定那是乌香的味道,忙不迭打趣身旁的男人。
“月姬啊,这你就错了,不就是乌香么,戒了就成,到底是货真价实的少女,不像您,”梁逸凑近月姬,轻佻的呼吸尽数喷洒在月姬脸上,“八十岁的人,长了十八岁的脸。”
“离我远点!”月姬喝道。
论岁数,他喊她奶奶都不为过,论辈分,他还该唤她一声司教,但此刻他竟轻佻至此,只恨她已到耄耋之年,身手大不如前,否则定将他千刀万剐,想着,月姬不禁啐了一口。
“你以为我想做什么?”梁逸见月姬不吃这套,有些挂不住脸,离了月姬的身子,不忘反唇相讥,“我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老太婆!”
“你!”月姬怒不可遏,就要出手教训梁逸,却听角落有人冷冷咳了一声。
一双黑眸正凝视着一切。
“倾城,你在啊?!”梁逸听见这再熟悉不过的咳嗽声,登时没了底气。
角落里的人不答,梁逸有些尴尬,连忙找话:“听夫人说,她捡了一匹小狼?”
“在里面。夫人交代月司教帮她戒除乌香,既然月司教已到,倾城先行告退。”
那人说罢,起身,从角落走了出来。
挺拔的身姿,迫人的气势,隐隐一股戾气,令人顿生寒意。
一样着黑色锦袍,黑如暗夜,唯一与月姬梁逸不同的,是他领口、腰际、袖摆及衣摆处,均绣有极为华丽的云月暗纹。黑色,如此肃杀的颜色,穿在他身上竟是这么适合。从暗影里走出的一瞬间,让人觉得,这是黑夜里走出来的神,又好像地狱里爬上来的修罗。
“当心点,既然是狼,就是会咬人的,尤其——男人。”
与梁逸擦肩而过,那人戏谑道,带着轻蔑与不齿,是故意说与梁逸听的。
自始至终,梁逸都不敢抬头看他一眼,即使心里早骂了千百遍。
待夜倾城离去,月姬和梁逸才向内室走去。
内室不大,极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这便是忘归岛的训诫室了。
此时,训诫室正中的椅子上,有一人斜倚,准确地说,是被硬绑在椅子上。
乌发黑衣,更衬出肤色莹莹如雪,不过十五六岁,已初显明月之姿。若不是乌香侵蚀,脸上留下淡淡痕迹,如此姿貌堪称完美。
不过这绝色少女,在二人走近时却无半点反应,原是昏迷未醒。
一壶冷水灌顶之后,少女终于缓缓醒来——
一双眼睛缓缓睁开,道是,明眸渐开横秋水,千斛明珠未觉多。
梁逸见此美貌,纵阅女无数,也难抑身心兴奋。
见梁逸目露歹意,再环视陌生的屋子,那双清眸一下换上提防。
月姬见此,一把将梁逸拽到旁边,上前一步,语气轻柔道:“你醒了?”
少女见月姬一头银发,话语间有说不出的温柔和亲和力,眼中的敌意也收敛一些:
“这是哪里?你们是什么人?”
月姬轻声应:“这里是忘归岛,我是月姬,来帮你戒除乌香之毒的。”
少女盯着月姬,眼眶微红:“那我父亲呢?”
月姬一怔,随即换上惯常的假笑:“这里还有很多孩子,跟你差不多大的,等你病好了,就能搬出去跟他们一起住了。”
少女不理,声音有些嘶哑:“我父亲呢?我要见我父亲!”
“见什么父亲!来了这里,谁都别想回去!”梁逸没了耐心,怒吼道。
“这不是阳家!到底是什么地方?!”
月姬起身倒了一盏茶,语气不复最初轻柔了:“这当然不是阳家,这里是忘归岛,是我天罗的秘密基地,为天罗培养最顶尖的刺客。”
“天罗?”少女惊疑。
月姬接道:“我瞧你不聋不瞎,竟不知我天罗的威名?天罗,是当今唯一能与朝廷政权抗衡的江湖组织,你该感谢,被天罗选中,是多么大的荣耀!”
少女不屑道:“我不要这劳什子荣耀!我只要回阳家,我要见到我的父亲!”
月姬冷笑:“别再做梦了,上了岛的人,一个都逃不了!但是,如果你留下,你成功了,总有一天,你会感激天罗的栽培,也会为杰出的自己而骄傲。”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
“有的人能离开,而有的人……一生都不能离开,”月姬呷了一口茶,“自由是最强者的特权,只有成为最强者,得到天罗的承认,才可以离开忘归岛,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就成为孤岛上的一缕游魂,用血肉之躯为最强者奠基。”
月姬话音落,少女隐约明白了什么,顷刻平复下来,似在思考,显出一种成人的冷静来。
月姬见她情绪平稳,试着与她拉近距离,轻柔问:“现在,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阳春。”
少女干脆地回答,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月姬手中的茶盏。
“阳春?”月姬对阳春的配合感到满意,面露笑意,“怎么?你渴了?”
阳春看看月姬,又看看茶盏,咽了几口口水,点点头。
月姬起身斟了一盏,端着朝阳春走去,见她手不方便,便弯腰俯首,准备亲自喂她。
她本不必如此,但她自信,这是得到阳春信赖的好手段。
不料,她将把茶盏递到阳春唇边,一个绳套便圈住她的脖子,椅子上的阳春一跃而起,拽着她就往墙角移去,她感到颈上的绳套迅速收紧,几乎不能呼吸。
阳春一边扼住她的要害,一边朝梁逸喝道:
“你!放我走,不然我杀了她!”
“你这丫头,竟敢偷袭六朝元老,快放开她,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
梁逸怒喝,举起狰狞的蛇杖,但碍于月姬的身份,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反应却正中阳春下怀,她笃定这月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冷哼一声:
“放开她,我才真的是死无全尸了!你去把门打开,让我走!”
“上了忘归岛,就是鬼神都走不了!你放开她,兴许夫人还能饶你一命!”
见梁逸无意退让,阳春又收紧一些。
“不,不……”月姬呜咽着,只能发出几个单音了。
“听见没有!放我走,不然,我要她陪葬!”
“不知深浅的丫头,等你把事情闹大,看夫人怎么收拾你!”
阳春冷哼:“我就知你做不了主,你不放我走,无妨,反正横竖都是死,闹大了更好,也让你们主子看看,天罗都养了些什么废物!”
“你!”梁逸被她怼得说不上话来,只能干挥蛇杖,像个二愣子。
“哈哈哈,说得好啊!”门口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
不用说,这时候能笑成这样的,也只有忘归岛的主人——绿蕊夫人了。
伴着笑声,一个美妇人款款步入。
阳春怔了,令岛上人闻风丧胆的绿蕊夫人,竟是这样一个雍容华贵的年轻妇人,她身着一袭艳色锦袍,袍上的花样是碧荷,一头长发黑如泼墨,滑如锦缎,却无过多的金银装饰,只由一支碧玉花簪轻轻绾起,“绿蕊”一名大概就因此得来。
“夫人,你来得的正好!赶紧治治这死丫头!”那蛇杖男人一脸谄媚,快步奔了过去。
绿蕊夫人见阳春挟持了月姬,不怒反笑:“瞧瞧,我都错过了什么好戏?”
阳春见她笑,更觉不寒而栗,当日石室之中,她便是这么笑,然后,那个人便出手杀了十几个侍卫,这世间果真有一种人,有花蕊一般的相貌,却有修罗一般的心肝。
想着,阳春不禁攥紧手中的绳套,确保唯一的人质不能脱逃,决意赌上一把:
“你是岛主?放我走,不然,我杀了她!”
绿蕊夫人盯着阳春看了半天,忽然大笑起来:“小丫头,我该说你勇敢,还是不知天高地厚?”说着她绕过桌椅坐了下来,好整以暇地看着眼前这场戏。
“你不信?”阳春一咬牙,狠了狠心,再一收紧。
“……”这一回,月姬已是满脸通红,呼吸困难,连单音都发不出来了。
“不是不信,”绿蕊夫人笑意盈盈地望着阳春,“是不在乎。记住,别拿无足轻重的人做人质,这样只会让你陷入更艰难的境地,这是给你上的第一课!”
话音落,阳春感到手里的人微怔了一下,竟放弃了挣扎。
真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主子一句话,求生的意志亦可以放弃。
天罗的死忠,竟到了这种地步?
“怎么?还不动手?”绿蕊夫人端起茶盏,气定神闲地呷了一口。
阳春怔了。
她什么意思?
她是完全不在乎这个人的命吗?
她杀不杀这个人,他们都不会放她走?
为了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结局,送了一条命,真的是她想要的吗?而这个人,刚才还亲手喂她喝水,即便那是伪装是手段,于她,也是一瞬的温暖啊!
阳春终于意识到,论狠,她终究狠不过这个女人,终于放开手。
见阳春撤手,黑铠侍卫迅速一拥而上,将她按倒在地。
阳春看着大口喘气的月姬,恍了神,突然后怕,就在刚才,她差点勒死这个人。
“夫人英明!阳春以下犯上,属下愿替夫人分忧,不如,将她交由属下处罚?”
方才大气都不敢出的梁逸,此时见事态可控,满脸谄笑,第一个上前,炽热地望向绿蕊夫人,对少女的觊觎昭然若揭。
“自然是要处置的,”绿蕊夫人却不理会,只淡道,“不过,不是你。她说的对,天罗不需要废物,梁逸,你也该做好自己本分的事了。”
梁逸闻言,登时面如土色。
须知绿蕊夫人向来偏袒他梁逸,这岛上,除了绿蕊夫人,还有那该死的夜倾城,他还真没受过别人的委屈,本想借机得到这绝色少女,不料反被当众指责,一时如鲠在喉。
“是,夫人说的是。”梁逸强压不悦,退了回来。
“倾城,”绿蕊夫人侧身看向旁边的年轻人,“你可知我为何留下她?”
阳春这才发现,那个人,不知何时也到了。
她的头被人按在地上,其实看不见那人的脸,只有一袭绣了云月的黑袍,和那股甜甜的独特的香气,才让她确定是他。此刻,唯他一人立于绿蕊夫人身侧,似乎是个特殊的存在。
“夫人爱才,而她天赋过人,故留了一命。”
那声音冷冷的,一如当日听到的,冰冷,无情,疏离,戏谑,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说对了一半。其实,最关键的,那一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你的影子。”
“夫人说笑了。”那声音依然淡漠。
“倾城,还记得七年前你砍我那一剑吗?整个忘归岛,几千个孩子,只有你敢!那日,她偷袭我,我就在想,她和你是不是同一类人,是不是淌着同样的血?今天的事证明,我并没有看错。想不想知道,她能不能成为第二个你,第二个卓绝非凡的夜倾城……”
女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巅峰快感,她自以为洞察一切又操纵一切,随意挖掘每个人的伤痛,随意操纵他人的命运,不带一丝同情心。
夜倾城看着癫狂的她,眼底掠过一丝复杂,面色却如常:“哦?那我拭目以待。”
绿蕊夫人点点头,接着优雅起身,从阳春眼前走过:“关进石室,饿七天。”
说罢拂袖转身,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
“哦,对了,你口口声声要回家,要见父亲,你一定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这里吧?”
阳春闻言一怔,再不能冷静:“你说什么?”
女人嫣然一笑,说出的话却如最尖的刀:
“你是阳家后人吧!就是阳家,亲自派人将你送到这里的。”
“不可能!”阳春瞪大眼睛,斩钉截铁道。
“怎么不可能?”绿蕊夫人笑意依旧,玩味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不可能是阳家,不可能是父亲!不可能!你骗我,你撒谎!”
绿蕊夫人看着几近崩溃的阳春,从袖中抽出一条手巾,扔到阳春面前:
“好好看看,这手巾上的徽记,是不是你阳家的族徽?”
阳春抬眼看去,那手巾上的徽记,跟那辆马车上的徽记,竟是一模一样,那是阙城阳家专属的族徽!当日云来客栈一别,铁叔去了云滇,她上了马车,可回阳家的路途好像很长,她睡了很久……醒来,便是那伸手不见五指的石室了……
见她迷惑,绿蕊夫人索性揭开所有伤口:“傻丫头,还不明白?阳家不是来接你回家,是直接送你来这里!你说,到底有多厌恶,才会亲手送你来这忘归炼狱?”
“不可能!不可能!”
阳春竭力否认着,她不肯信,也竭力强迫自己不要信,但心底,好像有什么地方,正在一点一点碎裂,那双清净的眼眸溢出凄凉。
绿蕊夫人最善捕捉人心,确定她已明白真相,不忘补上最后一刀:
“所以,这七天在石室好好思过,也打消离开的念头,阳家,你父亲,根本不要你!”
鬼魅般的声音从远处飘来,一字一字重重击打着她的心。
阳家,你父亲,根本不要你!
根本不要你……
不可能!骗我的!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为了惩罚我刻意编的谎言!
阳春颤抖着,想把听到的每个字都抹去,可那些话像是烙铁,深深印在她的心上,心底那个碎裂的角落,终于轰然倒塌了……
“何必说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同情她了?真相往往残酷,可越是鲜血淋漓,越要接受,唯有这样,才能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