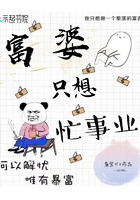“可那个孩子没死,他活下来了,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装疯卖傻,他忍辱负重,他含泪而活,所求的,不过是一个他早已猜到的真相,真到他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
“那个孩子,谷川,就是你。”
星鸦展颜一笑,面上的青肿早已消失不见(被她用术法遮住了),仿若春暖花又开。
刹那间,晃了谷川的眼。
“值得吗?即使他是迫不得已,但他若是知道,你为妖,该当如何?”
“我不是,胡说!胡说八道!你算什么东西,在这里置喙我,凭什么!”谷川外强中干地吼了几句,又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疯疯癫癫的。
星鸦冷眼旁观,也不去戳穿他。
而阿萱可能是真的看不下去了,提起谷川的衣领,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般,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是男人吗?争点气不行吗?你爹不要你了,你就准备不要你自己了?我呸!胆小鬼!”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你不是我你怎能知道我的痛苦,我现在是妖,是妖!那种肮脏的生物!!!”
“找死?!你再说一遍!”
阿萱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目光如炬地盯着谷川,若是眼神能杀人,谷川早就不知道投了几回胎了。
不过当着妖的面说人家肮脏,可不就是找死吗?
“我脏了!脏了!脏了!别碰我!”
谷川一手甩开即将要接近自己的手——阿萱的爪子。
星鸦同情般看着谷川,一脸的“这孩子傻了”的表情。
“我可能忘了告诉你,你跟前这个长得人畜无害的女人,就是妖,货真价实的三百年妖物。”星鸦唇角轻扬,心情颇好地勾出一抹恶劣的笑。
“啊——”
从永道山深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那道惨叫真的是让听者悲,感者痛的那种。
一盏茶过后,
被阿萱修理了一顿的谷川彻底学乖了,也不敢在星鸦面前放肆了,整个焉答答的,就像个鹌鹑一样缩在树下。
星鸦头疼的揉了揉眉心,“阿萱,你这样可真让我不好办啊!”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不,多配合啊,我肯定,你问什么,他答什么,乖的不得了的那种。”阿萱不服气地嘟囔。
“咳咳!”星鸦无奈地看了阿萱一眼,随后清了清嗓子,“谷川,你作恶多端,乱杀无辜,冤孽沉重,若是要你负责负债,你可愿意?”
谷川神色扭曲,五官皱在一块儿,一个字总结:丑。
“凭……”什么啊!
“啪!”
一记响亮的巴掌声。
“你刚刚要说什么?”阿萱言笑晏晏地看着他,看得他毛骨悚然。
“凭什么,凭什么……”谷川急的冷汗流了一额头,就是没想出怎么把话圆过去。
“凭什么,凭什么你这么好看!”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啪!”
又是一个巴掌。
“你丑你还有理了?”阿萱笑笑,吹了吹手掌,忽而想到些什么,顿了顿,然后又用极度嫌弃的神态甩了甩手,仿佛在甩什么脏东西。
“真脏,不是吗?”
话落,谷川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红,调色盘一样滑稽。
终于,他不情不愿地开口:“可以,但我要他们付出代价!”瓮声瓮气的。
“自然,但不需要你动手。”
“今后,你是跟着我修习的小妖,名——入画。”
晗武十年,五月初一,灵州州府府主谷殿祜,死于非命,死状与灵州北境死者相同,一时间,众人皆知,是灵州作死,败坏了气运而遭此劫难。
甚至连一向仁慈的州府主都难逃一死。
次日,大量证据铺天盖地,全都指向灵州府主做的龌龊肮脏事,以及其中与七麓之人私通书信,狼狈为奸的事实。
而灵州府众人,成为众矢之的。
仅仅一夜功夫,灵州府倒,诸位尽散,一州之地,瞬成无主之地。
而灵州,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晗武十年,八月十三日,经历了三个月的,堪比乱世的混乱局面,灵州迎来了新的管辖者——星川。
着青衫而立,云冠束发,剑眉星目,朗朗少年,手持利剑,颔首高抬,所指之处,苍龙腾啸!
此之者,是为乱世少英。
历时五月,灵州重焕生机,三年之后,跻身于十三州上三州。
在任五年,兢兢业业,所做善事皆为实务,风评良好。
后世称之为,缚灵者。
他在任期间,有瘟疫时期做的彻夜寻医问药,荒芜之年的布施粥米,也有和平时期的颁布一系列的法规,是真真切切地要将灵州打造成一个,少恶少乱到极致,几乎没有的安然之地。
晗武十五年,星川退任。
退任当天,凡是灵州人的,都跑到当地衙役公堂上,聚众闹事般,也不做什么,就是站在那里的门前。
待从灵州恩郡主州府方向发射出一门礼炮烟火时,‘哗啦啦’地一大片,整齐划一向着那个方向,弯腰低头行礼,一手下垂,紧贴腿根,一手摁在胸前,作最高灵州礼,以表敬意。
“州主,安好!”
统一的声音,洪亮有力,脱口的一瞬间,集合在一起的声音,震天动地,仿佛响彻云霄,从四面八方涌去恩郡。
谷川,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认为父亲谷殿祜是错的了,但他这一次,却是觉得那个男人可真是错得离谱。
坐在扶谷竹屋里的谷川神情恍惚,只是眼睛一转不转地盯着面前的画面。
清澈的水组成一面镜子,而镜子中央的画面,正是灵州各处现在的景况。
相当于现场直播。
“他竟然为了利益与自己的修为,而将灵州人当做货物,送给七麓的那群疯子!他怎么敢!”
嘶哑的嗓音中带着怒意。
“呵!你亲爹是个什么德性,你不知道吗?反正又不会危及到他自身。况且,你杀了多少灵州人,你心里没点逼‘数儿?”
轻飘飘的一句话,便让谷川彻底熄了火,焉答答的,垂头丧气。
星鸦淡淡瞧了他一眼,无所谓般,“你为什么用我的姓氏?”
“……没什么,谢谢你。”
“等等……”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谷川说完就出去了,只留下星鸦在一旁疑惑。
“我告诉他了。”阿萱这时走了进来。
“什么?”
“别总是把自己当英雄好吗?还有,现在,快回去,你还要忙你那孙什么东家的事呢!”
“诶!别忘了告诉他,他现在叫入画!不叫谷川!”
“知道了!”
阿萱不耐烦地一扫手,便将星鸦的一缕魂念送了回去。
蠢货!
阿萱气得磨了磨牙。
“她是个很好的人吧?”
谷川,哦,不,是入画,他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倚墙而笑,张扬的眉眼,有着他独特的桀骜。
“不然,也不会帮我还了这么多孽障。我就说嘛,她明明说我十恶不赦,恶贯满盈,我只是做了五年好事,便刑满释放了?这我自己都不信!”
入画抬手,在神请恍惚的阿萱眼前扇了扇。
“傻了?我说的话听到没!”
“啊!……嗯,我知道。”阿萱揉了揉发疼的脑袋,轻声说,“想听听我,我们的故事吗?”
入画一愣,然后莞尔。
“乐意至极。”
晗武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那是灵州的第一场雪。
细细软软的雪花就这样慢慢悠悠地飘了下来,落在刚出客栈的阿萱肩头,然后是头顶。
风开始冷了,夹杂着雪花,呼呼地朝人吹来。
“啊!乌鸦,第一场雪!”
惊喜的叫声,让还在大堂吃早膳的星鸦往外瞧了瞧,然后很是不在意的“嗯”了声。
阿萱不是没见过雪,但不得不说,灵州的雪确实是南易界中最美的存在了。
明明细细软软的白雪,却生的晶莹剔透,像冰晶一样,闪亮闪亮的。
飘悠落下时,让人如同置身于世外仙境一般。
温度若是再降些,地面会生出白雾,低低浅浅的一层,飘飘散散的,那才真是恍若九重天上的景色,朦朦胧胧的笼罩一片。
阿萱每次听星鸦这样描述,都恨不得马上到冬天。
也因为阿萱可爱的小愿望,星鸦留了下来,原本想带她去茉州看花的。
思及此处,星鸦再次无奈地耸了耸肩,阿萱自己不去的,回头错过了茉州五年一度的花神节也不怪她。
“乌……”
星鸦百无聊奈地戳了戳瓷碗里的饭,狐疑地抬头,瞟了一眼门口。
这一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
门外哪里还有阿萱的影子,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水泽泽的,方才纯白无暇的晶雪变得污秽脏乱,消融的雪水满地皆是。
“阿萱!”
星鸦面色阴沉,猛地搁下筷子,扔了一锭银子给店小二,便火速往外走。
“客官走好诶!”
仅披着一件薄薄的黑袍,里衣也只是夏日衣物,可明明身有修为,不惧严寒的星鸦,却分明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寒凉。
黑色的长靴踩在纯洁的雪上,留下肮脏的脚印。
这个时候谁还在乎踏雪无痕的风度啊!
“阿萱!”
星鸦那个急呀,一路走一路喊,一直走到了一个偏僻静默的小巷子里。
若不是星鸦身上的银铃响得厉害,她完全不能相信,阿萱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当然,也不保证是有人将她劫来的。
如果是后者,那么……
“该死!”
星鸦眼中燃烧着怒火,任是惊涛骇浪也扑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