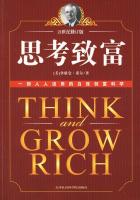世界上唯一随着时光流逝而越变越美的东西就是回忆。
人生在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立德”、“立功”,我不敢自诩,让世人或后人评说为好;“立言”我亦不敢,只想把自己的沧桑岁月、坎坷历程、人生感悟留在纸上,让后人或者读者,从中获取些许有益的东西。
开篇伊始,我想引用冰心的一首小诗——《成功的花儿》,作为引子: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明艳,
然而当初它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生命的开端
我的祖上,原系陕南紫阳朱氏分支派衍,别立小宗。明万历年间,因贸易商运,支脉朔迁,投寄宁夏中卫前所营落脚,继而转居中卫泉台子。人迁地变,我祖又由中卫迁至靖远三角城(又名三滩)、裴坡寺一带,辛勤耕种,家道渐兴,枝叶又渐繁茂蔓延。丁繁族旺,种地为生,渐难承载,我祖支脉又迁至常生窑马缠嘴,拓荒整地,蓄养家畜,从此创出了基业。
常生窑虽然临近黄河,但是山峦丛立,沟壑纵横,可耕可灌的土地仍然有限,已经很难承载数倍增生的人口了。我奶奶的娘家人——罗家宗族,率先迁至有自流大水浇灌庄稼的锁罕堡。听说我的罗家几个外太爷,人都特别勤快厚道,4个儿子也都十分精明能干,他们迁到锁罕堡后不久,就置办了水浇地、旱沙地、漫水地,车马牛羊,还置办了骆驼队,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家道也很兴旺。
常生窑人多地少,大多数人家生活都比较艰难。我们朱家,后来由于诸多的原因,家道也逐渐衰落,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所以,家父成基公,13岁就随我的祖父怀标太公,也迁至锁罕堡,投奔我奶奶的娘家——罗家来了。
1942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我就出生在锁罕堡(现叫兴泉),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从这个小镇开始的。
罗家在锁罕堡可算是土地成垧,牛羊满圈,车马骆驼队俱有的大户人家了。我的祖父率家迁居锁罕堡后,主要是仰仗罗家的帮助,才得以立脚。我的祖父勤快厚道,农活杂务,干练精明,并且人穷志不短,辛苦操劳了几年后,就改造了荒滩,自己日夜忙碌,铺压了20多亩旱沙地,这就为我们一家在锁罕堡生息、住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我的祖父携带我的父亲,除自耕自种自家的田地外,再忙里抽闲地打些短工,家里的日子也就渐渐过得下去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祖父于36岁的本命年上,难逃大劫,溘然与世长辞。实际上,他是含辛茹苦,长期辛劳,积劳成疾;再加上家道贫寒,缺医少药,过早地走完了人生之路。当时,在我们家里,祖父就是一片湛蓝晴朗的天,天塌下来了,我们的家顿时陷入一片黑暗。暗无天日的岁月何时才是个尽头呢?所幸的是,我的39岁的祖母,以妇道人少有的韧性和天赋,守寡持节,重新又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蓝天。祖母拉扯着父亲、叔父和3个姑姑,于艰难困顿之中重振家业,率领我们朱家继续挣扎向前。但是,苦难的家庭总是各有各的不幸——我的两个姑姑又先后生疾、夭折。肩负重担的祖母,在丧夫失女的沉重打击下,心里有多么大的痛苦呀!
祖母的眼泪哭干了,心血却不能流干呀——还有一家4口人呢!意志坚强的祖母,又一次擦干了眼泪,挺直了腰板,携儿领女,挣扎在人生坎坷崎岖的道路上。
我的父亲13岁就给舅舅家干活,叔父8岁也开始给舅舅家打杂,实际上就是混一口饭吃;祖母给舅舅家帮厨。就这样,依靠娘舅家,我们全家人都忙活了起来,一家4口人的性命才顾缠了下来。尽管日子过得很艰辛,但人活下来了就是万福。我从奶奶、父亲、叔父的口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那些辛酸的往事,我们也永远铭记娘舅家的救难之恩。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始终是我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而父亲则是港湾上的那片独特的风景。
父亲在18岁那年离开了娘舅家,从此独自支撑起了我们破碎而苦难的家庭。他赶着毛驴跑脚,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赚得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后来,我从奶奶的口中得知:父亲一边跑脚,一边操持家务,渐渐地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就和本村王家姑娘(即王连科、王连升的亲姑姑)拜堂成亲,组成了一个有人烧火做饭、有人操持家务的家庭。父亲和王氏先母生有一个心爱的女儿,小名梅花。可是王氏先母英年早逝,我们多难的家庭又陷入了一个老幼难生的境地。后来,梅花姐姐在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成人,许配给小芦塘的郝生魁为妻,生下5个姑娘、5个儿子——她就是郝虎、郝胜、爱娃等兄弟姐妹的亲娘。
日子再苦总是要过下去的。深受丧妻之苦的父亲,深知一家人的生存都指望着他,他又一次挺直了脊梁骨为着生活而奔忙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