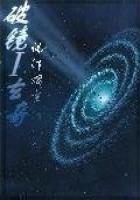玉幼清抬眼,柳周舟白着脸正低低咳嗽,她候了良久,直到柳周舟诧异她为何还不开口说话时,玉幼清正看着她,唇角微微一勾,轻轻问:“你多大了?”
柳周舟讶了讶,如实答:“未足二七。”
玉幼清想了想,大概是还不满十四岁的意思?
“你问我年纪做什么?”柳周舟兀自倒了杯水润喉。
“我只是听你方才提到了,蚀阳蛊。”
柳周舟瞪大了眼,茶盏啪一声磕在案角,她浑然未觉,“你一直醒着?”她挪到玉幼清身边,“那是你救了我?云七那个人脾气真古怪,像是全天下都得罪了他,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他就要杀我。不过他对你倒是真温……”
“能不能。”玉幼清提高嗓音打断了喋喋不休的柳周舟,“跟我说说蚀阳蛊。”
“蚀阳蛊?”柳周舟盘腿坐好,“方才你不是醒着,应该都听见了呀。”
玉幼清摇摇头,“我想知道的是,你从谁那里听来的这蛊。”
她深而静的凝视着柳周舟,这双微微凹陷、眼窝略深的眸子,让柳周舟想起了一个人,不是画像里那个戏子,那戏子的眸子干净而专注,闪烁着淡淡喜悦和向往。而玉幼清此时看着她的样子,很像四五年前,父亲领着她去述京探望病中的祖君时遇到的那个人,彼时那个人也像这样盯着她,泛着醉态的、微眯着,可她还是从那双比女子还要美,流转间却又轻易就能令女子神魂颠倒的眸子里,看出了一丝藏的很深很深的沧桑,是尝尽世态的模样。
和如今玉幼清瞧着她时的神情,一模一样。
她皱皱眉,躲开这种让她觉得沉重的眼神,随手晃着腰间穗子,道:“祖君传下的医书中记载了这种蛊,我自小熟读医书,真正诊过的病人虽只是家中府丁嬷嬷,可每每娘亲收到鹤春堂递进府里的诊书时,我都会在旁侧学着。而且蚀阳蛊的脉象特别,绝不会错的。”
玉幼清低低“唔”了一声,垂下头靠在锦褥里。
“你不信我?”柳周舟望着她,有些急切,“虽说我不知你现在这情状是为何,可你确然中过蚀阳蛊,而且这蛊毒也已解了。”她越说越快,“如果单凭医书中所写,我大约也会再慎重一二,可祖君当年曾诊过这样的脉,我与祖君难得见上一面,那时凑巧得知,非常好奇,不依不饶缠着祖君好久,他才愿与我细说。这蛊世上罕有,医书所写难免不够详尽,我当时听得尤其认真,一字都不曾落下也不敢忘的。”
“你祖君是何时到的述京?”
“大齐天和八年。”
“一到述京就在太医署任职?”
“入京便是太医署丞。”
“从不曾为王孙贵族外的人看过病?”
“只为皇族,连王孙大臣都不得祖君一瞧。”
一连几句,玉幼清问得快,柳周舟答得更快,太着急想证明自己,以至于未经大脑脱口而出。
玉幼清却慢了下来,两个字拖得悠长,“所以……”
“所以你可愿信我了?”柳周舟扑到玉幼清面前,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满满期待的光芒,玉幼清平静如水的眸子缓缓移过去,柳周舟一愣,垂下脑袋心思复杂的一点一点退回去坐好,忽然有些不安。
玉幼清却淡淡一笑,明媚,如日光,这是柳周舟第一次看见她这样颜色,即便此刻的她憔悴,样貌甚至连普通都说不上,柳周舟的不安情绪被她这一笑冲散,听她语调轻快的道:“所以我愿意信你。”
“真的?”柳周舟瞬间展颜,还想说些什么,却听玉幼清下了逐客令。
“柳小姐,你……”玉幼清一时不知如何拿捏言语,伸手指指脖子,“去休息吧。”
片刻后。
惶惶不安的拥蕊不断拿眼角觑着玉幼清,自小姐将她叫上马车,便一句话也无,自顾自的拿着卫寻备着给她解闷用的棋盘,自己跟自己博弈。小姐再平静不过,可她就是愈发觉得这气氛不对劲,自己被自己吓得心跳如擂鼓,额间密密的沁出了一层薄汗,几次嗫嚅着要开口,小姐不是落子时敲得棋盘啪嗒一声响,吓得她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就是叹气摇头,三番五次如此这般,拥蕊倒是委屈起来。
玉幼清心思并不在棋盘上,她也压根不会下棋。不过是想磨磨拥蕊这小丫头的耐性,这丫头哪里都好,可就是胆子小,心思太细太杂,想要套话,直接问,是不可能刨得到根问得到底的。
眼见得这丫头的性子被磨得差不多了,她轻轻拈起棋盘正中一颗被黑子包围的白子,慢吞吞问:“拥蕊,你可有何事瞒我?”
“瞒、瞒?”拥蕊一愣,目光闪了闪,颤着嗓音勉强笑道:“我、我没有……”
“自己说!”玉幼清霍然加重语气打断她,眸光仍是平平静静的垂着,翻来覆去的看着手中的棋子,似乎那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珠。
风吹过竹林时,往往只听到竹叶沙沙声,却闻不见那淡淡清爽的竹叶香;风吹过花海时,往往只闻见各色浓淡花香,却听不到柔软如花瓣,也是有声可循的。
当这马车里的人,换作越苏拙时,玉幼清的双眸已冷若冰霜,再无半分颜色。
越苏拙收起嬉闹笑意,想了想上马车时,拥蕊抽风似的眼睛,“少夫人这是……”
“别叫我少夫人。”玉幼清脸色阴沉,愈想愈气,猛地一拂袖,面前棋盘上棋子顿时哗啦啦落了一地,有几颗险些弹到越苏拙脸上。自她病后,脾气也是愈发不可自控。
“该说的不该说的,拥蕊都已经说了,还有什么是连她也不知道的,嗯?”
越苏拙侧脸避开,心中暗损那丫头真是不经吓啊不经吓,半点沉不住气。转过脸来时已换了一脸谄媚,“少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知道拥蕊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拥蕊和少夫人都是女儿家,女儿家私下里说的悄悄话那我……。”说着说着,他声越来越小,话语越来越含糊扭捏,一双眼睛不知该看向何处似的在马车里乱转。
玉幼清了然一笑,堂堂雪狐卫,如果像拥蕊一样好骗,随口一诈就和盘托出,也不配站在楚云起身边,她看向越苏拙,凝视着他,“你不说,我来说。”
“雪狐卫自小和阿楚一起长大,他想查什么在做什么,你不知?”她沉下嗓音咄咄逼人。
“我不知。”他嬉皮笑脸蒙混过关。
“二十年前前朝楚氏一族旧案,先皇帝所中蛊毒为何,你不知?”她冷冷一笑把话挑明。
“我还在吃奶呢。”他唆唆手指装疯卖傻。
“柳周舟,祖君柳氏,当今的太医署令,当年的太医署丞柳阿图,你不识?”她气上心头提高嗓音。
“我连述京城门都没踏进去过。”他目光乱转声如蚊吟。
玉幼清怒极反笑,怪不得楚云起要换这么个人在她身侧,她此刻若还乖乖呆在他的温泉山庄里,恐怕连李平舟的面都见不上,更遑论从何处去知晓楚云起的动向。
越苏拙,还真的是很好啊。
一个表面吊儿郎当陪着笑陪着闹的人,却比当初玉府“牢笼”几十双眼睛还要滴水不漏。
她不想再与他打哑谜,直截了当问:“他在哪里?”
越苏拙乱转的眸子一停,随即笑看着她,撩起车帘一角。
远远的,拥蕊抱着纳兰连城,纳兰方觉缠着卫寻,扒着他的衣角似乎要抱,他似乎有些抗拒,时不时抬头看向马车方向,正瞧见车帘掀起一角,抬脚似要过来,拥蕊立即往他身前一挡。
“咳咳……”风钻入车里,玉幼清猛地一阵咳嗽,脸色涨的通红,直觉胸腔疼的厉害,肺都要咳出来。
越苏拙忙放下车帘,替她拍背顺气。
玉幼清掩着嘴,斜挑起眼瞧越苏拙,“咳咳……如果不是…不是遇上柳周舟,咳咳,你们…咳咳…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越苏拙唰一下心虚的缩了回去。
玉幼清气急,咳得愈发厉害,却挣扎着爬起来,哑着嗓子道:“好!那我自己去找他!”
身前人影一晃,越苏拙闷声不语拦住了她的去路。
玉幼清目光逼人,默然无声与他对峙。
半晌,越苏拙为难的劝:“少夫人,你现在这样……知道太多对你没什么好处。”
玉幼清本是爬姿,此刻气力不支,慢吞吞坐下。她唇角微微一勾,“雪狐卫以后都不必再叫我少夫人了,你也不必再这么窝囊的跟在我身边看着我了。”
“我……”越苏拙面色尴尬。
玉幼清笑意不减,“你到的前一日,阿楚就说,要搬去京郊的三营。我当时就觉得他有事,且如果不是天大的事,他绝不会撇下我自己跑走。当时我正生气,来不及再与他说什么,就又遭刺杀受伤,再醒来时我见到阿楚,还以为他知道我受伤,赶来陪着我。”
她抬眼看向车帘,方才越苏拙打开车窗后并未来得及合上,车帘随风一掀一掀,露出窗外墨绿的树,恍惚间那日林中她目之所及枝叶藤蔓缠绕,扼颈之感再次袭来。
“我醒来时瞧见阿楚,心里很开心。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都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合起伙来骗我。我不止一次怀疑他到底是不是阿楚,可我后来想想,或许阿楚真的有什么天大的事走不开,又想哄我开心,才派了人来,直到刚才。”
“柳周舟提到蚀阳蛊时我醒着,我想,二十年前先皇真正死因就是这蚀阳蛊,楚氏一族旧案能否昭雪,或许关口就在此处。所以,刺杀我的人,和这蚀阳蛊有关,和草原霍川部有关,甚至和当年那桩案子有关。此行草原,太巧。而那个人,在听到这些之后,却动了杀机。他不是雪狐卫的人,对吗?他是……”她停住,忽然不想说出那个名字,那个似敌非友的男人,那个每一次她以为他在一点点主动靠近自己时,却又一手将她推离千里之外的男人。
越苏拙看着玉幼清始终平静的脸庞忽起一丝波澜,看着她慢慢将头撇向一边,慢慢抬起手挡在眼前,长长宽宽的袖垂下,随着风微微起伏,仿佛她肩头的颤动也是风的作为。
她闷闷的声音从长袖后低低传来,“阿楚他……来看……来过,是吗?”
越苏拙还是没有回答,可玉幼清知道,楚云起一定来过。那熟悉的冷香,是旁人仿不来的。他,看见自己现在的模样了吗?他……不对!玉幼清脑中猛地闪过一丝异样,她刹那之间扑到越苏拙面前,急急问:“燕回!草原乱了!陆腾出兵北境,阿楚远述京任三营统领,卫寻称病不朝。”她说的很乱,脑中却已将这一些看似并不能连在一起的事串联起来,“他,他要护我,他要护我,他来看我,他来。”她重复念叨着这几句,心念电转,倏的抬头,“他先我一步去了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