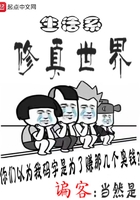萧南有瞬间图穷匕首见的错觉。
阿雪想问他的其实就是这个——阿雪一开始想问的其实就是三娘。萧南看了徐遇安一眼,不知道他为什么跟着苏仲雪胡闹。
萧南心平气和地说道:“我和阿雪有话要说,徐先生可以暂避么?”
他原可以找一万种更不留痕迹的借口,不必这样生硬和直白。但是这会儿他没有这个心情。
徐遇安行礼道:“殿下容我告退。”——他原该在苏仲雪质问宋王的时候就找借口退下去,给双方留足颜面,但是他没有。
或者说,一开始就不该跟着苏仲雪出现在这里。
萧南看着他退开的背影,心情有点复杂。
“殿下?”苏仲雪皱眉道,“徐先生也不是外人。”萧南“嗯”了一声,扭头看清音。清音哪里敢多话,默默然行礼退下。就只剩下他和苏仲雪。萧南这才说道:“……和是不是外人无关。”
苏仲雪冷笑一声:“殿下要乘人之危么?”
萧南奇道:“阿雪何出此言?”
苏仲雪:……
他居然和她装模作样、他居然和她装模作样!
萧南见她脸色都白了,也知道不能再与她胡说下去。阿雪的性子,又不是三娘,三娘还能与他你来我往调笑个几句——然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忙道:“眼下我自顾不暇,哪里还能乘人之危。”
苏仲雪面色稍缓,却还是哼了一声:“我问的不是这个。”
对,她问的不是这个,她问的是——他是不是还要娶三娘。他当然可以哄哄她,男人么,说几句甜言蜜语有什么难度。阿雪又不是别个,到头来她还能与他计较什么——但是他从来没有骗过她。
萧南沉默了片刻,说道:“如果我说——”
“嗯?”话到一半的戛然而止,任谁都要抓狂。
“如果我说,”萧南重复这四个字,眸光映着天光,涣散得像是回忆,“如果我说三娘她……是我的人呢?”
苏仲雪“啊”了一声,眉目里俱是惊色。整个人已经呆住了。她从未想过这个可能。她对萧南,一向都是放心的。
为什么不放心?他们之间,用多少诸如青梅竹马、同生共死、心有灵犀之类的词都不能尽述。兰陵公主又算什么呢,她见过的。她见过她,她没有她的美貌,更休说情分。他们之间有多少情分。
萧南并不是不知礼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轻重。他们之间这样亲昵,也都心照不宣地没有走到最后一步——除了礼教之外,未尝不是怕闹出人命。寄人篱下,他们一直活得小心翼翼。但是如今他说:“她是我的人。”
苏仲雪倒吸了一口气。
萧南的目光往下走,睫毛遮住了眸光。这让他的眉目看起来越发秀致和无辜。他知道苏仲雪误会了。
三娘当然是他的人。她一早就与他说过,他们喝过酒,成过亲,只是后来他南下,没有带她走——这一次不会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他都会带上她,不会留她一个人在洛阳城里,孤零零的一个人。
无论如何……
“什、什么时候的事?”苏仲雪难得的结巴起来。
萧南不作声。也作不得声。他不想骗她——何况一个谎言,要多少谎话要圆。
“是、是前年西山上么?”苏仲雪问。她当然知道那是一场骗局,一场针对于谨的骗局,但是她万万想不到——兰陵公主怎么肯?她后来、她后来不是还应了李家的婚约么?一念及此,背心发凉。
当然不会是之前,那之前,萧南甚至应了贺兰氏的婚约;那之后、那之后……苏仲雪没法想下去。
她从前也没有想过萧南只有她一个妻子。苏仲雪没有意识到她和萧南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她从来不觉得萧南会只有她一个女人,是因为他们要在洛阳立足,他们想借燕朝的兵,所以他们需要联姻——
她只想过那个女人应该是不如她,不如她美貌,不如她能干,不如她对他有用,更不如她与他的情分。
最好他一眼都不想多看她。
这样、这样……便是多一个人,她也可以假装骗自己说不得已。
但是这算什么!苏仲雪心里熊熊地烧着火,火烧得她思维迟钝,语声干涩:“那么,殿下是要带她走么?”
“……是。”萧南道。
“那么……”苏仲雪觉得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其实这个人是兰陵公主,她应该不意外才对,有什么可意外的呢,从正光四年的那个秋天开始,她还记得她的马蹄踩碎洛阳城里满地堆积的黄叶,沙沙。
那时候他和兰陵公主在一起。
那时候开始他就和兰陵公主反复纠缠,他图谋她,她拒绝他;他算计她,而最后落空;再之后他们联手,骗过了所有了,骗了于谨,骗过了贺兰氏,骗过了她,甚至骗过了姑母……骗过所有人。
她一定很得意罢,她冷冷地想。
正光六年之后,他就再没有说过要放手。这时候想起来,只觉得从头到尾都有迹可循,是她大意,是她以为他与她是一条心。
要不是有这些变故,没准这位还真能留在洛阳做驸马爷了!这些话在苏仲雪的胸口反复地响,反复的……没有出口。她说不出来,她从来都……说不出这些露骨的话。她也从来没有试过对他恶语相向。
一件事,但凡变成习惯,要改变过来,就都是不容易的。
譬如苏仲雪,思来想去,出口竟是极冷静的:“那么……殿下眼下就要开始做准备了。”
“……是。”萧南再应了一声。
苏仲雪扭头退了下去。她不知道她还能说些什么。她一早就说过她介意——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态度已经来得太迟。错的也许是她为什么还要问。她觉得她就该一记耳光摔在他脸上,或者吐一口血。
或者她该哭,像大多数小娘子遇见这样的事情时候的反应一样,悲悲戚戚地,捂住嘴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大约是她一早就知道,哭没有用。哭是所有行为中最没有用的一种——难道她想要换得他的怜悯么?
她苏仲雪何须人怜悯!
知道哭没用的也不止苏仲雪一个。嘉敏这会儿也没哭,她冷静得可怕——至少甘草是怕了,一声都不敢吭,跟着嘉敏进了明曜堂。
谢云然早就醒了。
应该的,她在孕中原就眠轻,何况出了这样的事。整个王府都在惶惶中,惶惶呼喊的婢子下人,惶惶奔走的部曲护卫,灼热的风,风里哔啵哔啵的响——那响声里充满了不祥的节奏。走水了。
这是三月,不是九月,天干物燥的秋。
这当然也不是意外。两军交战,哪里有什么意外。
四月和七月守在她身边,眼睛贼亮,寸步不离……直到嘉敏带着甘草走进来,所有人才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虽然三娘子未必就有什么好法子。但如今她是府里的主心骨。
“我做错了几件事。”嘉敏走到谢云然床边坐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谢云然心头一惊,勉强笑道:“混了细作进来?”
“是郑夫人。”嘉敏道。
到这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元明修并不是打算拿温姨娘做人质逼她出去,而是用来转移她的视线:姨娘没了,她焉能不悲,巨大的悲伤之下,又焉能不分神?她一分神,就是嘉欣的机会。
如今嘉欣烧了药材——却是谢云然日日安胎要用的。
谢云然点点头:“她待如何?”
“让我去面圣。”嘉敏说。
谢云然怔了一下:“三娘——”
嘉敏苦笑道:“不能不去——恐怕会留我在宫里,如此,府中就只有谢姐姐了。”她是来告别。
谢云然沉默了片刻:“不能不去么?”她当然知道是多此一问,但总还抱着一丝的希望。
嘉敏咽了口口水:“你放心。”
“三娘——”
“他不敢杀我。”嘉敏道。但是也不会放她回来。
“横竖父亲和哥哥还没有这么快回京。”嘉敏道,“总还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一两个月,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这一年的春天变故已经太多。
“没准宫里消息反而比府里灵通。”嘉敏说。
“而且姨娘……姨娘没了,总须得有人出面给她收敛。”那块玉佩是错不了的,嘉敏心里清楚。她不出面,谁能保证元明修不像前世萧南一般,任她挫骨扬灰。温姨娘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在他们看来。
谢云然一直没有说话。她当然知道三娘为什么不得不出府。或者她应该说“别去”——留下她!
但是她实在舍不得。
她舍不得腹中的孩子。
嘉敏握了握她的手:“姐姐保重——要等哥哥回来。”她说,“不要让我没法和哥哥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