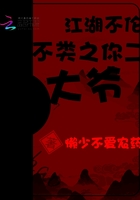“表姐把我绕糊涂了。”嘉敏说:“搅了陛下大婚的是吴人,行刺昭阳殿的也是吴人,陆皇后怨恨的,不该是吴人么?如果她都不怨恨原本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表姐,又有什么理由怨恨完全不相干的我呢?”
贺兰初袖看了她半晌,忽然说道:“三娘,你知道你如今人在哪里么?”
嘉敏环视四周,再一次。卧房并不大,除了当中极尽奢华的卧榻,就一张樱草色刻丝琉璃屏,她家中卧房里有长一色一样的,不过那屏上画的是山水巉石,这里是美人抱瑶琴,许是汉时昭君的典故。
窗下黄梨木妆台,雕饰得美轮美奂,台上明镜如皎,映着灯树里的火,青瓷美人觚里洁白一束月光花。
“是……凤仪宫?”嘉敏说。
“是凤仪宫,我从前住过的凤仪宫。从前,我得了好东西,总会给你备一份,所以从前你进宫,都住在凤仪宫里。”
不是玉琼苑。
嘉敏呵了一声,不以为然。
“三娘你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辰了?”
嘉敏看了一眼墙角的沙漏。其实不必看,她也知道天快要亮了。天边最远的地方,已经依稀可以看到鱼肚白,月亮残成一弯,越来越薄的影子,越来越薄,等待红日的一跃而出,金光万道。
“我并没有参与这件事,陛下固然信我,也未尝不防着我,毕竟,我是在府里长大。我娘亲至今也还在府里。所以我当时知道得并不多,我也是后来,一点一点拼凑起来。应该就是这时候了,报信的人已经出发,是高阳王。三娘你还记得高阳王么?”
高阳王,嘉敏记得这个人,是孝文帝的弟弟,论辈分,她须得喊一声“叔祖”。先帝时候颇为受宠,权重一时,富贵盖京华。据说洛阳能与他斗富的,就只有咸阳王。当然咸阳王的名声又不一样了。
原来是他。
明知道迫在眉睫,嘉敏也忍不住自嘲地笑了一笑:“陛下糊涂,我产子这么小的事,何至于劳动高阳王叔祖!”
“以姨父如今的权势,何人不谄,何人不媚,”贺兰初袖冷笑道:“高阳王又算得了什么,就是陛下亲至为贺,姨父也当得起。”她这时候已经改口说“如今”,不说“从前”,显然是默认了她们的处境。
时隔太久,嘉敏其实已经记不起父兄当日的权势,她并不曾因为权势受过委屈,自然也不会在乎,就好像大富之家的小儿,不会在意钱财多寡,虽然多总是好的,但是因为没有缺过,也就不至于汲汲以求。
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权臣阴影下度日如年的皇帝的妻子,贺兰初袖想必深有体会。
“眼下高阳王已经骑马出了宫城。”贺兰初袖说。暗夜里,并不能听到马蹄点地的声音,也许是隔得太远,凤仪宫里静得出奇,呼吸急促起来,姐妹俩不约而同想起十年前的晚上——对嘉敏是十年,对贺兰初袖,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高阳王出了宫城,往北走,抵达王府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姨父被高阳王的叩门声吵醒,十分不悦,他说,如果高阳王禀报的事情不能让他满意,他就用床头的斧子砍下他的脑袋……”
嘉敏不说话,这确然是父亲的口吻,她还记得。人在得志之后,人在得志多年之后,心境和举止会大不同于从前,就好像她从前认识的周城,和后来瑶光寺里周家的车夫不是一个人一样。
“高阳王说,是好消息,大好消息,他是来恭贺宋王妃弄璋之喜。”
宋王妃弄璋,不去送王府报喜,反来南平王府,那自然是因为南平王父子权势。
但是嘉敏只是个公主,嫁的又是异姓王,就算是生儿之喜,也不至于劳动宗室里辈分最高的高阳王。
南平王心里不是没有疑惑,但是高阳王轻佻地摘下他头上的帽子,舞了个回旋,无尽欢欣的神态,终于让南平王终于放了心——高阳王原本就是谄媚之辈,为了讨好他,弄出这么大阵仗来,并非不可能。
当然贺兰初袖并不敢把这一段说给嘉敏听。
“……然后姨父和表哥就轻车简从,跟着高阳王出了门,快马加鞭,往南进宫……”
夜色一丝一丝地被风抽尽,马蹄出了王府,声声,埋伏在乾安殿东门的鬼影幢幢,等候的煎熬,丝毫不亚于苦战的疲倦。
“不要再说了!”嘉敏忽然尖叫一声,她知道后来,她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必贺兰初袖再往下说,她猛地站起,又被贺兰初袖按住双肩:“姨父和表哥就在进宫来的路上,三娘,你还是不肯说么?”
“说、说什么?”嘉敏一时气短。
“说实话呀,”贺兰初袖压低了声音,就像是刚刚从轮回之地上来,还带着地狱的幽冷,那些话,那些字眼,经她的薄唇吐出,滋拉拉燃起一簇一簇的鬼火:“说实话呀,三娘……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
“你看这里,”贺兰初袖指着窗外,天色暮蓝,大多数星子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只有她们头顶的那颗,还散发着黯淡的光芒:“你看到了么,那是陆皇后,她没有走远,她就停在这里,在这里看着,在这里等着,三娘,你还不忏悔?”
“我……”嘉敏咬唇:“表姐要我忏悔什么?”
“没有时间了三娘,没有时间了!马儿跑得有多快,从王府到宫里,只需要半个时辰,再等等、再等等你就会听到马蹄的声音……如果、如果不能够得到她的原谅,你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何止是马蹄的声音,也许还有战鼓的声音,敲在每个人心里,咚咚咚,咚咚咚!
刀在鞘中低鸣的声音。
还有后来,血手攀上马车血手,惊鸿一瞥那张狰狞的面孔……是哥哥,是她的哥哥!
父亲已经找不到了,最后哥哥也没有找到,她没有能够为他们收尸,因为都碎了,所有人都……碎了。
撕心裂肺的恐惧,一滴汗,从嘉敏额上滚落,“啪嗒”打在地上,浅浅一个水坑。
背心已经全湿了,还有头发,头发湿漉漉地搭在额上,她知道自己的脸白得像鬼:“表姐到底要我忏悔什么?”
——如果忏悔能平息灵魂的怒火与怨恨,如果忏悔能令死者安息和离去,如果一切能回到从前,如果,如果,如果只是如果。
惊惶与混乱,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嘉敏咬紧牙关,是谁说过的,要逆天改命?
“前日陛下与皇后大婚,皇后绣衣上的凶谶,难道不是你做的么!”不肯说,还是不肯说,贺兰初袖多少有些懊恼,她死死盯住嘉敏的脸,盯住她的眼睛,她的眉,她每丝每毫的表情。
她就不信,到这一步,她就不信她还能扛得住,躲得过。
她早就该死了,贺兰初袖默默地想,前世如果不是南平王父子前脚进宫出事,后脚萧南就进宫接人,她当时就该死在乱兵中,和她的父兄一起死在乱刀之下,没有后来……后来近十年的好日子。
她不会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
“表姐凭什么认为是我做的!”嘉敏抬头来看着贺兰初袖:“我和陆皇后无冤无仇,我这样做了,能有什么好处?”
“在皇后死前,曾经召谢娘子进宫问话。”贺兰初袖说。
谢云然……嘉敏一怔。
“谢娘子说,她在陆皇后的赏花宴上出事,三娘很为她打抱不平。”话到这里,贺兰初袖语速忽然加快,容嘉敏开口,继续说道:“……尚衣局的绣娘,还有……瑶光寺里的素娘和……半夏,她们、她们什么都说了。”
“说了什么?”嘉敏只问。
“说了……是三娘你的指使!”贺兰初袖于忽然之间怒气勃发:“三娘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就算是陆皇后不慎导致了谢娘子的毁容,如今君臣名分已定,她是君你是臣,你这样做,于君是不忠,于友不义,于姨父是不孝,于天下人不仁,三娘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不忠不义不仁不孝的事!”
话音才落,就听得“怦”地一声,门被踹开,有人大步进来,一把揪住嘉敏的衣襟:“原来是你!”她说。
嘉敏前后这两生,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怨恨,怨恨近乎诅咒的声音。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偏头,躲开风驰电掣一记耳光,同时叫出声来:“陆皇后!”
是陆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