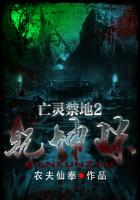第15章 捕魄幻手1
“清净如水,洗诸尘垢,雨甘露法。淳净温和,寂定明察,永离三垢,游戏神通……”烈日当顶,静风无痕。彭雨斋手捻长须,闭目微笑,口中念念有词,玉树临风,仙风道骨。
石坚席地而坐,按彭雨斋指示盘腿而坐。
“青颜,彭伯伯嘀嘀咕咕在念叨什么呀?”肖萍问。
“我也不大清楚。师父只是教我背熟了那些话,说以后在修炼时我会自己明白的。”青颜说。青颜是彭雨斋在谷边林子里拾来的弃婴,听彭雨斋说这孩子颇有些来历,当时彭雨斋抱养他时,他正躺在一个小竹篮里,一匹母狼正在喂他奶。此番彭雨斋收石坚为徒,按彭雨斋的规矩,青颜就叫石坚为师哥。
“哦。”涉及到修炼,肖萍知道这是不便问的。只能这样含糊地应一声。肖萍眉头紧锁,焦虑地望石坚一眼,又试探地望向彭雨斋。
彭雨斋不着痕迹地把头一偏,没有表情。继续到:“平心静气,心无尘染。石坚,怎样才能做到心无尘染?”
“师父,不静还不觉得,一静下来更觉得心乱了。”石坚老实作答。
“当然,你我凡夫,岂能无动于衷。老夫也是历经艰难困苦时身心极度疲惫、极度绝望时顿有所悟——那时想着豁出去了——忘却了身躯,忘却了性命,却反而激得一股心力场能出来。”
“可我忘不掉我自己啊。”
“啪!”彭雨斋当头一棒,石坚吃痛,重新坐直,听彭雨斋继续道:“万法本空,我们所见所感皆由自心幻化而生,能量亦然。生老病死、幻海沉浮,全系与心。每个人自身即为一个巨大能量的聚合体,但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罪。人不能自见真性,概因这些世间烦恼遮盖。
古往今来,多少世间人梦寐以求出世间的妙法,但学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幸得我佛慈悲,当年鸠摩罗什法师在中土传译“禅秘要法’中所的“不净观’和“白骨观’的技术,贯而通之,神而明之,虔诚制心修习,自然有拨云见日之时。”
石坚、肖萍听得昏昏欲睡,又不敢弄出动静,只得耐住性子。
“这是第一课。”彭雨斋不动声色,语气平缓地说:“昨日老朽已然告知,生物场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婴儿阶段尚能风雨不侵,这是因为场能充沛的缘故,只是他们不知使用而已。为什么场能显露?因为他们不知道恐惧、荣辱、真假、善恶,率性而往,往而无不利,这就是《易经》“元、亨、利贞’的意思。”
“师父!这就是您适才说的“淳净温和,寂定明察,永离三垢,游戏神通’之意吗?”青颜在一旁嫩声嫩气地插话。肖萍听他半文半白的说话风格就有点想笑,想必是从小只有彭雨斋相伴才至如此。
“乖徒弟,聪明。”彭雨斋满脸欣慰,接着说:“为什么人成年了,反而丧失了大部分使用场能的能力呢?因为成年人知道恐惧、荣辱,畏首畏尾……太爱自己啦!所以没有场能的对象化作用,所以第一课就是教你舍弃自我。第一步,“不净观’!”
肖萍见开始了真正的授课,拉了拉青彦的衣角,悄然离开。
“石坚!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臭皮囊。你可知否?”彭雨斋问。
“知道,师父。”石坚答得倒是脆生。
“知道?好!这就是教你认识臭皮囊的方法:专注一念,系念左脚大拇指上,观想大拇指前半节,如死后之初起溃烂,淤青紫涨,臭不可闻。”
石坚经历坎坷,解放前战事不断,从小见过的尸体无数,现在一闭眼,那些被日本人飞机炸得肠子一地的平民、血肉横飞的士兵、饿死在路边的腐尸跃然眼前,蝇蛆密布,蚊虫缭绕,一阵恶心。
“专念观想脓胞溃烂,化成脓水,露出了白骨,继而放出白色光芒”
石坚似乎闻到了尸水的味道,他熟悉这种味道,而此时却来自自己身体的内部。
“既见白骨,再反观依次使整个大拇指的肉,分裂开来,见到大拇指节的全节白骨,绽放白光。”
石坚想象着自己脚趾上的肉劈成两瓣,腐烂脓血,“滋滋”外翻,从骨头上褫落下来,恶臭熏天,苍蛆滚落,密密麻麻。
“哇!”一声,石坚吐了,使劲儿睁眼,却发现眼前漆黑,伸手抓握,却是是爪爪落空。折腾片刻,失去了知觉。
“石坚!石坚!你这是怎么了?”石坚躺在肖萍怀里。
“快!我兜里有药。”石坚满脸通红、脑门青筋暴露。他的老毛病又要犯了,心率过速,血压升高,本能地到衣兜里摸他随身的小药丸。肖萍帮他把药倒出,放进嘴里含着。
“哦?小子,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广的见识。”彭雨斋从容观察,不为所动。石坚正想我见的死尸多那是倒霉,怎么还成了“见识”了,又听彭雨斋说:“如此一来,倒是省去了许多不起观想的麻烦和过程——越快观成身不净,便越快破除我执,也便越快开发出你的场能。”
“师哥,我当日开始的时候用了很长的时日,后来师父烦了,才带我到了林子边坟地里刨死尸出来给我看,才起了观想。”青彦在旁鼓励石坚。
“咦?小子,待老夫把脉一观。”彭雨斋正想接着说,突然不说了,显然是看到了石坚身体状态的变化,上前掰开石坚的嘴巴,然后又抓起石坚的手腕,喃喃道:“嗯……面红目赤,舌质红绛,苔多黄腻,脉象弦滑,小子,你这是阴虚于心,阳亢于上,你平日里可曾心率过速?杀气怒号,不避亲疏?”
“是,师父……这毛病好像从记事以来就有了,后来我找医生看,医生说我这是一种病……”石坚从肖萍怀里坐起。
“病?”彭雨斋的表情更怪了。
“医生说我得了心脏病,那名字有点饶口,好像是个洋名称,不记得了。”
“哦?”
“医生说我心率过速、血压过高……”
“庸医!庸医!老夫明白了,你以后不用吃药了。”彭雨斋胸有成竹地说。
“医生说……”
“那是常人。老夫问你,你的“病’发作之时,你心率可达300、400?气力倍增,反应更快……你会做出异于常人的事?”
“好像是。”
“比如?”
“比如我能一把就逮住跳在空中的跳蚤。”
“比如你能和花猫贴身肉搏,差点弄死了这宝贝,而你自己只是受点皮肉伤,而且那还得是在你身中蛇毒的时候……哈哈哈哈!”
“嘿……”石坚抓自己的头皮。
“天意天意!你这根本就非心脏病!却是世间罕见的“双Y基因’,每逢应急状态,你的雄激素灌满你的血液,肌肉强度增强,脑子超常运转。如此天赋的人,天下也没几个。我见过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肖萍的父亲秦汉之。”
“啊!”肖萍一声惊叹。
“从今以后,你可以通过控制你的能量来控制你自己,需做到收放自如。”彭雨斋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也隐隐有些担忧。
“是,师父。可是真的很难。”石坚当然注意到了彭雨斋的担忧,闷声应答。
“废话!老夫这不正教导于你吗!”
接着几天,彭雨斋陆续教授“不净观”中的各种观想法,从脚趾到脚,再到腿、腰、肩、头等,从上到下;又从毛发到皮肤,再到黏膜、肌肉、内脏、骨骼等,从外到里;观想也变着法一次比一次恶心,从化脓到腐烂,从腐烂到生蛆,从生蛆到虫噬,从虫噬到互噬,脓血遍地,恶臭难当……极尽恶心之能事,把石坚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由自主地讨厌自己这个臭皮囊。周遭万物,入眼尽皆白骨,甚至看师父、肖萍等人都是一副白骨,害得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晚上还有功课。
黄昏时节,夕阳透过丛林的树叶缝隙洒向山谷,山谷里斑斓绚丽,为金字塔像披上一层金黄锦绣。
金字塔里光秃秃的石桌上,一个简易架子上悬挂着一颗用线吊着的蚕豆,石坚的两眼紧紧盯住它,在烛光的照耀下,石坚的眼珠闪闪发光,任由眼泪兀自下流。肖萍手拄腮帮,微笑着看着石坚,烛光使她的脸透出一层橘红的光晕。这是彭雨斋布置的晚自习,让石坚盯着这颗蚕豆,不借助任何外力,用意志力将豆子驱动。可是,无论石坚如何努力,豆子总是纹丝不动。
“肖萍,你父亲是什么人啊?好像是什么大人物?”石坚和肖萍从认识起就开始了亡命奔逃,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更别说详细问起肖萍的情况,目前对肖萍的了解都只是从一系列神秘的事件和她与彭雨斋对话的片言只语中得到的,越是这样,肖萍的身份就越是成了一个大问号。
“唉……之前你也听我和彭伯伯说起过,当时我父亲在北京,彭伯伯在上海,都是富可敌国的成功商人,当时在商界素有“京秦海彭’的说法儿。我父亲解放前夕因为与国民政府过往甚密,所以去了台湾,临行时阴差阳错,把我们母女撇下了。”
“那你是咋被郑寒他们盯上的?又咋跑到我们热谷县来的?”
“解放后我随我妈隐姓埋名,我妈在糊纸盒的街道合作社上班,供我上学,日子苦些,倒也平淡。没想到文革开始后,我们还是被揪了出来,我就“顺理成章’做了“黑五类’,唉……”肖萍神情黯淡,泪眼婆娑,石坚知道这一声叹息意味者什么,但一时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听肖萍顿了顿,接着说:“后来有一天,有两个人找上门来——哦!对了!其中个高的那人你见过,就是铁路上跟着郑寒的那个年轻人,问我要我父亲保存的一本书,说只要把书交出来就可以帮我和我妈“摘帽’。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当时只是“摘帽’心切,就问我妈要,我妈也不知道那书的下落。他们不信,把我绑架了,要挟我妈拿书换人,后来……后来,我乘他们路边停车解手的机会从吉普车里逃了出来,误打误撞上了知青的列车。后来……后来就碰到你了。”
“一本书?有那么重要?”石坚狐疑地问,突然想起了路生说起的“那本书”。现在看来,一系列怪事逐渐在脑子里联系起来。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叫做《大空幻化正观》的古书。我父亲离开大陆时我这不还小呢嘛,听大人说事儿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
“估计这书被农场的一个滩洲知青叫杨路生的得了,后来又丢了,郑寒怀疑是在普桂芝身上,所以一路追来。”石坚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这好端端的搅进浑水了。”肖萍忧心忡忡。
“哈!我最不怕的就是搅浑水!”石坚豪气地说。
石坚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的,早上起床就继续修习“不净观”。午饭稍事休息后,石坚要上山打柴、下田薅草、铲草锄地……当这些事做完后,石坚以为可以歇口气的时候,又被彭雨斋唤去做别的事,那感觉,就像是彭雨斋故意挖空心思要整治石坚,决不让石坚有片刻喘息机会。石坚从小吃过无数苦头,知道彭雨斋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也就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倒是肖萍看不下去了,几次卖乖撒娇,求彭雨斋让石坚休息会儿,但彭雨斋总是顾左右而言它,太极推手似的把肖萍的请求推到一边去了。石坚身上的几处旧伤再度复发,背上开始生疮,下田劳动时,惹得蚊蝇环绕,在伤口处产卵,过上几天,蝇蛆密密麻麻从伤口里爬出来,恶心之极。肖萍一开始为石坚清理伤口时,呕吐了几次才清理干净。可是,一个创伤才好,另一个又迫不及待长出来,此起彼伏。
晚上,那个盯蚕豆的、极为乏味的功课要持续四个小时。这样,石坚即使在闭眼睡觉的时候,也感觉老是有一颗蚕豆在自己的眉心中央滞留,怎么也消融不了,而最致命的是这些幻象引发的头痛欲裂。
而彭雨斋不安地发现,石坚的毅力、意志力都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意味,他做任何事,都似乎在和谁较劲,完全是种玩命的做法。有时甚至是一种自虐式的自我折磨,这让彭雨斋的担忧逐渐加重。
在受难式的魔鬼训练的同时,一股清泉正悄悄在石坚的心田流淌,滋润着他这颗干涩的心。等石坚察觉时,它已经变成了疯狂滋长,几近失控,而这对于石坚来说是不被允许的。石坚试着不去想这事,但事与愿违,他越是控制这种感情,它就越是泛滥,以至于只要离开肖萍一会儿,他都会如此急切地想念她。这种强烈的想念被肖萍那种若即若离、淡漠得近乎诡异的气质反弹得越发强烈,那是一种深谷里的花开、自顾自的美丽,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幸亏彭雨斋因为要让他俩尽快恢复体质,就让他们住在金字塔里,那两张石床刚好让俩人一人睡一张,这才得以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这天夜间,发生了一件对于石坚和肖萍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大事,这事无可挽回地注定了镌刻在俩人一生的生命里。当时夜已深,石坚和肖萍都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毫无先兆地,俩人的体内突然涌出强光,在空中盘旋片刻,凝成两根光柱,然后忽然缠绕在一起,充分混合后,最终合而为一,飘荡游弋。俩人赫然惊醒,混合后的光“哧溜”一下钻回俩人体内,俩人猛地坐起,对望片刻,然后同时说:“我梦见你了!”
第二天,俩人都缄口不提这事。肖萍依然为为石坚清理伤口,眼看伤口里有些滞留的脓血难以清理,肖萍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忽然俯身凑上嘴巴,用力吸允,一嘴脓血,然后用舌头为石坚舔净伤口,“我爸说唾液里有丰富的生物酶,有助于伤口恢复——你没见小猫小狗会舔伤口吗?”石坚惊得半天反应不过来,然后坚持不肯,却拗不过她的倔强。这以后,她会整天整天地在一旁陪石坚修炼,只要是被彭雨斋允许的,她都不离左右,尽管那样做十分乏味;肖萍会把石坚的头抱在怀里,亲吻石坚的额头,那正是石坚那颗“蚕豆”怎么也融化不了的地方,“我帮你把它吸出来吧”肖萍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肖萍会拄着腮巴仔细地看石坚的眼睛、鼻子、头发,“啊呀!原来一个毛孔是可以长几根头发的!像牙刷一样,先前儿我还以为一个毛孔只长一根头发呢!”肖萍有新发现的时候就会大呼小叫,弄得石坚难以集中精力;肖萍会估摸着石坚口渴的时候,自己用嘴巴含满一口水,然后渡到正在用功的石坚的嘴里,“这样你就不用浪费时间起来喝水啦”,但实际上扰得石坚更加无法集中精力了,而石坚吞下肖萍口中的水也如饮甘露,这时候,肖萍还会趁机把石坚的舌头含在嘴里来回裹动,像吃糖似的津津有味;肖萍会不时为石坚拉拉打折的衣领,整整不对称的袖口,掸一掸头发上的尘渣……肖萍能清楚地记得和石坚在一起时的每一个细节,会把每一天都当做纪念日……在这世外桃源般的谷里,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丝毫喧嚣,俩人朝夕相处,彼此早已在对方生命里悄然生长。爱情的滋润使石坚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从小磨砺得铁石心肠的性格也不知不觉增添了许多柔情。
这一天,石坚又开始上山打柴,在山腰上一颗榕树下坐下歇息。秋高气爽,一些不知名的叶子已然变黄,穿插在浓郁的墨绿色背景中,使山谷呈现出丰富的层次。蝉鸣鸟叫,松涛柏浪。此时尽管离彭雨斋交给的工作量还差得很远,但石坚还是再也抵御不住疲倦,不知不觉睡着了。
睡得正香,梦里依稀感到被人反剪双手,“咔嚓”一下自己的牙齿就啃到了地上的土。还没睁开眼,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小子!你真他妈命大!居然还活着!”
石坚的脖子被一只脚踩着紧紧压在山草上,只能斜眼看地上的投影,一顶鸭舌帽跃入眼帘。
“郑寒!你蓄意谋杀,应当主动自首向人民谢罪!”石坚突遭变故,正不知所措,胡乱虚幌一枪再说。
“哈哈哈哈!石坚,你以为你谁呢?还一副县长腔调。那杀人犯不是你吗?你正受到通缉呢!说!普桂芝在哪?肖萍在哪儿?”
“凭什么告诉你!”
“凭这个!”郑寒的身影移过来,蹲在了石坚的眼前,这回石坚看清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和枪口后面的狰狞面孔。石坚心想这杂碎也同样命大,居然没死。
“郑队,杀了他就更没办法找了。”压着石坚的人说话,石坚听出就是那个杨大勇。
“少罗嗦!闭上你的鸟嘴!”郑寒“咔嚓”拉开枪栓,把枪使劲往石坚脑门上顶,咆哮道:“说不说!”
石坚正想破口大骂,但奇怪地感觉到枪口颤抖起来,踩在脖子上的脚和反剪自己双手的那双手也慢慢松开了。
石坚翻身坐起身,眼前伫立着一个衣着奇怪的伟岸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