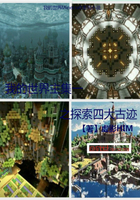“奴婢见过将军。”二人同时出声屈膝行礼。
寒烨昭看着两个人,没有说话。
邵以南一个外人,自然更不好搭腔。
水红色的可人儿抬眼,飞快地看了寒烨昭一眼,脸上就飞起了红晕。
淡紫色的人依旧冷若冰霜,低声道:“奴婢是奉夫人之命前来,看看能不能帮忙打点一下。”
寒烨昭道:“免了,回吧。”
两人应声称是,离开前,抬眼看了看期云阁的屋宇,目光颇为不善。
邵以南沉吟道:“你大张旗鼓地迎慕容蝶舞进门,就是要她死无葬身之地么?”
寒烨昭反问:“你怎会这么想?”
邵以南啼笑皆非。
出阁当日,蝶舞整个人没精打采的,起床梳洗就耗掉了半个时辰。之后就屋里屋外晃来晃去,看看这看看那,晃得两个丫鬟心慌不已。
中午,吃了几口东西,有修面的妇人来为蝶舞开脸、绞眉。
蝶舞坐在窗前,神色有几分恍惚。这一日的天气难得的晴朗,细细碎碎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她的脸上。
妇人满脸堆笑,行礼后,将螺钿盒打开,把妆粉器具一一分放在桌案上。
蝶舞看到妇人往白瓷碗里倒了大半碗的****,心生好奇,问道:“这是什么?”
妇人笑道:“回小姐的话,这是芽灰粉。”
含桃站在蝶舞身后,帮她把碎发往后梳起用簪钗别住。
妇人拿起粉扑,自蝶舞的额头至下颚,均匀的扑了芽灰粉,又拿出一捆白色细线来,将线套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上,俯低身来。
蝶舞有些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她其实很想全程观看开脸的每个细节。
妇人的力道很轻柔,动作很迅速。
蝶舞的唇角绽出一个似有似无的微笑,这种肌肤被人小心轻柔地对待的感觉,几乎可以称之为享受的。
妇人停下动作,把蝶舞脸上残存的粉末洗净,笑着告辞。
蝶舞为着她那份谨慎轻柔,特地吩咐含桃多赏了些银钱,妇人千恩万谢而去。
走到镜台前,蝶舞看着镜中的自己,呆愣了片刻。不过片刻光景,这张脸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不过是脸色愈发白净了,柳眉的眉形愈发清晰了,却使得整个人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端秀。
之后,又有专门负责梳妆的人来了,服侍着蝶舞梳妆、换衣。
穿上粉红色褙子的那一刻,蝶舞的心,还是一点一点的疼了。两世为人,没机会穿意味着纯洁幸福的白色婚纱,没资格穿代表喜庆吉祥的大红嫁衣。粉红色,谁能告诉她,这个颜色究竟意味着怎样的生涯?
从今往后,她只是只比奴仆的地位略高一等的妾。生而无名分,死后不留名。
有些东西,近在眼前,你不要,是洒脱;有些东西,也近在眼前,你被迫接受,是不甘。
傍晚时分,吉时将至。蝶舞去到前院,拜别大老爷和顾姨娘。
大老爷面容分外疲惫,数日间已苍老了几岁。顾姨娘似乎连哭泣的力气都已失去,明眸已无光彩。
大老爷说了几句叮嘱的话,把手边的一个精致的锦盒递给蝶舞,“这是我和你姨娘的一点心意。日后,你……你万事谨慎。若有难处,就写信知会我一声。”
“女儿谨记。”蝶舞站起身来,抬眼凝视着面前的两个人,眼角慢慢蓄积了泪水,缓缓滑落到腮边。是身体不受控制的本能的反应,还是心魂因为别离而难过不舍,她分辨不清。
罩上盖头,蝶舞在丫鬟的搀扶下走至青布小轿前。
府门外已经汇聚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她只迟疑了片刻,便上了轿子。
她的泪水,她能流露出来的伤悲,从来就有限。况且,此刻没人会在意她的不舍她的不甘。人们要看的不过是这个过程,留待明日当做茶余饭后的趣闻。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又都是错的。既如此,不如随心。
有人在一旁恭声道:“将军,吉时已到。”
“走吧。”言语简短,语声动听之余,毫无温度。
寒烨昭?他亲自来迎她入门?蝶舞吃了一惊,这个人,是嫌这笑话闹得不够大么?早就听说他是以娶妻之仪筹备纳妾之事,那时她只觉得他多此一举,即便如此,谁又能高看她和他一眼少一句讥笑?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闲得没事亲自前来,带着她在京城转着圈子现世。
在震耳的鞭炮声中,轿子被抬起,道路两旁的议论声愈发嘈杂刺耳。
蝶舞在心里捣鼓着记忆中有限的几句圣经箴言,以求不闻轿外语声,速速结束这场灾难。
几匹快马自轿子后方赶来,马蹄声渐渐放缓,尾随在后面。
“断袖将军花痴女,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有人忽然高声喊了这么一嗓子,继而,几个人哈哈大笑。
轿子停了下来。
蝶舞死的心都有了。她曾在学校大礼堂千余人的注视下走到台上领奖,她曾数次召开董事会、员工大会。她习惯了被羡慕、被嫉妒、被仰视,如今在当街众目睽睽下成为笑柄,足够令她抓狂。
片刻后,她就觉察到了异状,走在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数以千计,一路喧哗,此时竟全部噤声,整条长街鸦雀无声。
寒烨昭的语声不急不缓地响起:“把他们几个绑了,送到宫里去交给圣上。”
“是!”几十道男声齐齐应道。
就有人喝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