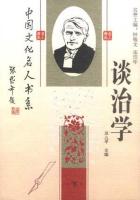寒烨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早她淘气地说的那句不许洗脸,脸上的表情就不自觉地柔和下来。
“你看看,说到你心里去了吧?”钟离睿心安理得地笑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有时间朕也跟太后说说话,让她别总见四郡主。”
寒烨昭道谢之后,又道:“臣最近分身乏术,皇上能否让邵将军助臣一臂之力?”
“邵以南?”钟离睿一口回绝,“你想都别想!朕不把他弄得服服帖帖不算完,再说,他一个想辞官的废物能帮你什么忙?”
寒烨昭不说话了,知道这君臣二人不耗出个结果来是不会罢休的。
“加你俸禄,就这么定了。”钟离睿拍拍寒烨昭的肩膀,兴冲冲地赶往南书房。
邵以南站在龙书案前,昏昏欲睡。昨夜就被钟离睿宣进宫里,一直就这么站着,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钟离睿走进来落座,故意板起脸来,把一摞奏折丢给邵以南,“你给朕看一遍,言官进谏的就先放到一边,关乎军情民情的挑出来给朕过目。”
邵以南勉强睁开眼,“启禀皇上,罪臣想洗把脸。”
“去吧。”钟离睿促狭地笑,“需不需要沐浴更衣?”
邵以南打了个呵欠,甩甩头,拿起一份奏折,“罪臣这脸,不洗也罢。”心里第一千零一次咒骂着钟离睿。
钟离睿不以为意,指了指下手的椅子,“坐吧,站着碍眼。”
邵以南坐到椅子上,困意更重,“罪臣想喝杯酽茶。”
钟离睿点头,唤来宫女,继而埋首处理朝政,偶尔抬头看一眼邵以南,心里直笑,只要身在宫中,自己就是九五之尊,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倔脾气。
中午、晚上,钟离睿命邵以南陪坐一起用膳,晚膳席间两人一起喝了几杯酒。
宴席撤下,邵以南实在是受不了了,跪拜行礼,道:“罪臣恳请皇上隆恩,允罪臣回府稍事休息。”
钟离睿却指了指里间的龙塌,“累就去眠一眠,回府之事,你就别想了。”
邵以南婉拒道:“罪臣不敢。”
钟离睿眼睛也不眨一下,“这是口谕。”
算你狠。邵以南心里恶狠狠地骂着,你个混球,这笔账早晚跟你算清楚。
钟离睿掐算着时间,先去太后那儿坐了坐,母子二人说了会子话。提起寒烨昭之事,太后道:“四郡主说烨昭独宠一房妾室,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妾室这许久也无喜讯。”
钟离睿笑道:“烨昭一个断袖,你让他从哪儿去弄什么喜讯?他歇在哪儿,也就是做做样子。”
“哀家不管他怎样,既有妻妾,就得安安稳稳过日子。再者,他最近不也没胡来么,言官最近都闲得发慌了吧?”太后眉目间尽是笑意,“人哪,这年岁不是白长的,连你最近也一心扑在国事上,稳重了许多。哀家总算是能松心了。”
钟离睿看着太后的笑脸,开始很悲观地想象她痛哭流涕会是个什么样子,不由得叹息一声:“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
太后问道:“何事不能两全其美?”
“世事大多如此。”钟离睿敷衍地笑笑,又把话题扯回到寒烨昭身上,“母后,您日后还是别管烨昭的家事了,他是八尺男儿,府中之事自然不会跟您提及,四郡主与您说什么,也不过是一面之词,您若事事遂了她的心愿,烨昭的后院怕是就要起火了,如今正是指望他为国效力的时候,还是不要让他分心为好。”
太后并不认同,道:“八尺男儿,我朝栋梁,能安邦定国,自然也能做好一家之主,他不说就是不值一提,或是无事可说。”
钟离睿笑道:“母后既然晓得烨昭能做好一家之主,就更不需为他劳神了。”说完又强调,“如今战事在即,处处都指望着他,朕实在是不想出任何差错。”
“他那个性子,刀枪不入的,能出什么差错?”太后和蔼笑道,“好了,哀家记下了。我如今也是关心则乱,这段日子就多见了四郡主几次,日后一心礼佛便是。皇上以大局为重,哀家欢喜还来不及,自然不会节外生枝。”
“如此甚好。”钟离睿此行目的达到,笑容分外清朗。
“你和烨昭都是一副样子。”太后眼中有欣慰亦有遗憾,“大事当前就格外有担当,国泰民安时就一味胡来,真不知说你们什么好。”说着担忧地叹气,“待你们闲下来,可别又闹出什么笑话来。”
笑话是一定会闹的!钟离睿心里重重点头,言辞却不敢现出分毫,又和太后寒暄几句,告辞回到南书房。
宫女太监毕恭毕敬站在书房门外,不管皇上在与不在,都是丝毫也不敢懈怠。他们知道,睡在龙塌上的邵将军如今可是皇上最惦记的人,每日都把邵将军的名字挂在嘴边说上几十次:
“邵以南那个欠打的混账东西……”
“邵以南那个要辞官的废物……”
“邵以南那个不争气的祸害……”
虽没有一句褒奖之词,却从不提及治罪之事,证明邵将军还是被皇上极为看重的。因而,皇上不在时,他们便做些讨好邵以南的事,例如偷递茶点,例如此时加一条锦被。
钟离睿走到龙塌前,久久定睛看着邵以南,整个人似是被谁施了定身术。
初时想来仍是恼火……那夜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了自己的心思,得到的回答是一场恶斗。他处处手下留情,邵以南却是恨不得要把他弄死才安心。这也就罢了,习武之人,谁会在意那些皮肉之苦,让他恼的是第二日。他苦闷多时,邵以南却是一夜之间就能决定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