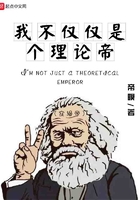宗望道:“你差不多得了,她是自己要走又不是被人杀了,天长日久,你慢慢找她就是了,到时要杀要剐,她能怎的?”
宗弼哭道:“她变心了,她不喜欢我了……”
宗辅道:“要说她姐俩也真有意思,当妹妹的放着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的少年不要,非要嫁老姐夫,当姐姐的跟你睡也睡了爱了爱了,还要满世界乱跑——这都是日子太顺了要找刺激吗?”
宗弼不听则已,听了哭的更甚。
宗望笑道:“我看你还是别劝了——宗弼,你先说说给宗隽喝的那杯血是怎么回事,说完再哭吧,宗隽都快疼死了。”
宗弼便把误打误撞喝了两杯仙茶的事说了,道:“你看,我早上割血时留的伤口已经完全好了,连疤都没留。”
宗望道:“宗隽伤的那么重,你给他喝的够不够?”
宗弼道:“再给他割点也没什么,不过都过去一天了,还能有效吗?”
宗望道:“无论如何,你再割点给他吧?”
宗弼应了,拿刀割了两杯,一杯给宗隽,一杯给孙和尚。
宗望看孙和尚喝了,见他伤口并没有马上愈合,只是精神立时好了些,忙教宗隽也喝了一杯。
宗隽脸上生了好些新肉出来,红的十分吓人,再喝一杯血,亦觉精神好些,慢慢吃了些粥,迷糊睡了。
次日清晨,宗望来探宗隽,见他肤色已如常人,正拿面镜子细看。
宗望大喜,笑道:“宗隽,你全好了!”
宗隽笑望哥哥一眼,明眸善睐,俊美非常。
宗望摸摸他头,笑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倒似比宗弼还俊些,以后也不用再怕见人了。”
此时宋使前来,宗望便领着诸弟与宋使见面。
宗辅等人见宗隽面目如常,尽皆喜悦,连宗弼也不哭了,庆幸多年恩怨终于了结。
可他转念想到萨萨逃走,又觉难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
宇文虚中见金人欢喜,忙将财物并美女献上,并称李纲已被撤职。
宗望心情大好,笑道:“劫营的事,反正他们都被杀了,就算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皇帝,让他将各地勤王部队撤走,待我们安全撤到黄河以北,拿下三镇,就把人质放回。”
宇文虚中大喜过望,叩首拜谢。
宗弼道:“你们亲王当中,最丑最笨的是哪个?”
宇文虚中不解,宗望、宗辅都忍不住笑,道:“现在这个亲王不听话,你们换个笨些乖些的来。”
宗弼道:“换个最丑的!”
宇文虚中不解,道:“能否让在下与康王一见?”
宗望不许。
不久,钦宗果教各地部队撤离汴梁,又严令不许追击。
李纲、种师道等人几番请求追击金军,终因钦宗惶恐惧怕精神崩溃不得成行。
宗望既得大量财宝并割让三镇诏书,待徽宗五子肃王赵枢置换康王赵构后,便敛军北撤,安然到达黄河以北。
宗弼见军中无事,执意返回汴梁找萨萨。
宗望遣人将割让三镇诏书交给宗翰,不料张孝纯、王禀拒绝奉诏,坚守孤城。
宗翰大怒,发誓破城,下令西路军继续围城。宗望亦因不得三镇不肯释放赵枢和张邦昌。可怜肃王赵枢至死,再也没有踏上宋土。
彀英无聊的脑袋上长草,缠他老子几天,也往汴梁来。
玉儿临时起意逃跑,不曾带许多财物,只好将随身的配饰玉器卖了,先替岳飞治伤。她官居五品尚服,颇有些值钱物什,倒得了不少钱。
岳飞歉声道:“我不曾帮上你,倒要你几番相救。”
玉儿道:“我不通事务,倒是跟你在一起,才觉得安心——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岳飞道:“我伤不妨事,等过个两三天,你用这些钱,在汴梁城郊找个谋生的去处,一来不必见到旧识,二来生活也方便些。”
玉儿道:“可是我什么都不会。”
岳飞道:“那你在宫中主要做什么呢?”
玉儿道:“最开始主管官家配饰宝器、字画印玺,后来总管宫中服舆仪仗。我年纪轻,许多事情做的不好,只是因为与他有婚约,所以官居五品。”
岳飞道:“不妨,你既有本钱,许多事情并不需要亲力亲为——你跟他,成婚了吗?”
玉儿点头,道:“虽未行典礼,但,已是人尽皆知了,可是,我实在不想一辈子被他软禁……现在跑出来,又不知该如何生活——我是不是特别蠢?”
岳飞道:“怎么会呢?你这么聪明,这些琐碎俗事,你很快就学会了。”
玉儿道:“岳大哥,那你有什么打算?”
岳飞叹一口气,道:“一月前他领兵攻下我家所在的汤阴,后来金军围攻汴梁,我自知力薄,仍然来了,待安顿好你,我就回家照顾我浑家。”她就快生了,我务要尽早回去,不可心生杂念。
玉儿道:“岳大哥拳拳报国之心,实在令人佩服……此次金军南下,因果复杂,希望他们撤军之后,不复再来。”
岳飞苦笑道:“若真以黄河为界,连我也成了金人。”
休养2~3天,岳飞领玉儿在城郊寻摸安身之处,不想在一处磨坊前见到一个男人打他老婆。
那男子身量不高,貌不惊人,打起女人来却颇有气势,仿佛是纵横疆场的大将,只听他骂道:“不识抬举的婊子,给你吃给你喝,还有什么不足,倒来忤逆老子!”
那妇人心灰意冷,只是垂头哭泣。
岳飞心下不忍,止他道:“这位大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般打她?”
那男子道:“我自打她,关你什么事!”
说着一脚踹在那妇人心口,道:“你给我滚回去!”
那妇人痛哭伏于地,默然不应。
那男子表情狰狞,又是一脚踹去,道:“你找死是吧!”
岳飞大怒,一脚踹翻那男子,道:“你这厮太不要脸,怎可倚强凌弱欺负一个妇道人家,况她还是你浑家!”
那男子瞪眼道:“我打我婆娘,关你鸟事!”
玉儿将那妇人扶起,怒道:“什么欺软怕硬的恶狗,打死他!”
岳飞吃了一惊,转头看那妇人,觉她眼中似有不忍,上前揪着那男子道:“我本欲打你,念你浑家忧心——你倒说说,她究竟做错什么,竟这般打她?”
那男子道:“我要她切二斤羊肉,谁知她买了二斤猪肉,油腻腻的,谁要吃它!”
岳飞怒道:“就为这你竟打她?她是你奴隶吗?就算她是,你这主人禽兽不如!”
那男子惧怕岳飞,不敢吭声。
玉儿将那妇人扶到里屋,握着她手道:“这位姐姐,他经常打你吗?”
那妇人泣不成声,缓缓点头。
玉儿大怒,道:“刚才真该痛打他一顿!”
那妇人眼露不忍,道:“他终是我相公。”
玉儿道:“相公怎么了?相公就能欺负你?便是奴仆……”我虽是个女奴,宗干和宗弼却待我很好,从来不曾欺负我。若不是他们,不知我的日子该是怎样的光景。
这样想着,倒有些同情那妇人,道:“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那妇人道:“我娘家姓李,我自小在这染坊长大,后来我爹因为赌钱把染坊卖了,买主就是他。我初见他时,他,他对我父女大献殷勤,说他只是帮我和我爹守住家产,又讨好我那鬼迷心窍的爹,求他将我嫁给他……后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境败落,为了买我家的染坊,特意编了一个小两口投亲的故事去诓他那远房表姐,我不过是他故事里的浑家。”
李氏擦擦眼泪,继续道:“再后来,他又拉着我去他那远房表姐跟前献好,说我俩都姓李,正可做好姐妹,他远房表姐虽是京师第一名妓,于小家户生活却像个小妮子似的好奇羡慕的很,竟然特意花钱为我们置了一处小宅,之后,又因欢喜他表演的夫妻情深和殷勤周到,屡次给他财物……”
李娃冷笑道:“可实际上,他根本不懂漂染,也从来不做家务,里里外外大小事务都是我父女辛苦张罗,只是财权在他手上,我爹死的时候,他明明有钱……却不肯请医生,我眼看着我爹,一点点病死了,一点点病死了,一点点病死了我却没有办法……”
玉儿替李娃擦眼泪,心痛道:“这太坏了,你怎么不想想别的办法?”
李娃哭道:“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想什么办法,我跑到妓院去求他表姐,她表姐心善,倒真给了我些钱……都被他抢走藏起来了……后来,他打我就越来越没顾忌了,从每月一次,到每月2次,到3天一次,到高兴了就打,不高兴也打,有理由也打,没理由也打……他口口声声说他给我吃给我穿,可这染坊的生意是我爹留下的,其他的钱是他表姐给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凭什么这样?凭什么啊?”
玉儿不知说什么好,伸手把她搂进怀里,抱着她头安慰,道:“可能恰恰因为你们都对他太好了,他又知道你如今无依无靠,才这么无所顾忌。”
李娃道:“前些日子不太平,我们一直没法进城,进城以后发现,汴梁城倡优伶人的家都被抄了,又赶上汴梁城戒严,柴米皆贵,他表姐孤身在小宅里,担惊受怕,挨饿受冻,他居然,就逼他表姐离开了,说她勾引太上皇,是汴梁城的罪人……呵呵,呵呵呵,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从来也不知道,他居然是个爱国义士,大义灭亲,灭亲之后,还要问她表姐讨饭钱、房钱、工钱……我为什么嫁给这样一个人,为什么……”
玉儿道:“你嫁他本是上当受骗,又何必从一而终,今日岳大哥在此,你求他杀了那畜生,以后守着这染坊,或者雇帮工,或者觅良配,总好过终生受他欺侮。”
李娃心下犹疑,心中不忍,道:“兵荒马乱,我一个妇道人家,若没了男人,如何过活?况随意杀人,乃是死罪……只求他以后少打我些,也就是了。”
玉儿心道:原来岳大哥方才不打那禽兽,确是顾念她。她这么善良贤惠的妇人,竟是个糊涂人。
玉儿劝她一会儿,道:“那,李夫人后来去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