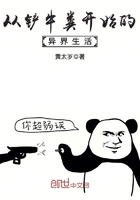微弱的气息拂过指尖,还活着。
只是看她这幅样子,怕也只是勉强吊着半条命。
利索地将她放到车上,长吉这才发现,她身上凉的吓人,脚上的布鞋也不知道怎么磨破了。脏兮兮地,连同衣摆的边上,都沾满了尘土。
半路上碰见巡防的武侯,这次没有陆仲安在,长吉解释了半天,最后靠着陆府的马车,才勉强通过。回到府里,已经是子时了。
云水居的灯光还在闪烁,里面的人却是睡下了。不敢惊扰陆仲安,长吉看了看脏兮兮的赵子遇,也不敢往里带。
屋里头的那个,是出了名的好洁净。白日里,但凡陆仲安不在府上,便会有一群婢妇家奴奔忙在云水居里,不间断的揩拭,直到地板锃亮,旮旯也都不染一丝纤尘,才算作罢。
上回赵子遇能在云水居过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换了衣服,而且事出有因。今日,看她这一身灰尘,长吉可不敢自作主张。
犹豫了一番,长吉悄悄叫了府里最老实的两个婢子出来。
“你们把她带进去,给她好生洗洗,换身衣服,再灌点药。”
“啊?”大莲和小莲见到赵子遇,惊讶的捂住嘴巴。
这……这不就是那天帮夫人去县狱的赵家娘子么。
长吉不明所以,还以为她们是被赵子遇的男性装扮吓到了,连忙压低声音说:“不用怕,这是个女子。不过,你们两个记好了,此事万万不可外传,三夫人也不准说。若是走漏一点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
大莲和小莲闻言,赶紧点点头。抱着赵子遇往府里进。
甩开长吉,二人商量了少顷,干脆直接把赵子遇带回了松香阁。
千秋看到两日未归的主子,吓了一跳,三个人顿时忙做一团。又是烧水,又是煎药,直待赵子遇在热水桶里睁开眼睛,几个人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姑娘可真是吓死婢子们了。”
千秋端着一碗汤药躬身走到她面前,杏眸里泪光涟涟。
热气氤氲,什么都看不真切。赵子遇抬手摸了摸额角,那里的血管似乎在跳动,连带着头疼地厉害,四肢也像灌了铅似的,麻木又沉重。
缓了好一会,千秋又唤了她几声,她才缓缓想起来,自己似乎被赶下了车,还在路中间站了很久很久,后来实在又累又困,好像就睡着了。
“别说婢子们了,若是夫人知晓,定也是要担忧得紧呢。”小莲哀婉地皱着柳叶眉,边说边小心翼翼地用水瓢往她身上淋水。
“没事的,我只是太困了。”赵子遇抬头笑了笑,接过千秋递过来的汤药,缓缓喝了下去。
千秋见她还笑得出来,不免嗔怪道:“是冷才会困的,姑娘方才险些冻坏了,若是一直睡下去,怕是人就没了,凶险的很。”
“是呀,眼下春末夏初,正是昼夜温寒料峭之时,可万不能大意了。”大莲也在一旁附和。
看到大莲,赵子遇想起什么,问道:“可是三夫人带我回来的?”
大莲迷惑地摇摇头:“是长吉。他还让婢子们不要告诉旁人呢。不过婢子们想了想,千秋是姑娘的人,怎么能算旁人呢,而且婢子们不知姑娘平日里吃什么补药,所以就自作主张把姑娘带来这儿了。”
“长吉……”赵子遇像是没反应过来似的,喃喃重复了一遍,念着念着,她伸手抓了一把头发,倏地从木桶里坐了起来。
“拿身衣服来。”
几人被她的脸色微微吓到,赶紧手忙脚乱地帮她穿衣。
赵子遇头疼地紧,猛然站起来更是不适,千秋在一旁扶着她,担心地问:“姑娘还要去哪里,夜已经这样深了,而且姑娘这身子,可如何是好啊。”
“哪里都行,不能在这里。”赵子遇敛下睫毛,看了一眼大莲:“我来松香阁的事……”
“婢子们晓得,一定不会乱说。夫人都告诫婢子们好多回了呢。”
接近四更,府里过道上点的灯都快熄灭了,赵子遇踮着脚,摇摇晃晃地回到云水居。
前厅的软榻上还放着她昨天盖过的锦衾,整整齐齐的叠放成一个被卷。赵子遇生怕惊到里屋的狗东西,只好轻手轻脚地爬上软榻。
拉过被子钻了进去,赵子遇发觉被子是暖的,还有沉水香的气味,侧身看了看,原来是边上搁了一个薰笼。
赵子遇往薰笼边挪了挪,抓住被子蒙着脑袋。被子里香香软软,她却有些心神不宁,陆仲安叫她滚的,她却又滚回来了,到底是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屈辱感。
本来还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明天怎么和那狗东西继续相处。可这一日奔波,冷热交替,着实把她折腾的够呛,一合眼便睡了过去。
第二日,赵子遇没有见到陆仲安。
她的身子终究是败下阵来,在过度劳累和受了风寒后,再次陷入昏沉,连带着起了温症。
见她昏睡了一上午迟迟不醒,长吉只好在软榻周围拉了纱帐,叫来府上的医女隔帘替她诊治。连灌了三大碗的汤药,又给她扎了针,才令她的病情勉强稳住。
傍晚的时候,陆仲安回府,赵子遇依旧未醒。
若无其事地扫了一眼帐子里的人,陆仲安问道:“医女看过了么?”
长吉躬身:“看过了,是染了温症,加上她自身的不足之症,才会昏睡。好在睡上一阵,或能减轻病症。只是以后都只能静养,不能劳碌惊惧,否则以她眼下这具身子,怕是难以撑过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