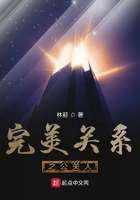颜文不再将头抵在窗上,而是用手指在窗上胡乱的描绘着。看着窗外变换的事物,颜文努力的从记忆中搜索着有关于他们的印记。他已经太久没有回到过家乡了。
赵瑞泽从后视镜注意到颜文的状态忍不住说道:“哥。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太久没有回来了。我都感觉自己不认识这里了。”颜文收敛神色回答道。
“是啊。现在这里真的变化太大了。以前哪有这么多高楼。你看看,这街上的人这么多。以前哪里有这样的景象。很多地方现在都认不出来是哪里了。”赵瑞泽说道。
颜文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随后剧烈的咳嗽了起来。等到不再咳嗽,又吸了一口。
赵瑞泽皱起眉头语气严肃的说道:“哥。你还是戒烟吧。你看看你都咳成这个样子了。”
颜文将吸了一半的烟按灭,又咳了一阵,然后回答道:“没事,没事。这不是老沈看不惯我抽烟嘛。提前过过瘾,免得到时候在他面前抽烟招他嫌。”
“你现在也就怕被沈哥哥嫌弃。就应该让他来看看你一天天怎么糟蹋自己身体的。我看到时候你还敢不敢了。”赵瑞泽说道。
“嘿。小兔崽子。胳膊肘往外拐。还沈哥哥。到底谁是你哥?造反呢你。”颜文轻拍了一个赵瑞泽。
赵瑞泽没回话,而是一个急转后将车停住。
颜文一个没注意被惯性带着磕了头。
“你搞什么?”颜文揉着磕在车窗上头。
赵瑞泽笑的一脸温和回答道:“哥。到沈哥哥家了。”
“你个死腹黑!臭小子。”颜文揉着脑袋骂骂咧咧的下了车。
沈诚已经在家里等候着他。
两个人上次见面仅仅时隔几个月,沈诚没想到颜文竟然虚弱了这么多。颜文才进门说话时沈诚就听到他的声音已经有些中气不足了。现在看到人站在面前,更让沈诚怀疑自己与他上次见面已经是几年前了。颜文身体的虚弱简直是写在了脸上!
“你怎么回事?前两天我听你打电话的时候的声音还挺好的。怎么现在听着这么虚弱?你是不是还没有戒烟?饭也没有好好吃。你弟弟一走你就懒得吃饭。你看看你虚弱成什么样子了。不是说都布置好了吗?你也就是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别老是虚耗精神了。”沈诚等颜文一坐下就连珠炮一样的问道。
颜文被问的一愣,而后笑着回答道:“没有了。赵瑞泽不在的时候安颜都会给我做饭的。我这段时间吃的比以前好多了。再说了我也没有劳心费神。这次把那个关键的人说服了就没我什么事了。剩下的时间我可以慢慢修养啊。你看看你,结了婚怎么和个居委会大妈一样似得。刚才我差点以为居委会过来查户口呢。”
“你以为我想啊。要不是你半死不活的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懒得问你那么多。”沈诚给颜文和赵瑞泽倒了一杯热水,“将就喝吧。我和瞿哲两个人都没有喝茶的习惯,家里也没有预备着茶叶。”
“说起来瞿哲哪里去了?”颜文问道。
“他同事和他调休了。今天他去上班了。”
“你这行啊。现在瞿哲工作,你躺在家里当大爷。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很嘛。”
“胡扯。你看看那阳台上的衣服谁洗的。家里的卫生谁打扫的。你那些破事谁给你跑的腿。我也就是现在不想去工作罢了。要不然凭着我的资历什么工作找不到啊。”沈诚又给颜文接了一杯水。
“那是。凭你的资历在咱们这个三线都算不上的城市什么工作找不到。不过你这贤良淑德,甘心当个家庭主妇。不对,不对。是家庭主夫。哈哈哈哈。”颜文放声大笑。
“笑吧。笑一笑,十年少。多笑笑对身体好。别老是一天到晚有什么都憋在心里。迟早憋死你自己。我还等着有生之年参加你婚礼呢。”沈诚说道。
“婚礼就算了。那不可能。都说了要单身一辈子的。当初说好咱们两个要是一直单身就买一间老年公寓做邻居。没想到你中途背叛组织。让我伟大的计划都破灭了。”
“我可没打算孤独终老。你说说你,安颜那么大的人都摆在眼前了,你还不把她拿下。”
“人家有老公,有孩子的。我拿下什么。”
“离了。孩子也上大学了。是时候有一个新开始了。”
“乘人之危啊这是。”
“趁虚而入最好拿下。”
“我这身体……”
“身体可以养好。真的,你努努力。我真的不希望你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弟弟早晚都要成家,总不能一辈子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安颜现在也是没个主心骨。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是最好的时机了。”沈诚说道。
颜文迟疑片刻,说道:“你现在说这些有没有用啊。这是两个人的事情。我总不能还和年轻时一厢情愿吧。安颜她愿不愿意呢?谁知道。”
“你呀。明明追求的是自由自在,偏偏又太在乎别人的感受。都这么多年了,安颜也不是当初那个不成熟的小女孩了。她知道谁是真正对她好的人。瞿哲上次见过她以后就说你们两个有可能。”
“别介。你们家瞿哲向来判断就不靠谱。当初在欧洲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判断,我们那一队人才被暴风雪困在山里半个月。好家伙,就因为他一句不可能下雪,我们差点就把饿死在山里。当初他还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你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呢。你看看,打脸啪啪啪。但凡他说什么有可能,那就绝对没可能。说什么不可能,那就绝对要成。”颜文说道。
“他还那么说过?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嘿。他可没这么和我说过。”
“诶呦。说错话了。你可别和瞿哲说是我说的啊。当初你们两个刚刚认识,他也是自己骗自己。没有其他意思。”颜文急忙解释道。
“看你那样。我知道他没有其他意思,我也没想怎么样。你看我和瞿哲一开始都觉得没可能。现在呢?还不是过的挺好的。你就努努力吧。争取把安颜拿下了。”沈诚笑着说道。
“嘿。怎么还绕回来了。还是别说我了。说说那位大人物吧。他现在还在岸上等着钓鱼吗?”颜文问道。
“是啊。现在他每天在湿地公园河边钓鱼。只是我和瞿哲前几次去和他接触,不能让他心动。到底还是钓的鱼小了。他还在等着。”
颜文食指中指交叠弹了一下水杯,杯中的水起了层层波纹。“那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是他是聪明的渔夫,还是愚蠢的鳟鱼吧。”
杯中的波纹早已消失不见。
鱼钩入水带起来微小的涟漪转瞬即逝。身旁的桶里只有几尾小鱼。龚予赐有些不耐烦的舒展了一下身体。这些天钓上来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实在是让人感觉没有意思。
这还真是百无聊赖。
“Doch endlich ward dem Diebe
Die Zeit zu lang. Er macht
Das Baechlein tueckisch truebe,
Und eh ich es gedacht,
So zuckte seine Rute,
Das Fischlein zappelt dran,
Und ich mit regem Blute
Sah die Betrog’ne an
但渔夫不愿久等
浪费时光。
立刻就把那河水弄浑
我还来不及想,
他就已提起钓竿,
把小鳟鱼钓到水面。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
看鳟鱼受欺骗。”
龚予赐身后传来了一阵歌声。
“狡猾的渔夫究竟有没有钓到他想要的鱼?”歌声过后有人说道。
“现在看来这鱼儿自己送上了门。”龚予赐起身看向那人说道。
“龚予赐先生。久仰大名。我是颜文。”颜文说道。
“我才应该说久仰大名。颜文先生。”
两个人礼貌的握了手。龚予赐从一旁的袋子中取出一个马扎放在自己马扎的旁边。
“颜先生,请。”龚予赐向马扎伸了伸手示意颜文坐下。
“多谢。”颜文伸手示意龚予赐回到座位。
“看来龚先生没有什么收获啊。”
“都是些小鱼小虾,没什么意思。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大鱼藏的越来越深了。”龚予赐抬了抬鱼竿说道。
“小鱼不知道这世界的危险,自然无知者无畏。大鱼见的多了,自然不会轻易上钩。再说小鱼虽小,倒也是一口肉。龚先生是看不上这小鱼肉吗?”
“吃惯了大鱼。这小鱼实在是没有食欲。”
“想要吃大鱼可要有耐心啊。”
“我已经很有耐心了。”
“还不够。”
“要什么?”
“诚意。”
“诚意?呵。现在是你们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付出什么诚意?颜先生开玩笑吧。”
“不。是你需要我们。”
“怎么说?”
“你一直在等我。”
“凭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够。”
“当然。我还有您太太的亲笔信。”颜文从衣兜里取出一封信,“相信这个的说服力应该很足。”
龚予赐笑了一下,脸上的表情舒缓了不少。他等待的东西终于到了。
龚予赐将信接了过来。他没有看,而是放到自己的衣兜里。
“她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与她接触的是另一个人。我现在的身体可受不了高原反应。”
“她在青藏高原?”
“是。在墨脱。老实说,如果不是她在去年到墨脱支教,我根本找不到她。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墨脱支教过。后来虽然离开了,但是墨脱支教的工作我也时常会参加。去年我弟弟转达了你让我找人的意思时,我正在审理参加墨脱支教的成员名单。她的名字赫然在列。还真是巧啊。”
“去年你就知道。现在才告诉我?”
“抱歉。为了让你一步一步上我们的贼船,我只能出此下策。”
“你觉得我已经上你们的贼船了?”
“你刚才把信收起来都没有看一下是真是假。这说明你对我有一些信任。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自作多情。”龚予赐起身走到一旁停着的车,从后备箱拿出来一个保温饭盒。
“我自己做的寿司。来一个?”
龚予赐把饭盒递给颜文。
颜文不客气的拿了一个,两三口吃完。
“不错啊。你这手艺蛮好的。我在欧洲认识的那个日本朋友都没有你做的好吃。”
“我太太教的。”龚予赐拿起一个,慢慢的吃了起来。
“说起来你和你太太什么情况啊。”
“你不知道?”
“我上哪知道去。当初告诉我消息的人只是告诉我要以你太太离开为筹码要挟你。其他的,他就不愿意多说了。我再去查这件事,也只是找到了一些细枝末节。”
“你弟弟来和我谈判的时候,可不像是信息不足的。”
“大多数都是我自己推断出来的。看起来判断的还算准确。”
“你都判断出来了。还用得着我说?”
“总归是不一样的。我就喜欢听那些不一样的故事。你愿意讲讲吗?”
“男人家怎么这么八卦?”
“不算八卦。这叫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趣味。”
“就一个不入流的小说家?算了吧。”
颜文从龚予赐的饭盒里又拿了一个寿司。
龚予赐沉默良久。他拇指支在太阳穴上,食指在眉心上方放着,中指摩挲着眉心。
“也好。这件事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和外人说过了。夫妻之间的心结,总归是当局者迷。也许你这个不入流的小说家可以给我点建议。”
颜文又拿了一个寿司。
龚予赐看了看手里空了的饭盒。
“我现在的成功离不开我父亲。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我是个标准的富家子弟。比起那些彬彬有礼、学识渊博的富家子弟,我多少都有点爱玩了。
倒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富二代的爱玩。就是不喜欢读书上学,经常跑到剧院听戏去。我这做派倒像是个满清的八旗子弟,整天提笼遛鸟。有时间就去听听戏,其他时候就猫在家里聊QQ。反正家业大,花的起。而且也不差我一个人继承这家业。我爸爸看我这样,也不强求我去读书上学。只要不落了歪道上,随着我折腾。
我就是那时候认识我太太的。她是京剧演员,梅派青衣。说起来也奇怪,明明听过那么多名家,可我偏偏就独喜欢她那出梅派的《红鬃烈马》。我听说你也是个戏迷,想来你也知道《红鬃烈马》全折要唱下来有多难。现在没几个人拿得起来。大多数都是先让不太出名的孩子唱前面的《别窑》,然后大角儿再唱后面的《武家坡》和《大登殿》。这也是为了捧那些不出名的新人。大多数买票的都是冲着角儿来的。我太太就是唱前面《别窑》的。可那些年她也一直是个不红不火,不尴不尬的位置。往往就是今天这出子戏完了,你就听,都是说那些角儿如何如何。就没几个人聊他的。说起来也奇怪,明明和她一起被捧的新人都火了,就她还是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
我就不服了。明明唱的那么好,凭什么不红啊。后来她一有演出我就一定去,去了就是第一排。该叫好的地方,嗓子喊劈了我也继续。东西也没少送,可就是没啥回音。我是无所谓,捧角儿嘛。那过去为了捧角一掷千金的有的是。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她就是我的角儿。
也就是那段时间我再网上认识了一个京剧演员。你笑什么?也是,你一听这个开始就应该猜到了吧。那个人就是我太太。可当时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只当可以从她嘴里套出一点后台的事。两个人在网上天南海北的胡聊,有时候她也会给我透露一点后台的事。
我还是经常去捧她的场。不过我也开始去酒吧,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有几个玩的不错的,也经常请他们一起去听戏。其中有一个家里是做玉石生意的。我和他聊的投机,两个人几号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我平时对朋友花钱一点也不手软。大家开心嘛。有谁找我借钱,我一定给。结果那年夏天,他找我借一笔钱。那笔钱实在太大了。我不是借不出,但是我也不能不疑心他要这笔钱干什么。我问他钱的用处,他就死活不说。我就越来越觉得他可疑了。他见我疑心,就不再提借钱的事情。反而告诉我他过几天就要离开北京,希望我可以今天晚上可以陪他出去喝喝酒,就当是践行了。
我看他面色不好,只以为他是遇到了什么难关。那么大一笔钱我是不能借给他。不过在接受范围之内借给他一笔钱我还是愿意的。晚上去喝酒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张卡给他。结果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抓住机会开口,他一直在劝我酒。我本来我就觉得白天可能冤枉他了,这时候他劝我酒我也不好拒绝。不知不觉就醉倒了。到我清醒起来以后,我才发现他把我绑架了!
他开车带着我一路南下到中泰边境。一路上他把我双手绑起来,身边两个大汉寸步不离。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我早就搬出来一个人住,而且时常不联系父母。朋友更是没有一个是经常联系的。我这次被绑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好在那天晚上出来除了要借给他的那张卡以外,我根本就没有多带钱。他急匆匆的带我南下,才发现我身上根本没钱。我问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才告诉我他们家去年破了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快点还清那些钱,他居然想要铤而走险去贩毒。但是又缺乏买毒品的资金。这时候他想到了我。
本来还是想借的。结果看我怀疑他,他居然下了狠心把我绑架了。结果现在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我看他越来越焦虑,我就越来越害怕。为了让人知道我被绑架了,我告诉他我可以在网上转账到银行卡,这样他就有钱去买毒品了。他自然是愿意的。我被他那两个手下带到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黑网吧办转账。他们两个不懂网上转账那一套,我就故意做的很复杂。他们两个等的不耐烦,就在我旁边的两台电脑上玩红色警戒,我趁他们不注意在QQ上给她发了消息。
钱到手以后,他还是不愿意放过我,非要带着我偷渡。到边境附近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跳了河。本来以为可以自己跑掉的,没想到跳下河以后才发现河水冰冷难耐,直接把腿都冻抽筋了。后来我直接在河里昏迷了。等我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了。
警察告诉我,我太太当时接到我的消息就报了警,还把第二天的演出推掉,亲自南下来找我。我跳河前半个小时警方就已经包围了我们待着的那个破楼。我太太冒着生命危险跟在警方身后。我昏迷在河里飘着,是我太太第一个发现并且毫不犹豫跳下去把我救上来的。
老天爷啊,那么冰凉的水啊!她把我救上来就让警察帮忙把我送到医院。而她一到医院就昏倒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些天来例假。可她还是毫不犹豫的跳下去救我。后果就是我这个本来该死的人生龙活虎的,她却一直高烧昏迷。那段时间我一直守在她身边,哪怕什么都帮不了她,哪怕她的病痛转移不到我身上。可是我就是坐在她身边,一整天都是一晃就过去了。人们都是心爱之人生病感觉度日如年,可我偏偏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就是在她的病床旁边,我想明白了我喜欢的角儿和我经常聊天的网友居然是一个人。
我就那么等着她醒来,一天又一天。她睁眼的那一刻,我抱住她哭的被单都湿了。我以前不信神也不信佛。那一块我真的感谢上天,我谢谢它,它没有让她离开我。两个人身体基本康复以后一起回了北京。她身体始终没有康复。医生说她寒气入体,以后妇科病少不了。而且她的嗓子也不能再唱戏。我几乎毁了她的全部!可她告诉我没关系,因为她觉得救了我比什么都重要。
那段时间我好几次搂着她哭的不能自已。男人有泪不轻弹。可我觉得在她面前我哭的心安理得。我带她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我要娶她当媳妇。我爸爸出乎意料的没同意。我还以为他是介意我太太以前是个唱戏的,没想到他却说如果要结婚我就必须到公司上班。我当时就差点哭出来了。爸爸为我们好,我怎么可能不明白。当场我就给爸爸妈妈磕了一个头。我告诉他们我的命是我媳妇捡回来的,我就是为了她我也要拼命工作,给她一个富足幸福的生活。
我确实做到了。这些年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她自从跳河救我以后,一到冬天脚就冰凉。我每次都会亲自打好热水给她洗脚,然后拿毯子把她的脚包起来放到我怀里暖着。她就安心的打理着家里的一切,从来都没有让我因为家里的琐事烦心过。
直到去年立秋的晚上,我正在给她洗完脚。她突然问我:‘这么长时间咱们两个都没有一个孩子。你后悔吗?’
‘想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后悔。只要你在我身边,有没有孩子都是无所谓的事。’
‘可是我后悔了。’
‘不……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身为你的妻子,却没有给你生下个一儿半女的。这是我的失职啊!以前我没有问你,是怕你对我失望。可是我不能骗自己一辈子。你是个正常男人,你怎么可能不希望有个孩子呢?都是因为我,你为了顾及我的感受才说不想要孩子。我已经自私的占有你的爱情、你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年了。可我怎么就没有想过你的感受呢?你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反驳过我。你该受了多少委屈啊?都是我的错,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现在我觉得咱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就当是我最后一次任性吧。好吗?来,我们睡吧。’
我太太就那样搂着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收拾东西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要去西藏支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可是够觉得没有必要。我对她的感情天地可鉴。她现在只是自己绕进了死胡同,出来散散心也好。可是她到了冬天居然连她自己的行踪和消息都不给我了。我心里着急,可偏偏身体不争气住了院。正好这个时候你找到了我。我也调查过你,知道每年内地教师到西藏支教的工作你都会参与审核。没办法,只好先让你代我去找找关于她支教的消息。”
龚予赐讲起和太太的故事兴致勃勃的,颜文在一旁边听边嚼着奥利奥。
龚予赐把最后一块奥利奥抢了过来吃掉。颜文见状拍了拍手上的残渣,将包装袋揣回衣兜。
秋高气爽,万里层云,河水泱泱。对岸的白杨微微晃动着,远处大桥上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颜文站起伸展了一下身体,说道:“说真的,我一开始还蛮确定你会帮我的。不过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就不敢肯定了。你们两个还真是典型的笨蛋夫妻啊。”
龚予赐闻言哈哈大笑,说道:“没错没错,就是笨蛋夫妻。你这个词我喜欢。”
“怎么样?要帮我吗?”
“帮。”
“这么爽快?为什么?”
“我不想让她对我失望。”
“有点意思。”颜文对龚予赐伸出手。
“不是吧?这么恶俗的桥段你也来?”
龚予赐伸出手,与颜文击了个掌。
颜文说服龚予赐后就没有停留,直接赶回省城。回到家后,颜文几天没有出现在咖啡店,而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
赵瑞泽实在看不下去,带着安颜把颜文从家里拽了出来,把颜文带回了咖啡店。
颜文一开始还是老大的不愿意,直到他被拖在安颜为他买的躺椅旁。一见躺椅,颜文二话没说就躺了上去。一边吩咐赵瑞泽下去给自己烧茶,一边让安颜打开手机给自己播放京剧。
安颜现在也乐的陪颜文待着,偶尔听到喜欢的京剧段落也要跟着唱上一段。两个人时常就在二楼坐上一白天。要不就是听听京剧评书;要不就是颜文看书,安颜在一旁玩手机;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用手机看电视剧。
安宁和程橙橙有时也会来待一会。颜文自然不让两个人闲着,每次安宁一来就让安宁为他读书,而程橙橙就去帮安颜打扫卫生。以至于安宁有时候感觉自己和程橙橙是为养老院服务的志愿者。
心情好的时候颜文总爱唱几句:“
天赐国号地做保,
在陈桥扶起龙一条。
昔日里打马过金桥,
偶遇先生八卦高。
算得孤王八字好,
后来一定坐九朝。
到如今果应前言兆,
你比那诸葛也不差分毫。
施罢一礼坐陈桥……”
安颜捂住耳朵,嫌弃的说道:“别唱了。最后一句都不在调上。”
“那我这嗓子也就是个自娱自乐了。你还指望多有水平呢。”颜文说道。
“诶,我说,你知道你适合什么派吗?”
“什么派?高派肯定不适合。麒派?”
安颜摇了摇头。
“马派?”
“不是。”
“杨派?”
安颜又摇了摇头。
“余派?”
“不是。”
“言派?”
安颜又摇了摇头。
“谭派?”
“不是。”
“唐派?”
“都不对。”
“嘿。我总不至于适合梅、尚、程、荀吧。”
“就你。你唱青衣花旦啊?还是算了吧。”
“那你倒是说我适合哪派啊。”
“你适合‘没准’派。”
安颜说完就笑的前仰后合。
颜文瞬间黑了脸。看着笑的前仰后合的安颜,问道:“你在笑什么?”
安颜憋笑回答:“我想起高兴的事情。”
“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可以唱青衣花旦,你那个老烟嗓连个老生你都唱不了。”
安颜笑的更开心了。
颜文瞬间黑了脸。
“你说的这个青衣花旦它好唱吗?”
“它不是好唱不好唱的问题。它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可以嘲笑你的话题。”
“今天晚上你洗锅。”
“玩不起。”
“就是玩不起了。”
颜文坦荡荡的承认。
安颜撅着嘴说道:“洗锅就洗锅。洗锅也是我比你唱得好。”
颜文失笑道:“怎么咱们两个和小孩子似得。”
安颜点了一下颜文的额头,说道:“你才是小孩子。你就是个长不大孩子。”
“好好好,我是孩子好吧。”
颜文无奈的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