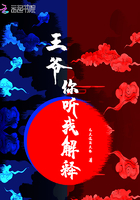云溪躺在软塌上,静静地凝着宁西洛半侧而来的眸。
自入了房后,一切皆为寂静,宁西洛褪去了一身的脏污,却没有触碰她一分,反而点了她的穴道,将她放在这里短暂的小憩。屋内密不透风,反而因为那些暖炉逐渐烘干了衣裳上的潮湿,只是那血还在,依旧醒目而刺眼。
此时,云溪对着萧院正混浊的眸,只是再度浅笑:“萧院正?”
萧院正晃过神来,立即从箱中拿出了物什,轻垫在云溪的手臂下,隔着一层锦帕为她号脉。
他是跪着号脉的,云溪微皱眉。
而一侧,宁西洛再度冷声:“有碍?”
萧院正连忙收回了手,立刻起身,他垂着眸轻声道:“这姑娘的脉象无碍,似是以前曾受过大大的小小的伤,所以身体还是有些虚的。”
说此话间,萧院正藏在衣下的手倒是有些轻晃,似是在怕。
烛火轻晃,映的那张俊美的容颜似冷似暖。
宁西洛只是轻瞥了萧院正,便道:“你在腹诽朕为何不让你去看那重伤之人?”
萧院正立刻跪下:“臣不敢。”
那凤眸之中带着浅淡的笑意,却令人胆寒:“带着你的东西随顾生言去那里,你只用告诉那受伤之人,你有办法让他不做内监便可,他会说出该说出的话。”
说这话之时,云溪心中一紧,已然看不透了宁西洛的心绪。
这木易逻即便是赴死,也不愿说出公主的下落,自然是严刑逼供也未尝可行。而如今,宁西洛如此之话,倒是让她抿了眉,甚是不解。
萧院正来此处,并不见得是为她号脉,而是非来不可。
因为,他寻到了审问流烟于何处的办法了吗?
萧院正虽然不解,却依旧俯首而礼,随即便小声出了门,一直到大门紧闭,那凤眸才以柔和之色凝视着云溪。
身上的被褥被他掀开,他修长的手轻触云溪腰间的带子:“天亮便启程。”
云溪一动不动,眸色凝望着他的手,隐晦道:“不做内监,倒是真的有办法救他?萧院正的医术,倒是如此高明了?”
宁西洛的手顿了一瞬,已然将她那浸染血水的外衫褪去。
宁西洛将她横抱而起,走向那浴桶之前,却停驻了身,凤眸萦绕着云溪的面具,唇角微扬,眸内的闪烁早已阴晴不定。
“他只是吓昏了过去,朕何曾刺中过要害?”他道。
一句疑问,云溪便彻底明了。
即便用了那融虫蛊又如何,人的性子终究是不会变了,宁西洛利用了木易逻胆怯的缺点,便抓住了他的命脉。木易逻或许不怕死,但是终究逃脱不了男人最怕的东西……
云溪被宁西洛轻轻放于那浴桶之中,里衣与那温热的水相融于瞬间,淡淡的血渍于水中晕染而开,而身前之人的神情却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叩叩——
有人敲了门,又进了门,那浴桶之前的薄纱遮挡了顾生言疾步而来的模样,却未遮挡桌上被刚刚放置的熏香之味。
顾生言垂身而退,将门关闭。
那熏香之味腾然而起,浅浅淡淡,是那熟悉的味道——狐幽香。
身上的穴道被他加重了力度,隔着那层面具,宁西洛却依旧凝视着她的眸。此时,云溪站于浴桶之内,只是任凭他看着。
“皇上乏了,便可招人去侍寝,莫要忘了与云溪的约定。”心中的惧怕越来越浓,云溪拼命地冲击着那穴道,内力微震,那面具险些掉落下来,却被他再度扣紧。
那狐幽香的味道越来越浓厚,而宁西洛的手已然落在她肩膀之上。
凤眸微微眯着,他想解开云溪的里衣之时,却停住了手,一句淡语:“若你一直带着这面具,朕倒是不知,你与溪儿究竟有何不同。”
云溪突然愣住了心神。
终究,宁西洛想让她带着面具,终究是因这层原因吗?他依旧是他,可她却早已不是画溪了。那缥缈尘世,早已不需要画溪的存在了。
云溪轻声道:“是皇上杀了画溪将军的,又何必念念不忘?如今,对一个替代品如此而语,到底是心底的愧疚罢了。”
清眸冷对凤眸。
那张俊美至极的容颜未曾恼怒,却将云溪按在了浴桶之中,任凭烟雾缭绕,任凭屋内的闷热越来越大,他都不再移开那眸。
只是很久后,云溪听到了宁西洛一句浅薄之语:“朕说过,不后悔杀她,却从未说过是朕愿意去杀她的。”
浴桶之中的水逐渐变的冰冷。
而云溪却始终不明这句话中的意思,只是缄默而凝望,等待着那狐幽香散尽,等待着他不再沉浸于梦中。
自画蓝凤进宫之后,便有了狐幽香,而宁西洛却一直用的隐秘。张良曾说过,宁西洛夜夜伴随狐幽香入梦,即便画蓝凤在身侧陪着,这狐幽香或许也缺失不可。
这一夜发生很多事,却又似乎过了很久。
宁西洛将她从浴桶中抱起,放于那床上,逐而轻轻擦拭着云溪身上的水渍,每一处动作都温和至极。他没有逾越与多余的动作,反而将云溪的衣服换掉,又重新为她穿上了干净的衣物。
笨拙而温柔。
想必,宁西洛的心神早已被这狐幽香乱了,而她却能保持着清醒。
如此的宁西洛,她见过。不是现在,也无非画蓝凤进宫那些时日,而是她进宫之后的两年,她见过宁西洛所有的温柔,皆对准了她。可,这些又能怎样?待时机成熟,她一定会杀了宁西洛,即便不舍,即便她还爱……
猛然,云溪的心一抽痛。
此时此刻,她看着宁西洛,看着那浅薄散开的狐幽香,却听到那悠扬而起的唇线。
他道:“溪儿,我好想你……”
无非“朕”,而是“我”,就如同那年,他对她所说的“回家”一般。
云溪的身子被宁西洛抱紧入了怀中,而他口中却念着画溪的名字。此时,宁西洛的每一处温柔或许都处于过去之中。
她不明,也不懂。
若真的爱,却为何要做那种事情,或许兵权当真如此重要?就像画蓝凤所说的那般?即便是如何的理由,爱散了,便再也无法回去了,不是吗?
“即便性子相同,带上了这面具,混乱了视觉,云溪也终究不是画溪将军。皇上也终究爱的不是云溪,而是过去的愧疚。”
云溪苦笑间,穴道猛然被她冲开……
宁西洛松开了她,看着云溪一掌对准了窗户,窗布被掌风撕裂,风夹杂着雪花揉进了这屋,席卷了所有的狐幽香之味。
她冰冷着容颜,将那面具缓缓拿下,惨白的容颜对准了宁西洛:“皇上只需要知道,过去的一切皆为过去,即便画溪将军醒来,也定然不会原谅皇上对画府所做之事。无论缘由,皆不会!即便皇上以狐幽香当做深情,也不过是虚妄。”
当那凤眸凝视着云溪的脸时,那抹温柔逐渐被冰冷替代。
宁西洛站于那昏黄的烛光中,眸色如深渊般悠远,他怒道:“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