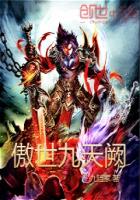附中每年春季举办运动会,秋季则是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定于九月下旬举办,初、高中部同时进行。
鲁宁宁是初二一班的副班长,因班长终日沉迷学习不能自拔,李实秦便把组织报名的工作强加给了鲁宁宁。
附中每年级一班都是实验班,实验班的学生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只会啃书本,一个个的也身负才艺,但因十月份全国大赛较多,他们班几乎每个人都有参赛,因而大多数对艺术节不感兴趣。
鲁宁宁也是如此,她也不想接手,但李实秦显然比她赖皮,同仇敌忾地一通抱怨后,告诉她“重在参与”,出个节目就行,千万别花太多心思去夺取胜利的果实,要给普通班的学生发光发热的机会。“不然风采都让咱们夺得了,他们会对人生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学也不行玩也不行,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就是这么残酷。”李实秦右臂撑在讲台,踮着左脚有节奏地晃动着,一想到三班陆老师吃瘪的模样,他自己先乐了起来,唾沫星子刮下了镶嵌牙齿上的韭菜,落到唇边。
鲁宁宁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伸手在面前扇扇,“老李,你也注意下个人卫生吧,别人家姑娘又把你甩了。”鲁宁宁反抗无效,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李实秦伸手摸脸,拿下唇边的韭菜叶,拔高喉咙,“宁宁,就一个节目就行,不用太多哈,马上要英语竞赛了,你得把精力放竞赛上。”
鲁宁宁撇撇嘴,心说我就是想放精力在这上面也得有人配合我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听过吗?鲁宁宁扫了眼纷纷逃散的同学,对着正收拾东西的许朱林哀叹:“本是同林鸟,大难各自飞。可怜深闺女,难为无米炊。”
“色鬼!”许朱林把书包往身后一甩,并脚提臀拔身绷直,双手捂着前胸,“休想在奴家身上打主意!奴家生是罗公子的生人,死是罗公子的死鬼!”
“什么玩意儿啊。”鲁宁宁脸上一个大写的“烦”字,拨楞开许朱林,拉开椅子坐下,想了想琢磨过味儿来,“我感叹你们薄情寡义,又不是强调‘夫妻’两个字。再说,”鲁宁宁挑着薄薄的眼皮上下打量着许朱林,“罗熠的人怎么也轮不上你啊。”
许朱林扭着小碎步蹭到鲁宁宁身边,亲热得和一只大哈巴狗一样,“哎,宁宁,你真喜欢罗熠啊?咱俩关系这么好,告诉我呗。”
“滚犊子!”鲁宁宁盯着嬉皮笑脸的许朱林,没半点儿好脸色。
许朱林毫不在意鲁宁宁的横眉冷对,挤下大半张椅子后,悄咪咪地道:“宁宁,你这里,”许朱林指着鲁宁宁额头,见鲁宁宁看过来,才说,“额头对应心脏,心经有热,热随血脉上行,就会形成痘痘,附加表征是脾气差,常生气。”
鲁宁宁拿起一本书“啪啪”地把书桌拍得震天响,“马上要竞赛,还有期中考,又要准备艺术节,我就是蜈蚣有上万条爪儿,也架不住就一个脑袋啊。”她颓丧地趴在桌子上,懊燥地踢了下前桌的椅子。
“老李不是说了吗?以竞赛为主,艺术节的事儿不用太上心。”许朱林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他常为朋友“两勒插刀”,“宁宁,是不是出一个节目就行了,我告诉你,你报罗熠。”
“罗熠?!”鲁宁宁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想让自己血脉畅通,以防再长一颗痘痘,“你是让他表演胸口碎大石吗?”她虽觉得罗熠很可爱,但还没有到盲目的地步,罗熠那么胖,能有什么才艺。
“独唱啊,不,边弹边唱,钢琴,也可以大提琴,大提琴还是小提琴?我也忘了,反正他会好几种乐器的。”许朱林瞧着鲁宁宁震惊的样子,有些不可思议,“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当然不知道啊,罗熠还会这些?你不会是骗我的吧?”鲁宁宁把校服袖子撸到胳膊肘,紧握拳头着拳头在许朱林面前比划。
许朱林瞧着鲁宁宁炸毛小猫一样,明明就是一个傻白甜的软妹子,可还要强撑,特别想笑,但本着同学应该互相互助的精神,他不打算拆穿鲁宁宁。“真的,他小学时和学校合唱队的领唱,哦,忘了,你不是附小的。”
鲁宁宁收回拳头,对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些不自在,声音都弱了,“那我问问他。”
“直接报上,你问他他肯定不同意。”许朱林道,“哎,你这样看我干吗,我又不是要害他,是他真的唱得非常不错。”
鲁宁宁还是犹豫,她怕罗熠生气,虽然他一直都挺好脾气的,但是没有征求过对方意见就赶鸭子上架,终究是底气不足。但是······鲁宁宁绞着手指,最后心一横,把罗熠的名字报了上去。
第二天午饭,罗熠照旧和许朱林一起,鲁宁宁在第二节下课时就告诉罗熠要和他们一起吃,两人在楼道里等去洗手间的鲁宁宁,看队伍都排到楼道里了,罗熠心里着急,他担心碰不上闻莺。
过了五六分钟,鲁宁宁甩着手上的水珠子跑过来,“你们吃什么?兰州拉面?”
“行啊。”许朱林说,“罗熠,你吃吧?”
罗熠满心思都沉浸在与闻莺的偶遇当中,根本没注意许朱林说什么,他想要是碰到闻莺,就问问她,她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可一路上,连闻莺的影子都没看到。罗熠有些闷闷不乐,怪鲁宁宁懒驴上磨屎尿多,也怪许朱林非要答应鲁宁宁一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