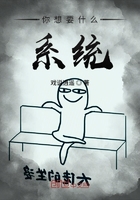孤秉拙书无量苦,赴死埋骨金台前。
缘由凡人当世,人曰此世为凡世,亦为凡人之世界。所言至此,后来人不禁奇怪这遍地凡人的世界,怎得人心却是不甘顺承这等平凡?只因久前,这世间竟迎来了两种非同凡人的存在:一为神,一为魔,而当两者出世之际,由此,凡世大变!
神、魔分别权衡着两种不同力量的极致,而当有极致的顶峰力量,自然便有了各自势力的崛起,这两属势力随之赴起构兵,只水火不容,再因二者皆欲一统天下,以是,那早前预谋已久的交兵,乃说是灭世大战便由此爆发。
一时间,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冻死骨胄甲尸四处可见,可谓是生不如死,死不如不生,凡世百姓屈辱地苟活于世,可就当人们根本不欲挣扎不欲反抗之际,又一个凌驾所有的超凡存在横空出世——
他只手大败神魔的原本无敌的力量,回笼舐血生灵之刀戟冷兵,平息在在戕害之硝烟暴乱,以是挽救了世间万万苍生。而后人们拜之为王,又称始王,值此情势下,神魔于王称臣,凡人亦甘愿接受始王统治,更甘愿接受其庇护,就此,旧凡世湮坠,而新凡世附生。
自始王治世以来,凡世去旧从新,其间始王开创凡人俗物修炼之说,其以自身本源之气作引,继而结合阴阳五行,将麾下神魔之力融尽并炼为一体,终极将之均分于人,往后继承此等新生之气力之人便有了修炼根本,由此,世间为尊崇王之仁德,将此传承之气称为拜祭王者所得之气力,素称祭气。
至此,继承祭气之人肉身资质皆会开始显现变异,或筋骨增韧,或经脉大开,而为教人们更好地支配这股力量,王又将毕生奇诀收录于《五行书》当中,如若继承祭气之人经由后天对《五行书》的参悟及修炼,届时破空而行、排山倒海亦不在话下,如若当真有勇夫经艰辛困乏之苦修以晋升至书中最高境界,终得脱离轮回桎梏,悟彻天道,蜕其凡胎,得以永生。
而后随着血脉相传,祭气便一直活跃在凡世间,生生不息,渐渐的,凡世物阜民熙。
*
自始王羽化起,凡世世代变更,权位流转,直有李姓崛起,其间李焉李赞父子豪取龙座,取“天”为国号,定都长安,再置东都洛阳,遂建得天朝,一统神州,今值九任皇帝李鹔在位,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更是开创李天盛世。
是夜,此时京畿长安却尽显繁华,且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千灯万火映照得城内环河金光闪闪,城里绒絮如烟,桥梁彩绘,风帘翠幕,暮焰荧荧;其间高低错落的人家,寻欢作乐的人客,大街小巷,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好是热闹,满城亮彻繁荣之象,是极金迷纸醉骄奢淫逸的寻乐瑶池,却亦是极万万修士飞黄腾达的圆志高殿,以是置身其中,便是置身人间绝顶。
易辰走在城中心的街头,目光游离之际不忘一上一下地把玩着手中的玉佩,眉头紧锁,双耳赤红,很明显,其心里当下正是热血沸腾久不能停息的,至于四处乱瞅的眼神,纯粹是为躲闪不远处高楼上,一附于窗前看似浓妆艳抹的女子的注意,但很遗憾,后者仿佛已经注视到了他拙劣的掩饰,更是可能揣测到了他的来意,旋即女子嘴角轻扬,眼波流转着无限韵味,未几向他妩媚地招了招手,好似套笼了又一个有趣的猎物。
银铛楼,男人之家,长安城最受欢迎的青楼之一,而眼下,易辰正站在其大门对街,方躲过楼上妩媚女子的视线,以是当下害臊地面红耳赤,淌着冷汗愣着神,真就是这咫尺距离却亦叫他难迈半步,心里亦是又惊又惶,甚是踌躇。
“未满弱冠男子严禁入内!”
映入眼帘的是大门旁的一块题了告示的竖匾,这让只有束发之年的门对面站着的当事人好生尴尬,那么抉择时候到了,进,还是不进?
进了,这事若是走漏了风声怕是要丢死个人,不仅如此,大众更会以为易家年轻一代也不过是所谓花花之辈,家族颜面更是无地自处,但是不进吧,这已经承诺给他人的事就怕得黄了,信誉更会一落千丈,况且那人于自己心中地位至高,怎得都不想就此罢手了去,唉……
原来这便是所谓的进退两难啊,进则丢了颜面,不进又失了人品……
“算了算了,一颗破石头而已,届时大不了换个别的送给她……”思前想后,当事人终于决定要脸不要德行了,可这么决定下来心里又莫明地多些落差,“但那款绝版品种现在怕是有价也无市啊!这可如何是好……”
“哼!这几年碎骨断筋的修炼我无一不挺了过来,区区一个青楼就要逼我退去?笑话!”甩了甩袖口,易辰一副看破世俗的势态,不屑道,“管他成年不成年!不管了进去了!”
“咳咳,我进这种颜色之地绝非是抱着无耻下流的念头而来的,”易辰双手攒紧,头默默低下,眼神不自觉只看向前方低处,加速迈步向前,像是做贼怕人认出来一样,其间自己安慰着自己道,“我是来办正事的!真的是在办正事!正事要紧,正事要紧……”
此时街道上还且不算拥挤,来来往往的行人商贩个个形如自然,只是从一旁望去,一个双手插兜低着头板着脸的严肃少年正飞速移身至银铛楼大门去,这逛青楼就逛青楼吧,怎么给人的感觉像是上次来结的账价钱算多了,亏了,这次来把多余的再逛回来你不给我逛我就砍人的架势一样,其实这也倒是个不错的安慰自己快活的理由,一旁推着贩车叫卖的老汉皆是看在眼中,旋即一副罢了罢了我懂我不言的样子猥琐了一笑。
“哎呦!”
一声痛叫响起,原来易辰在加速闯进大门时,不巧撞到了一刚从楼里迎面而来的黑袍男子,看其面相是有不惑之年,模样算是英俊,只是目光碎散,脸颊醉醺,呼吸里还掺着一股浓厚的酒味儿,行走间姿势就像骑着猪一样摇摇晃晃,身后有一位年轻随从跟着,但后者貌似也没有要去扶这个喝高了的主子的意思。
就在方才,古恪终于被侍卫楚琛哄下酒桌,只是这厮一路上仍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这都快出大门了还不忘发着酒疯,还不忘要与美人儿再满上一壶,真让得后者不能多说他又拿他没辙,只得紧紧跟随,任他疯癫,甚觉丢人至极。
楚琛看着眼前仿佛肢体关节坏死而不能正常行走的主子,强撑的笑脸好像再表达“哎对!古叔您就要这样弄,您这骑猪的水平当真是越来越高了,放眼天朝九州有哪个骑猪能骑过您的人,对就是这样,快骑快骑,骑到门口我就扶您上车!”
只是话说再回来,其同时坚定的眼神里又好像不忘告诉旁人说“大家听我说嗷,我呢是不认识这个寡痞①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一起的嗷!我堂堂天策府典签怎么可能会服侍这种寡痞!”
“喂!寡痞!不对叫错了——古叔!我们快到门口了,要不您到那儿等会儿,待我去驾车完了再过来接您!”
说罢,楚琛便想着冲出大门取车,然后完了想赶紧把这厮拎走,只是还不待他动身,这时前面的醉汉却是一屁股坐倒在地,眼下好似受了冲突一般,而这一出便是惊住了楚琛,毕竟眼下青楼一行虽说弄得自己上了头,但纵使这厮喝得再烂摊,再一副烂泥样儿,自己终究是奉旨行事,更何况谈公不谈私,人也是咱叔呀,以是这怎能让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中伤!是也不是?
“古——”
“走路不长眼啊?没见前面有人啊?骑猪急着撞树啊?”
不待醉汉身后的随从发言,易辰赶紧先发质问,一串痛斥三言吼出,既掩饰了他当下强装沉稳心里实则乱套的伪饰,又成功转移了旁人对自己岁数的思疑,终极好以争取到混入青楼的绝佳时机。
“哼!行了算了!下次注意点!”
又不待醉汉反驳,易辰再是一串原谅三言强行终止话头,旋即侧身离开,只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
青楼宵夜之地像这种口角之争、小打小闹的场面频频发生,以是食客都见怪不怪了,而随着易辰的离开,旁人见没了戏看索性也都各自散了忙着快活去了。
“哼!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浪啊!区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不乖乖修练好以加官晋爵,竟是在这等年纪逛上男人之家了,呸!咦?人呢?”
还未及反应过来的坐在地上的古恪刚想着骂回去找台子下,不料人家先噘了自己就撒腿跑不见了,于是只得借着酒劲生着闷气道:“他娘的别让我再碰到这臭小子,不然定要令得他三拜九叩叫祖宗!”
一旁的楚琛汗颜,这堂堂无量宗宗主于长安城某知名青楼被一陌生少年予以侮辱,竟还是吃了个闷亏下不了台面,虽说身为其贴身侍卫,但是看着自己主子这般衰相心里却是莫名的舒爽,眼下心里好似还在为方才那个陌生少年暗声叫好!
看着坐在地上自言自语耍着酒疯的古恪,楚琛先是顿了顿,瞅了瞅四周,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然后眼神又回到古恪身上,深呼一口气,小声自言道:“古叔,多有得罪了……”
“咦,你这小子还回来做什么?慢着,休要乱来!”楚琛装作方才的陌生少年又回来找茬的架势,趁着坐在地上的古恪尚未酒醒,赶忙自导自演起一场好戏,“古叔小心,这厮竟是想动手伤你,快快护住脑袋!”
彼时,古恪坐在地上,借着酒劲还一直痛骂着方才那个挫了他气场的嚣张少年,可这时突然听见楚琛貌似很是紧迫的告戒声,缘由楚琛一直负责着自己的人身安全,其有应己必回,于是当下赶紧就地双手抱头缩成一团,以好保护自己又方便后者清敌。
这一晚,只见银铛楼大门口内,一正装男子对着蜷缩在地的猥琐醉汉施以拳脚、暴力凌虐,期间醉汉几度欲松手认清施暴者面目,不料后者无不看穿其意,几度快是得逞却又被怼了回去,而施暴者考虑到拳脚有限,或是难起致命效用,于是又抄起一旁宴上的镶钢铜椅,而后用劲挥向醉汉身上,几经挣扎,半个时辰后醉汉终于脱力,躺倒在地浑身抽搐,再一会儿又是口吐白沫直至七窍流血,最终休克……
“好了吗?”见古恪已是休克在地,保险起见,楚琛又往前者身上揣了几脚,见没反应,这才吐了口气,“终于安静了……”
说罢,楚琛扔掉了手中的钝器,从兜里掏出一张手巾擦了擦汗,放松之际,又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转身看向方才在一旁看戏的几个龟公,先问向最靠近的一个龟公甲,道:“你!就你!过来!”
龟公甲一听自己被抡椅狂魔叫上,暗暗叫苦,身后一群龟公乙丙丁赶忙松了一口气,龟公甲无奈地迎上前去,恭敬道:“公子您是在叫小的我?”
“不是叫你那我是在叫谁?”楚琛装作一副威严的样子,以自身强盛的气场压迫着这倒霉的下人不敢违抗,说道,“我且问你,方才打这地上的寡痞——不是,打这地上的醉汉的人,是不是我?”
龟公甲见楚琛指向地上已是休克的醉汉,且又是质问向自己,那不怒自威的样子叫人甚是害怕,眼下哪还敢扯谎说假,赶忙道:“当然是公子您打——”
“噗——”
只见龟公甲话未说完,便是吃了楚琛一记鞭腿,“嗖”的一声便飞出了门外,然后口吐白沫遂即休克在地,这时楚琛又转头看向剩下的龟公们,这不禁让这些人深深地打了个冷颤,甚是恐惧。
“你们!方才打这地上的醉汉的人,是不是我?”楚琛继续佯装威严,问道。
“啊!不是公子您,不是公子您!”听闻抡椅狂魔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人立马学了聪明,急得都跪着磕头道,“公子饶命!公子饶命啊!”
“哼!算你们实相!”说罢,楚琛抓起躺在地上的古恪的一边脚踝,继而事不关己地拽起他走出银铛楼大门,期间古恪脑袋卡在门槛上,前者只好使劲一拉,不料磕得古恪又是喷了一口老血,休克得更是安静了,临出门,楚琛不忘回首向方才那些龟公予以要挟,“都他娘的,嘴都管严实了!”
“公子放心,公子放心!”听闻抡椅狂魔又是一次明示着的暗示,剩下的龟公赶忙再磕头保证道,“小的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啊!”
闻言,楚琛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拖着古恪向马车那里走去。
注:
①寡痞:关中方言,傻子、蠢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