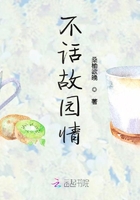想看看,确定他究竟是不是那个人。
她不可能再欺骗自己,在一阵对视后,失望的感觉也被对方看到了。
那为什么…站在眼前的,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人。
“让他们不要动我,保证我在船上的工作。”沈沭在他胸前小声道。
“你应该听说过我,我现在不一定不杀人,你的命在我手上,你为什么觉得我会保证你?”
他有些有趣得说道。
“因为…你想知道更多,而我可以现在就自杀。”
“你不会的。”他笑着,晃了晃肩膀转身。
“是误会。”他对一旁的经理说。
“啊…?”
他不想再重复,经理也马上反应过来。
“噢…好,好的!”
“她万一是?”尊骞不放心的问尊应。
“她不是,那边的人不会想开枪杀了我。”他慢慢走了出去。
几个人回头朝沈沭看了看,三三两两的紧跟着出去了。
“那家伙一定藏在船上,不止是监视这么简单,是想趁你不注意抢走那东西?”
“好好查查,但不用拦,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
尊应的声音消失在过道上。
…
这两个小时发生的一切像一场梦。
沈沭瘫坐在地上,她告诉自己要坚强。
她再次看见了那个人,她和他在一个邮轮上相处了那么多天,她终于…
但这次,再也不要陷入他的陷阱。
她必须隐藏好,想办法让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联系吴sir。
不出意料,沈沭带枪这件事众人皆知,她不能再继续服务人了,她甚至还被隔开监视着。
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她被盘问着来头。
一切显示她的身份是安全的。
今夜要提早返航,邮轮正常后加速了。
晚上她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手机也不能碰,直到证明她的身份是安全后。
一夜无眠的第二天,她被总务敲开了门,归还了手机。
“过来一下。”
她跟着走去,余光瞥见有人在角落抽着烟,很明显她也被他的人盯着。
“她们都作证,这把枪并不是从你这里出来的,是你间接放在了柜子里。”
“是的,她只是知道放在哪里,那一天都太忙了,我们忘记告诉总务。”林稚极力替她说话。
沈沭微笑着看向她。
“监控也确实拍到,虽然是在死角,但这枪确实是她的手出来的。”经理指了指旁边的女孩。
那个紧张的女服务生点点头。
“我很抱歉,确实不够理智的,在工作时由于误会想报私仇,我当时的情绪过于极端,给大家造成了恐慌。”沈沭冷静的自述。
“关于具体的,我们并不清楚,但连他们也提出是误会,那就只能这样算,可是,你的第一心并不是真正为了工作来邮轮的,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也无法让你继续留下。”经理对她说。
沈沭预料到了。
但她希望的就是如此,她必须先下船,才能联系到吴sir,想办法在靠岸前抓到那个人。
“经理,再给她一次机会吧,人伦常情我也能理解,如果换作是我刚好知道这件事,我也许会极端一些,刚好碰上在船上见到手枪,可是她工作态度一直很好,我都是看着的。”总务为她说话。
沈沭是有些动容的,就在她她刚想主动请辞时。
经理抬了抬手,“按理说是不能容你,可是那帮人真的难糊弄,身份也不一般,他们说要让你一定留下,我们也不敢不照做。”
沈沭抬头。
“你说什么?!”
一定是尊应的意思,他不会让她轻易离开的,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危险的存在,这次的行为她确实冲动了。
该死,沈沭啊沈沭你为什么总是不理智。
“但是你得跟她们分开来,下午可以继续照常工作,等这趟结束他们走了,我再决定你的去留。”
听这个意思,沈沭感到十分迷茫。
…
“你当时那是干什么呢!”林稚她们追着她问。
沈沭只好编造说什么自己是那个老人的义女,又是员工,在那艘船上的事故让她很痛心,于是误会了那个头目就是尊应,冲动得拿枪抵住他的脑袋。
总务出来后和她交谈了几个小时,对她说了一些注意的事情和话。
终于她又穿上黑色的工作服。
她被分配到上面去,不再做服务类的工作,也没有再看见那帮人。
一些女乘务看见她还是十分后怕,议论着。
她空下来给吴sir.打了个许多个电话,害怕被听到于是转成语音。
那些信息暂时没有收到回复。
晚餐后她在楼上整理柜台时,有人上来喊她。
“经理让你过去。”
沈沭下电梯,走到靠近大厅的地方,她望见中间的客人比那夜少了很多,待在房间里。
但依旧是热闹的很,许是那帮人快要提前下船了。
“这位是法国的乘客,你翻译一下他的意思。”
沈沭仅凭蹩脚的法语表达着他的问题,并且快速的解决着。
经理点点头,拍拍她的肩膀让她去忙。
转身便撞上一个胸堂。
“抱歉。”她下意识道。
“又是你啊?”对方的声音有些熟悉。
沈沭抬头,是那个胡子的男人。
沈沭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偶尔听见他们喊他骞二。
她看着对方摊开的外套里包扎的地方。
对于他,沈沭是抱歉的。
“对不起。”她弯腰。
尊骞摇摇头,“算了,你再深一点他可就不会放过你了,我是不对女人动手,否则也真是倒霉。”
相比那群人,他就像个绅士的老大哥。
“不过听说你撞上的人真不少啊。”
沈沭咬唇,“我想给你赔罪。”
“想赔罪来这边!”远处传来一声。
肖巴喊着她过去。
沈沭看到尊应坐在那里,一群人有说有笑,明晚他们要走了,似乎兴致不错。
她抬首走了过去。
沈沭扎了个高马尾,发型将她的五官显得更精致大方。
她好像没事人一样,她必须作出这样的表现,前天晚上拿着枪对着他们的女人现在也可以淡定得站在面前为他们服务。
似乎是被沈沭这样的气质意外得惊艳到了,一行人复杂的眼神里藏着一丝最开始对她的期待。
他们看了看尊应,他是唯一一个在沈沭走来时没有盯着她的。
就像无数次她为他服务过的一样,沈沭想到这里就意难平,对他更加厌恶,而尊应的心却生长着一丝优越。
克制的隐性优越和势在必得的沉着。
“忙归忙,我们可是不会放过你的。”肖巴笑着对她说。
沈沭微笑,“就像我多少次为各位弯腰倒酒一样,如果我在意被放过的话,早就在每天早上换房物时做手脚了。”
他们猛然一愣,没想到还有这茬。
这也侧面说明沈沭确实不是蓄谋的敌人。
“靠,她会不会偷了我枕头下的钱包。”
一个梳着中分的青年男人突然奇怪说道并被无语的打了一记。
“咳咳…”
台上的喇叭声突然刺耳。
麦克的声音震耳欲聋,经理拿着单子站上台。
瞬间注意力都朝台上看去,沈沭也就尴尬的站在那里。
她低下头,能感到某个人一直注视着她,炽热而令她不敢对视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
尊应是迷茫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拿这个女人怎么样,他并不在乎好像从来没把这个事放进考虑范围过。
他饮着一杯又一杯的烈酒也不见那如雕刻般的俊美面孔上有太多的起伏。
“真的不认识她?会不会是两年前…”肖巴凑近他的耳边。
一年多前的一个晚上,他莫名醒在了飞往南京的夜班机上,他毫无记忆,头痛欲裂。
碰上了一家赌场进去逛了一圈,给了一个家伙一点颜色,之后担心自己是被下了药,认为是黑鲸的人干的,随便拉着两个人去干了黑鲸在香港的货物藏匿点。
之后打算回洛马,却又没了记忆。
醒来后是在一条小船上。
…
“各位乘客,很高兴,到了明天我们部分乘客就要离开结束这趟短暂的海旅,而其他的乘客则是照常在次日从上海下船…”
“这次的一些不当也引起了诸多恐慌,我们昨晚的抽号就现在公布并赠送奖品。”
说是抽号,其实只在豪华场的人里反复。
“什么酒来着?”尊应旁边的人问。
“沙龙香槟。”尊骞眯了眯眼睛。
“什么水平?”
他举了几个手指头。
几个人点点头似乎觉着可以。
便起身欢呼起来,“动动动!给劳资动起来!”
“动!动!”
他们对着台上箱子里滚动的球号。
“29,27,30,这三桌一共九瓶加一个瑞士手表!”
“哇厚!”沈沭这边打起了响指。
中分青年催喊过来,肖巴也有点兴奋,忙重复今晚要打通宵。
“号拿去给大家看看意思意思。”经理走过来。
几人突然愣住。
一个问:“号呢?”
另一个:“不知道啊,我有一个29。”
一头云雾。
沈沭突然想起点什么…
“在我这…”她小声道。
注意力又转到她身上,那天还没发完呢。
“放上来!没想到仇也是你缘也是你,够巧的。”他们打趣着。
沈沭把27递给了肖巴,30则是…
她伸出手,对方并没有接。
道是旁边的人拿了过去,“今晚主你们三个!”
又欢呼了起来。
传说中死贵死贵的酒从大厅另一头送过来,不少人都朝这看。
“全开了,头六杯谁喝?”肖巴问。
有人响应,“当然是应二。”
沈沭微微抬眸,看着对方,他刚好对上。
她以为他们会叫他老大,以他为首是肯定的,肖巴可以确定是他们里的人,没想到一切都这么巧。
“恩!?”他们把酒杯伸过去。
尊应没有接过,倒是侧过问服务员那块表儿呢。
对方表示马上拿来。
“没想到你倒中意这玩意。”
服务生走了回来,端着一个精致的表盒,一看就价值不菲。
沈沭仔细敲了敲,里面表的镶嵌度和外观都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今晚的赠品和这些人几个晚上的开销,一船的收益比又算得上什么。
他踩掉了烟头,抬手让其靠近来。
那笔挺的白色西装袖子,分明的手掌,好像和表就是一对。
“过来。”他看向沈沭。
沈沭一愣,迟疑了几秒,慢慢走了过去。
她再一次离他十分得近。
尊应抽出那块表,拍在了沈沭的动脉上,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别这样。”她立马说道。
对方挑眉,两只手都抚上那表环,凉凉的感觉从手上传来。
轻轻一扣,色泽如银姬美女一样的钻表就戴在了她手上。
沈沭一脸看不透。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想。”他坐下。
她想起来申怀赎,当她问他为什么,从什么时候有想和她交往的想法时,他说,任何我想的时候。
也是这样,古怪的霸道里带着一种温柔,可惜那种温柔是假象。
她讨厌假象,所有不真实的东西。
“瞧瞧,这样还不够意思?”他的兄弟调侃道。
肖巴嘴角浅笑着不语,尊骞喝着酒似乎也明白了几分。
或许当许多次他不去看他,可他身边的却在打量沈沭时,一切就该明了。
轻易得不再追究一个举枪对着他们的女人的交换就是,这个女人对某个人的吸引力。
价值的等价交换,都明白了。
“他不追究你那天的行为,还送你表,美妞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
推了一杯酒过来,沈沭有些苦闷。
又不是她要的表,他这样算什么,看经理对着这场面的察言观色,也是给她日后添堵了。
“太多了。”沈沭当然知道他们在偷偷倒酒。
她只喝一杯。
转眼满当当的三杯都快洒出来了。
“你自己挑一杯。”
沈沭瞥着尊应,她看向离他最近的,拿了起来。
“嘿—”掌声重复上演。
她仰头几口吞咽下,看见坐着的人眼睛里闪着光彩。
她故意拿他喝过的那杯,他是想愉悦的话,足够愉悦了吧。
带着几丝挑逗,沈沭擦干嘴唇,她想告诉他,自己不是随便的女人。
和想象中不同,这酒味道到是带了几丝甘甜。
尊应盯着她饮完,唇上残留的金黄液体,喉结缓缓动着,当然也被沈沭看到了。
她在他们娱乐时悄无声息地走开。
“你说他什么时候看上的,不每回都一人孤溜溜坐在那喝酒嘛?”
…
沈沭漫无目的地穿梭在每个地方,心中满是如何如何找到尊应就是申怀赎,他是炸船主谋的证据。
…
时针慢慢走向凌晨一点半
沈沭打开窗户,夜景的船灯亮进来,她把电风扇关上,今夜天气十分凉爽。
她已经打包好日记和她要寄给吴sir的东西。
突然门被敲响,持续又迟缓得敲着。
她打开,惊讶得愣在原地。
门外地板上的影子里走进一个覆盖上那瘦弱影子的高大身躯。
“你要干什么?”
沈沭看向他,打开门时从楼上那被打碎过的窗户里传来舞曲音乐,悠扬得配合此刻的月光。
一切都是那么柔和。
男人微微红的腮下不停喘动着浓烈的气息。
他开合的齿间飘出清香的酒味。
“要你。”他道。
沈沭张大了眼睛。
伴随着她一句“你疯了?”
还没落下,就被一阵顺着风席卷而来的身躯扑向身后的床。
门被猛烈的关上,海面荡着几层宁静的波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