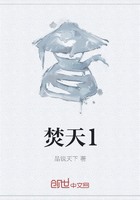良文玉走后,回春堂的庭院中便多了一个孤独的背影,在皎洁的月光下被拉的悠长,时常一个人在月光下发呆。
“丁前辈……”,突然一阵急促的叫声打破平静,只见一只灵猴从门口蹿进来,像它第一次进入庭院一样,上窜瞎跳,抓耳挠腮。随后,一个少年急冲进来,怀中抱着一个姑娘。尽管已经入秋,天色渐凉,依然能看见他浑身上下汗流浃背,而他怀中的姑娘已经气息奄奄。
龙吟回神一看,眼前的少年竟是那日替他们解围的羽翼尘,而他怀中的奄奄一息的姑娘就是荆柔若。吃惊地问道:“荆师妹怎么了?”
又转头冲着内堂大喊道:“师傅,快出来。”
丁白鹤听到叫声从内堂走来。羽翼尘一见丁白鹤,抱着荆柔若双膝跪地道:“还请丁前辈救她一命。”
他从未求过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求人,说着就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当一个人足够在意的时候,他的很多行为多半不由自主。
丁白鹤一边扶起他,一边说道“请进内堂说话。”
丁白鹤将手搭在荆柔若脉上,面色凝重道“你们遇到阴毒老祖了?”
羽翼尘道:“没有。”
丁白鹤心道:“如此伤势显然是阴毒老祖的寒冰针所为,自那日离开之后,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了阴毒老祖的消息,这伤又是从何而来。丁白鹤疑惑道:“她这伤是何人所为?”
羽翼尘道:“凤歌。”
丁白鹤道:“凤歌是何人?”
羽翼尘道:“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他是七生门门主,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之前江湖上的一些大案都是他所为。”他也不知道丁白鹤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总觉得回答的越详细可能对荆柔若的病情越有帮助,
丁白鹤摸着胡须喃喃道:“奇怪,阴毒老祖何时有了传人。”
羽翼尘对凤歌是何许人并不感兴趣,他只在乎荆柔若的伤势。见丁白鹤如此迟疑,上前一步关切的问道:“丁前辈,她的伤能治吗?”
丁白鹤道:“她中的是印度老祖的寒冰针,中伤者体内阴寒,若不是少侠强行用内力给她续命,恐怕命已休矣。只是阴毒老祖已许久未涉江湖。我只道他这门绝技已经失传,竟不料这世上还有传人。这种伤我也没有治过,但如果用千年的天山雪莲做药引或可一试。以天山雪莲祛除她体内的寒气,再把她体内的寒毒逼出来。”
羽翼尘急问道:“这千年天山雪莲哪里能找到?”
丁白鹤道:“这千年雪莲地处西域,对海拔、地势、气候外部生存条件要求极高,存活率极低,要摘得一株绝非易事。”
羽翼尘深情的望着荆柔若道:“纵然刀山火海,我也义无反顾。”
羽翼尘对附身对荆柔若耳边轻轻说道:“等我回来,”说着转身就要出门。
丁白鹤道:“少侠留步,你恐怕要带上她一起上路。她体内的阴寒之气,全靠西门叶梭70年的功力续命。少侠此去不知何时能归,只怕万一……”说到这里,他表情突然有些凝重。
羽翼尘已经明白了他的话,他俯下身慢慢抱起荆柔若。说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半步。”
说着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话说那日羽翼尘走后,众人尽皆散去。漠北双雄行至丛林之时。只听背后一声娇喝:“淫贼哪里走?”
二人刚一回头,一根金铃索迎面打来。二人退后一看,来人竟是那日他们调戏的良文淑,背后站着一个手拿玉扇的翩翩美少年,及一众人等。良文淑当日迫于无奈,被他二人胁迫,一直愤愤不平。这次恰好有机会,想趁机出了这口恶气。
漠北双雄一看他们人多势众,心道:“如此情形绝对讨不到半点便宜,三十六计,先走为妙。”二人相互使了一个眼色。假装不敌,边打边退,良文淑只道二人如此不堪,攻势越来越猛。
一旁的良文玉看的一清二楚,他们显然是有意如此,他也并不着急出手,一来想让妹妹出出恶气,二来是在凤歌的地盘,不知道他们跟凤歌什么关系,也没有贸然出手。
不一会良文淑就将二人逼到了斜坡边上,二人同时向斜坡跳下。骆通的位置离良文淑更近,跳下时回身甩出飞刀,刚好打中良文淑肩部,良文淑脚下一滑,也随着他们一起滚下山坡。
人还没停,只见一少年脚踏白马,手提长枪,飞奔而来。漠北双雄吃了一惊,来人竟是连日来追赶他们的罗非,当下也不及多想,拔腿就跑。罗非将良文淑扶上马,刚想问她伤势如何,就听见良文淑娇喝道:“快追上他们。”
罗非一拉缰绳冲二人飞奔而去。
不觉间,天空下起了雨,广西的天气就是如此,雨天比晴天多,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两人行至河边时,马奔跑速度过快,脚下一滑,连人带马,一起落入水中。漠北双雄见状,心中暗自窃喜,只道二人会就此丢了性命。
罗非正睁着漠北双雄的方向,全然没有注意脚下,突然被马带入水中,当真吃了一惊。两人瞬间被河水向下游冲去。此时良文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力气,她手臂死死抱着罗非的脖子。罗非一边奋力抓住岸边的树枝,一边将长枪递给良文淑,示意她抓住长枪。否则被人在大水中搂着脖子根本无法呼吸。大雨淋湿了罗非的头发,盖得他完全睁不开眼睛,只能看见眼前一个模糊的身影。
罗非挣扎着爬上岸边。一只脚缠在岸边的树上,另一只脚向前撑着,身体后倾,用尽全身力气,将良文淑拉上岸边。
此时两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良文淑刚上岸就已经昏了过去。罗非也是仰面朝天,大口喘息着,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躺在大雨中。
过了好一会,罗非缓过一口气,发现身边的良文淑还在昏迷中。他慢慢的将八节枪拆开,绑在双腿上。他习惯了这样的方式行走,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丢下自己的枪。
罗非将良文淑伏在背上,慢慢向前走着。不一会走到一个山洞下方。罗非从路边的树上扯下一根藤条,将良文淑缠在身后,驮着她向山洞爬去。大雨冲刷下的岩壁相当丝滑,手下根本不好着力。罗非一只手先抓住一块岩石,然后用手臂撑在崖臂上,给身体一个着力点,然后人再慢慢向上爬,尽管从下面看,这只是很小的一段路程,但罗非却用了很长时间才爬到洞口。到达洞口时,四肢勒的全是血痕。
罗非在山洞里找来一堆枯草,将良文淑慢慢放下,人已累得筋疲力尽。不觉竟在山洞里睡着了,此时良文淑还在昏迷中。洞中万籁俱静,只能听见二人的呼吸声。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罗非在一阵寒风中惊醒,打了个冷颤,慢慢起身,发现外面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黄昏时分,伴着雨后的彩虹,从洞口看去,美如画卷。罗非自幼在西夏长大,并没有见过南方雨后绮丽的美,不觉看痴了。
不知从哪传来了一阵叫声打破了思绪。罗非起身,顺着声音找去,只见一只野鸡在草丛中穿梭,罗非紧紧跟在后面,随手抓起一块石头,冲着鸡头用力一甩,那野鸡就瘫倒在地。须知他从小在部队练习打靶射箭,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罗非又从山洞里找来一些枯枝,在里面支起一个架子,将野鸡放在上面,用打火石点燃。
“妈妈、哥哥……”,火光下,良文淑神志不清的说着梦话。罗非扭头一看,只见她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像是中毒的迹象。之前在黑暗中,罗非并没有怎么注意良文淑,只觉她可能是太过劳累,暂时昏迷。
如今看来情况不妙,他左手一探良文淑的额头,只觉她额头滚烫,再看她人神志不清。罗非心道:“刚被大雨淋湿,又穿着湿衣服睡了这么久,应该是发烧了。”
罗非又掀开良文淑的肩口,只见伤口处瘀紫,边缘部分在河水浸泡下开始泛白,显然是中毒所致。立即趴在她肩口上,大口吮吸。不一会,良文淑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但觉肩口隐隐作痛,慢慢睁开眼睛,只见一人正贴在自己肩上大口吮吸,大叫一声“你干什么”,一个巴掌已经甩出,罗非刚抬头时恰好嘴里刚帮她吸了一口毒血,这一巴掌正好将他口中的毒血打出来,不偏不倚,全部喷在良文淑脸上。良文淑这一巴掌甩出,人已经没了力气,又瘫倒在罗非怀里。罗非见她脸上被喷的全是毒血,准备用衣服想帮她擦拭,结果手抓衣服时由于太过紧张,又碰到了良文淑的胸部,人还没反应过来,又挨了一个耳光。
火光照射下,只见罗非脸色绯红,不知是火光照射还是太过害羞,亦或是被打的结果。
罗非连续挨了几个耳光,人突然就懵了,呆呆地望着良文淑,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
火光下,只见良文淑浑身湿透,肌肤胜雪,散发着少女淡淡的体香,发丝上还沾着未干的雨滴,在火光下折射出斑斓的色彩,更添了几分明艳动人。良文淑娇嗔道“你在看什么。”
罗非回过神来,支支吾吾道:“没看什么。”,说着眼睛不知道该看向何处,一会看向四周,一会又看看良文淑的反映。
他越这么说,良文淑越生气,道:“你还看,哼,你们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说着竟哭了起来。
罗非自小在军队长大,对男女之事本就木讷,此刻他与这妙龄少女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本是救人心切,却被人连续扇了耳光,更让他不解的是,对方却先哭了起来,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说道:“都是我不好,在下不知哪里冒犯了姑娘,还望大人不记小人过。”
良文淑当然知道他绝不会有非分之想。只是他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想到近日来的遭遇,又与哥哥走散,心中委屈才不觉哭了出来。但罗非如何懂得女儿家的心思,只道是自己得罪了她。良文淑也不理他,只管自己哭泣。
过了好一会,罗非起身向外走去,良文淑道:“你干什么去?”
罗非道:“姑娘伤口中了毒又感染了风寒,我去找些草药给你敷一下伤口,随便看看有没有什么驱寒的东西。”
良文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人待在山洞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就对罗非说了一句:“那你早点回来。”
罗非点点头便向外走去。
不一会,罗非带了两把草药回来,手上还拿了一个半破的陶瓷罐。
他将其中一把草药放在嘴里嚼碎,然后吐出来敷在良文淑伤口上,良文淑只觉伤口处先是先是像被蜜蜂蛰了一下,继而又是一阵清凉。
罗非抓住良文淑肩口的衣角准备撕开,却被良文淑一把推开。问道:“你干什么?”
罗非道:“姑娘的伤口部位已经化脓,要让它全部露出来透气,这样就恢复的更快。”
良文淑道:“不早说,人家哪里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说着慢慢把手拿开。
罗非本来没想太多,被她这么一说,反倒有些顾虑,疑惑道:“那我现在能撕了吗?”
这种事于女孩子本来就不好讲出口,良文淑羞红了脸,低头道:“你讨厌……”
其实女孩子在脆弱中有更强的保护欲,很多举动也只是下意识的反映,但罗非到底是为人耿直,于女儿家的心思一窍不通。依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挠着头问道:“那我到底能不能撕?”
良文淑道:“哎呀,你笨死啦,难道要人家自己撕吗?”
罗非这才恍然大悟,小心翼翼的将良文淑肩口的衣服撕开,用纱布包扎好。然后将另一把草药放在破罐中捣碎,添上水放在架子上。
不一会,良文淑觉得伤口好多了,没有之前那么痒疼了,她好奇的问罗非道:“你给我敷的是什么。”
罗非道:“野田七,一种专门止血化瘀的草药。”
良文淑道:“那你现在熬的什么?”
罗非道:“是一些驱寒的草药,你感染了风寒,喝些汤药会好点,我随便找了一些,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
良文淑本来还有些虚弱,被他这么一说,噗嗤一笑道:“你怎么这么傻,哪有人喜欢喝药的。”
罗非心道:“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难懂,一会哭,一会又笑。”他也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只道她高兴就好,不要再来寻自己的不是,只是赔笑的点了点头,并不答话,低头只管熬药。
不一会,药罐开始沸腾。这时飘来了阵阵鸡肉的香味,罗非之前烤的野鸡也熟了。罗非准备想先把野鸡拿下来,刚伸手发现药罐里的水溢出来,又慌忙找东西把药罐端下来,罐还没有放稳,又跑去拿烧鸡,此时鸡已经被烤焦了,药罐里的药也撒了一半……
罗非喂良文淑喝下汤药。对良文淑道:“姑娘现在好点了吗?”
良文淑道:“好多了。”
罗非道:“姑娘可以将湿衣服脱下来,在火架边烤一下,待衣服干了再穿上便是。”
良文淑觉他说的也有道理,自己穿着这湿衣服确实难受。对罗非道:“那你先出去,不许偷看。”
罗非转身向洞外走去,到洞口时回头对良文淑说道:“我就在洞口,姑娘有事叫唤我。”
罗非一个人坐在洞口,观察天上的星星。初看时,只见一颗最亮的星星横挂正中间,周围无数小星星围着它不时移动。不一会他就入了迷,以最亮的星星为首的星星不时向左移动,而它正前方的星星又不断向它原来的位置移动,罗非将它们想象成两支军队,双方在移动中你来我往,激战正酣,眼前的场景像极了孙子兵法中的“围魏救赵”之计,想到忘情处,他口中还时不时喊着:“冲……”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洞里“啊”的一声大叫,罗非的思绪被打破,他慌忙跑进洞里,这一下当真是非同小可。只见良文淑半身裸露,只穿一个肚兜,手里拿着刚烘干的衣服,影子映射在墙上,呈现出一个迷人的酮体,正不知所措的看着自己。原来她正准备穿衣服时,脚下一只蟑螂爬过,良文淑不自主的大叫一声,罗非以为她遇到了什么危险,就慌忙冲了进来。
两人瞬间都是一惊,良文淑赶紧用衣服遮住上身,大叫道:“谁让你进来的?”
罗非赶紧转身退出去,边走边解释道:“对不起,对不起……”边走心里还翻江倒海,心道:“还好是离得远,这要是离得近,脸上不知道又会挨多少耳光。”
良文淑也不理他,快速把衣服穿上。一会良文淑道:“你可以进来了。”
罗非缓缓进来,发现良文淑已经穿戴整齐。他不敢靠近,生怕又挨耳光,远远对着良文淑道:“在下并非有意冒犯,我以为姑娘有什么危险,情急之下,所以……”接着又支支吾吾道:“我什么也没看到。”
良文淑只觉这是羞愧难当,道:“你不要再说了。”
罗非再也不敢多言。
次日,罗非早早地起来,想去寻找一些野果充饥。刚走出洞口就发现漠北双雄两兄弟径直向山洞走来。立马返回洞中,将此事告诉良文淑,并对良文淑说道:“咱们先找个地方躲一下吧,你身上有伤,咱们打不过他们。”
良文淑并没有想走的意思,悄悄凑到罗非耳边窃窃私语了一阵。
罗非疑惑地看着她道:“背后伤人,会不会有失君子所为?”
良文淑道:“亏你还是个将军,用你们的话这叫兵不厌诈。况且他们本就不是什么正派人士,跟他们讲什么江湖道义。”
罗非心道:“也是,毕竟这二人在西夏为非作歹多年,多年抓他不住,今日结果了他们也算是给之前他们坑害过的人一个说法。”
于是他慢慢解下腿上的八节枪,将它们拼在一起。
良文淑跑出洞口,故意在漠北双雄视野内摘几个野果让他们看到,然后跑回洞中。
漠北双雄见良文淑一人,一路追着她的方向来到洞口。他们悄悄走到洞口,探头俯耳,只听良文淑嚎啕大哭,边哭口中还边喊:“罗公子,你千万不能死啊……”
漠北双雄当然知道她说的是罗非,当时心下暗喜,心道:“这罗非怎么突然会死呢?莫不是之前落入水中,溺水所致。”
二人探头往洞里一看,只见良文淑抱着罗非的头痛哭不止,边上散落了一地野果。罗非脚上缠着纱布,奄奄一息地对良文淑道:“想我纵横沙场一生,今日却被区区一条毒蛇要了性命,我怕是活不成了,你不要管我,快点走吧。”
良文淑哭着说道:“不,要走一起走。”说着声泪俱下。
二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罗非是被毒蛇所伤。
“哈哈哈……”骆通当先跳进洞口,笑着对良文淑说道:“小娘皮,你早晚还是逃不出咱们兄弟的手掌心。”边说边搓着双手,色眯眯的盯着良文淑。他兄弟二人那日就对良文淑有非分之想,今日见罗非死去,良文淑孤身一人,顿时又起歹心。
良文淑一见二人进来,表现出极度慌张的样子,胡乱抓起身边的野果向二人扔去,边仍边喊:“不要过来……”,还不时低头对罗非说道:“罗公子醒醒。”让人完全卸下防备,只道罗非已经必死无疑。骆通低头再看,罗非依然半眯着眼睛,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当下也不犹豫,大踏步向良文淑走去。待骆通走近,良文淑突然滚开。只见罗非左手在地上一撑,人已经侧立而起,右手一枪刺出,一招“将军夜引弓”,正中骆通咽喉。顷刻间,骆通当场毙命。这一下变化之快,动作之迅,当真让二人始料未及。连骆通自己都没有想到,还手的机会都没有。骆宇见转,扭头就跑。刚转过身,发现腰间已经被一支飞来的铃铛缠住。罗非纵身而起,一枪刺在骆宇后颈上。只是片刻之间,罗非就登时结果了二人性命。
就在两人倒下之际,罗非突然朝着洞口方向跪地叩拜,时而又仰面痛哭,口中不时喊道:“爹娘在上,今日我终于手刃仇人,为你们二老报仇。”与之前一贯温文儒雅的形象判若两人,这一下倒是让良文淑吃了一惊,这漠北双雄竟与他有杀父之仇。她只道罗非千里迢迢追赶二人只是为了将其抓回西夏。
良文淑见罗非情绪有些激动,一时也不知如何劝他,只是轻轻摸着他的肩膀道:“没事了,都过去了。”
许久,待罗非情绪稍有平静,良文淑问道:“他们是你的杀父仇人?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罗非抬头望着天空平静地说道:“19年前的一个夜晚,西夏的一个偏远小镇,下着瓢泼大雨。两个盗贼闯入一户人家,准备盗走他们家中的祖传之物,前朝皇帝御赐的一幅画,也是他们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后来事情败露,被当场抓住,他二人竟起了歹心,狠心将这一对夫妇杀害。家中唯一的老仆趁夜黑抱走了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没过多久,老仆也过世了。那孩子孤苦无依,后来被一个将军收养,收为义子,并传他武艺,并请高手匠人替他打造了一根八节枪。”
良文淑若有所思的问道:“那两个盗贼就是这两个坏蛋,那对夫妇就是你的父母,而那个孩子就是你?”
罗非道:“是。”
良文淑心道:“想不到这儒雅少年身上还背负着如此血海深仇。”
这也让良文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试图从一个人的相貌中读懂他的全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能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