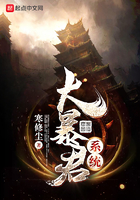劲风从深渊往上吹,峭壁上布满了青苔,几根小小的树苗从悬崖的缝隙中探出,在风化的岩石上,努力地汲取着阳光和空气。峭壁上还能看到几从荆棘,开着淡紫色的花朵。
陈晓雨喊道:“你不要命了吗?”风委实太大,他只有用喊才能让杨羽芊听到。杨羽芊不说话,陈晓雨喊道:“抱紧我!”随即迅速拔出了剑,将之深深插入了悬崖之中。
由于两人的惯性太大,剑在峭壁中留下长而深的划痕,那划痕拖了几丈远才停下,此时陈晓雨已经筋疲力尽。
杨羽芊却欣喜道:“你终于拔剑了。”
陈晓雨:“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
杨羽芊:“谁让你先疯的?”此话一出,直接将陈晓雨噎住,陈晓雨沉默半晌,道:“你说的对,的确是我先疯的。”
陈晓雨看着自己插在悬崖上的剑,再看看此刻抱住他的杨羽芊,像是想通了什么。他想想自己刚刚的出剑,哪里有片刻的迟疑?整个天下,藏龙卧虎,比自己厉害的何止许村山一人,可难道因为无法胜过他们就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吗?
什么才是拔剑的真正含义?在浩渺的远古,人第一次拔剑或许只是因为和一头野兽的狭路相逢。拔剑,不过是人在危急关头的求生本能而已。
拔剑,可能死,不拔剑,一定死。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只是最简单的道理,往往需要经历许多复杂的事情才明白。
峭壁中的剑齿松动,竟有几分要脱落的迹象,陈晓雨用尽全力将杨羽芊扔了上去,而下一刻,剑终于从峭壁中脱落,陈晓雨落向谷底,而杨羽芊飞向崖顶,她的眼泪被狂风吹散,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死!”
她无助地伸出手,渴望可以抓住他,而他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陈晓雨看着杨羽芊,她一身红衣翻卷不息,像一朵在风中盛开的玫瑰,一如他和她的初逢。
杨羽芊落在了崖顶边缘,而陈晓雨还在不断下坠,他调整身形,再次尝试将剑插入峭壁中以减缓下坠的速度,只是因为实在没了多少力气,效果大打折扣,突然感到下方有什么东西出现在视野中,陈晓雨还没反应过来,便撞了上去,随即失去了意识。
陈晓雨恢复意识时,才发现自己撞在了一棵树上,幸运的是自己只受了些外伤,而且体力已经恢复了许多,若非经过刚刚的缓冲,现在怕是爬都爬不起来,陈晓雨心想。
他抬头望向崖顶方向,只见一片云雾缭绕,往下看去,同样是深不见底,树的周围虽然有些藤蔓,却不知道这些藤蔓有多长,延伸到什么地方,在当他思考如何离开时,他却发现了在这棵树不远处,居然有一个山洞。
陈晓雨顺着藤蔓荡了过去,一个纵身便跳向了山洞中。在跳向山洞时,陈晓雨便感到了些异样,果然,落向山洞的那一瞬间,陈晓雨便看到自己跳向了张“巨网”,陈晓雨下意识的挥剑便斩,待他落到地面上时,那张“巨网”已经被斩为两截,无辜的躺在地上,这时他才看清,那不过是无数藤蔓编制而成的吊床。
吊床的不远处,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长长的胡子凌乱不堪,显然是缺乏打理,而他的手中,却捧着一把黄色的野雏菊,像是要给吊床做最后的装饰。那捧野雏菊,在陈晓雨的注视下,全部扔在了地上。
那人怒道:“好个无理后生,老夫千方百计找了这么个好地方睡觉,都被你给搅黄了!”
陈晓雨赶紧赔礼道:“前辈对不起,对不起。”那人哪里会听他解释道歉,随手捡起地上的半截藤蔓便攻了过来。
陈晓雨看得分明,那软软的藤蔓,到那人手中突然变直,可见那人的内功造诣是多么纯熟,这跟束衣成棍,有什么分别?
陈晓雨拔剑应战,藤蔓与剑相击,竟然丝毫无损,陈晓雨此刻用剑,不再有丝毫的犹豫,他已然从许村山造成的阴影中走出。凌厉的快剑如行云流水一般,直逼得那人一步步后退。剑意潇洒恣意,浑然天成,那人也不免称赞道:“好剑法!”随后说道:“老夫要认真了,小心!”
说罢改换剑招,发起反攻。看似剑招迟缓,可陈晓雨知道这剑招远比之前的剑招要凶险得多。之前的剑招虽然迅疾,但变化却少,一剑刺出,便成定势,而现在的却不同,剑招缓慢,却每一招都包含了多种可能,每一招都暗含了其他的杀招,这正是以慢打快的打法。
陈晓雨不敢大意,全力应战,两人在算不上宽敞的山洞中上下翻飞,不断拆招。陈晓雨感到对方越发难缠,攻击的方位也十分刁钻,从藤蔓各种奇怪的角度攻来,陈晓雨越发感到吃力,危急关头,使出公孙所传的忘忧六式,瞬间转守为攻。
那人看到陈晓雨使出这套剑法,当即大惊,继而大喜,两人继续交战,陈晓雨右手手肘处被点了一下,他只感到一阵酸麻,右手便失去了力量。当他漆黑的长剑掉落在地时,那人的藤蔓恰好落在他的他的左胸,只是藤蔓已经不再笔直,很显然,在最后的关头,那人收敛了自己的内力,以免伤及陈晓雨。
陈晓雨道:“我输了。”
那人将藤蔓随手一扔,仰天长叹一声,道:“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曾见过这套剑法了。”随后转向陈晓雨,道:“想必你便是公孙的弟子吧。”
陈晓雨这下也十分吃惊,道:“难道前辈认得我家师傅?”
那人道:“何止是认识。”声音中竟有几分落寞和悲怆。
那人走到山洞边上的一张石床上缓缓坐下,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陈晓雨跟着走了过去,那人道:“我本是魔教大长老,一生独来独往,除了你师父公孙无忧之外,再无其他朋友。”
陈晓雨这下更惊讶了,差点没再次拔出剑来,魔教在他看来,都是罪大恶极之徒,可转念一想,此人自然自称是师傅朋友,而且刚刚有意识地避免伤及他,那便一定和魔教的其他人不同了。魔教的大长老?师傅的朋友?他心中不禁有几分埋怨师傅从来没有给他说过自己的往事。
陈晓雨在记忆中搜寻,总算找到了师傅曾说过关于一个朋友的只言片语,那是师傅偶尔说起往事时,用过最为少见的两个字——朋友。陈晓雨只知道那人叫顾柯怀,却从未想过,那人会是魔教的大长老,也从未想过,会在这样一个破山洞中被自己撞见。
公孙总是这样,许多事情总是蜻蜓点水地说一下,待陈晓雨追问,他又闭口不答,故意将话题转向他处。若是陈晓雨逼问得急了,他便说:“该知道时你自然知道了。”这几乎都成了公孙的口头禅了,只是这些话,反倒越发激起了陈晓雨的好奇之心。
陈晓雨:“顾前辈为何叫我家师傅公孙无忧呢?”
顾柯怀:“没有‘无忧’,何来‘忘忧’?”顾柯怀叹了口气,道:“终究是为情所伤罢了,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早便退隐,我也不会一个人孤独这么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