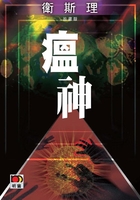夜色正好,微风徐徐。
少女的簪子被透过指缝间的月光照得花眼,淡绿色的裙摆被风儿轻轻托起,正好配上出门时披得满身银光。
眨眨眼,不紧不慢地放下了刚刚高举上空的右手,又表面性地整理了一下衣襟,这才上前两步。
屋檐的一方檐角有着被修补数次的痕迹,刚走的春雨留下孤独的檐角滴滴答答,脚下斑驳的三两台阶生了青苔,这里似乎存在许久了。
少女欲要开门,却停顿了一下,转为敲门的动作,又突然开始若有所思起来,停下了动作,开始对门旁那层薄薄的窗棂纸打起了主意。
做贼心虚地俯耳贴着窗棂纸,只听得有一气没一气的小孩子的哭闹声,少女像泄了气一样,身子又往下沉了沉。
“还打算偷听到什么时候?”
门忽地一下打开来,险蹭过少女脸颊,里面跨步走出一位容貌较好的女子,清雅不失几分成熟。
这可着实让少女吓得直起身板往后哆嗦了一步。
“师、师姐早啊!”已经开始结结巴巴了。
少女尴尬地笑了笑,又被抓包了……
“你啊……”那无意开门有意吓人的女子无奈地用手指点了点少女的眉心,“进来吧。”
少女笑嘻嘻地跟上了口中的“师姐”,可这刚一进门,就被一个小孩子冲过来抹鼻涕抹眼泪紧抓裙摆不放。
“呜呜……江小姨,阿娘不让我,不让我娶阿月……”
哭诉完了又接着揪起少女裙摆一通乱抹。
估摸着他亲娘也不少遭抹。
少女深吸一口气,瞧见半躲在屏风后的小姑娘,皱着眉头一个劲儿地朝自己使眼色。
换好了衣服的师姐边合屋门边扭头看,眼看自家儿子在师妹身上抹得差不多了,许是心里平衡了,才忍着笑意清嗓开口。
“哎,小兔崽子你可别血口喷人啊,就算我同意,你姐姐能同意吗?再说了,人江月可不喜欢爱哭鼻子的小鬼。”
听了这话,男孩半晌才整理好情绪委屈地向后撤了几步,抬着头两眼泪汪汪地望着自己当亲人的江希苋。
“来,江月,过来。”
没法子啊,谁叫江月是她捡回来的呢?少女轻叹一声,可怜自己年少命苦又当娘。
名叫江月的女孩儿这才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眼神中掺杂着些许复杂,但并未作声。
沈尘川似是看出了江月的为难,撇着嘴,带着未褪的哭腔说道:“我家教书的先生都说了,要是当真喜欢一女子,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若是自己看来,那通通都不好使了。小姨,我是一定要娶江月的……”男孩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怯生生地望了望阿娘,“等我像先生那般出人头地,就去你家提亲。”
江月知道,沈尘川只是借着江希苋壮自己胆的机会,把事情说明了说透彻,可江月不知道的是,不知道那些情爱之事。
少女一头雾水,默默地在心里酝酿着作答的话。
“那就等你出人头地再说。”师姐摆摆手继续道:“过两天给你换个更好的先生,给你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愣着干嘛?还不快去睡觉。”
说罢便瞪了少女一眼。
就好像那逐客令是对她下的一样。
少女叹了口气,定了定神,一本正经地对着沈尘川说道:“尘川,你听姐说,等姐成了盛安最富的富婆,就给江月备好整房整房的嫁妆等你来……”
“江希苋!”
“哎!师姐你别推,别推我我能走!江月?江月跟上!”
“砰”的一声,一大一小就这样被赶出了门。若不是深夜,还寻思着谁家倒霉的酒鬼又被赶出来了。
江希苋叹了口气,明明是来找自己帮忙把寄养的江月带回去的,怎么连送客都这么霸道……
“你怎么来了?”
江月很少先开口。
二人并排背靠着木门,江希苋沉默良久,刚要开口,忽的一下房内的光亮被吹灭了,吓得少女抖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收留你的大妈叫我接你回去。”
“不是还有两个月吗?”
江希苋刻意地压低了声音道:“两个月?你住了还不到一个月师姐就给我来信了,说是沈尘川那小子对你死缠烂打你是百挠不屈,场面一度精彩。别说三个月,就是半个时辰,她也不想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便心思都放在了儿女情长上。”
不过这样也好,倒省了方才那番口出狂言之势,也不知光是那嫁妆就要吃她多少!
显极了不情愿:“走吧,赶紧回家,这夜黑风高的,要是哪里窜出来大批的贼,咱俩咋死的都不知道。”
说完二人便朝着府邸外的大道走去。
其实嘴上说着是“娘俩”,但实际上二人也就只相差了四岁。小的也才刚刚垂髫,大的捡小的,小的才不愿喊声“娘”。
“江希苋?”江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看上去些许烦躁的少女。
“又怎么了?”不耐烦地踢远了脚边的小碎石。
“娶我是什么?”
“娶你是傻狗。”这次踢的是水缸,显是知道了疼,这才收敛起来。
“……”
二人悠闲地走着,有时路过谁家灯火明亮,还会上前去敲门试探着要个钱讨个债,可灯火总是会在一串的敲门声过后巧合得灭掉,再接着就是江希苋的一个个朝天翻的白眼。
“白眼狼。”
“啥?谁教你的?”
江月别过头,不再看江希苋。
“沈尘川家教书的。”
“真真该换。”
当初还是自家那做私塾的表亲,非得力荐自己的学生去师姐家教书,江希苋还没表上态,师姐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却怎么也想不到竟是把自己搞不定的学生随手丢了出去。
着实令人头疼。
从院落到大道,又从大道到城门,再穿行那片竹林,就能看见林中的旷地上有间粗糙的竹屋,那儿便是家了。
还未走近,江希苋便远远地瞧见了屋外桌子上被月夜笼罩着的长剑,心里不知是喜是忧,只是嘱咐了江月两句就去了城中的花马小道。
来回小半个时辰的路途,江希苋硬生生要走上一个时辰。
那是一家无论何时都不会打烊的酒馆,白日里是老板娘与自家女儿管账,夜晚则是老板一人管账,当然连馆里的厨子和打杂的下人都是分批干活儿的,所以若是碰见生面孔,也不必过于惊讶。
那儿的老板是个鬓角微白的中年男人,一双被岁月拂过的弯成了月牙的眼,眼角似弯起时触了千年湖面,又在一瞬间结了冰霜。
江希苋好极了同他打交道,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浮上心头。
“老板,还是老样子。”
说着,江希苋便递上去了自己随身携带着的酒葫芦和几枚铜钱。
“好嘞,您坐那儿歇歇,一会儿就给您拿来。”
“嗯,谢了。”
坐上长凳,趴在被酒酿浸过千万遍的老旧木桌上,深吸一口,缓缓地合上双眼,思绪万千。
……
“老板,来坛桂……”刚入了酒馆的少女,瞟见了角落里趴着的江希苋,又改口道:“嗯……一坛桂花酿,一坛桃花酿。”
清朗的女声扰了思绪,江希苋眼皮也没抬一下,又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趴着。
都这么晚了,是谁还没有回家舒舒服服地做上一个美梦呢?
谁知道呢……
只觉睡意昏沉。
一袭华服的少女面无表情地坐到了江希苋身旁的位子,欲言又止。
那老板看到这二人的样子也不禁乐呵了起来,把酒抱到了江希苋趴着的那张桌子上,就刻不容缓地避开他俩去忙活别的了。
许是酒馆内来的人多了,越发觉得吵闹。
耳边的嘈杂声也随着意识的清醒越来越清晰。
再一睁眼,已然是日上三竿。
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看看酒馆里的客人,花马道上的行人,还有高高的的日头,再用衣袖蹭蹭嘴角的口水,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又忽地觉得肩膀有点沉。
酒馆里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儿看见她醒了,便放下手中的活儿踱步走过来,嬉皮笑脸地说道:“可算是醒了,你周围一圈儿我可没叫他们坐过,来些水提提神?”
女孩细长的柳叶眉在这个年龄段更显几分清秀,那双俏皮水灵的桃花眼溢满了笑意,圆圆的脸蛋也有些可爱,在江希苋印象中,她总是着一身鹅黄色的襦裙忙碌地在酒馆中跑来跑去。
“有心了,呼,还是好困。”可同是及笄之年,江希苋觉得自己的灵动可爱也还要比她差上几分。
江希苋摆摆手,把脸埋在掌心中蹭了两下,这才发现桌上除了自己的那壶酒,还赫然地多出了一小坛酒,以及身上做工精细的暗青色衣袍。
这让她大梦初醒便一头雾水。
待到回过神时,少女已经递过来了一杯刚烧好的水。
“晾晾吧,也不急这一会儿,喝完再走。”
“好。”似是想起了什么,又叫了一声扭头就要干活的女孩,“菁竹。”
“哎,怎么啦?”菁竹应了一声又转身走了过来。
“这袍子,还有这酒,是谁落下的?”江希苋伸手分别指了指这两样物件。
“我爹爹也没同我细说,只是叫我好生照看你。若是你问起来,只说这些都是一少女赠与你的。”
“哦……那你这儿能替我保管一下这大衣吗?万一她回来取……”
菁竹摇了摇头,严肃道:“不能不能,虽然我不懂,但是这个做工和刺绣一看就是官家人才穿得起的,这么贵重的物件儿我可不敢收。”
“好吧,麻烦你了,那我就不打扰你干活啦。”
眼瞅着菁竹又去忙活了,江希苋将大衣平铺在木桌上,细细观察着。
衣领上是与其颜色相近的不规则刺绣,衣身绣着狐狸与丹顶鹤的样式,狐狸邃紫的眼睛,丹顶鹤头顶的一点朱红,绣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美感,使得两只动物间的争斗意志更添几分,以青色渐变的山河刺绣为背景,如此鬼斧神工,就是当代最好的绣娘也要赞叹一下。
收起又惊又喜的眼神,这毕竟不是自己的衣物,还是要想个办法还回去啊,这么贵重,哪能轻易送人?别要是哪天讹上了自己……
“唉……”江希苋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宝贝似地将衣物叠好后,不忘把随身携带的酒葫芦绑在了腰间,水晾得差不多了,便一饮而尽,温热过喉,犹感舒适。
一手抱起衣物,一手提着陌生人赠的酒,向酒店老板娘告别后,直径向门口走去,却被抽开身的菁竹喊住了。
“阿苋?我听说封崖之战早早打完了,好像比预期要早了几个月呢!估摸着常叔也差不多回去了吧?问问这次战事如何,据说这事儿官家可没叫往外说……哦,对了,记得代我问问他何时还欠下的酒钱。”
“好好好,有空来做做客听说书?”
“去,一定去,嘿嘿。”
这边刚应了江希苋那边又被老板娘叫了去。
菁竹整天像个大忙人,有时闲下来也只喜欢听常叔讲驰骋沙场的那些事儿。
好的是只要这次战事一结束,无论成败,常叔都会告老还乡。
毕竟这也是他同江希苋之间的约定。
待到江希苋回到家中时,桌上的剑已经不见了,按理说十余年来一直都是江希苋在替他收拾,他也绝不可能勤快起来。
一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了。
江希苋慌乱地将手头的衣物和酒撂在了桌上,跑去推门而入,动静不小,只见江月坐在椅子上被粗麻绳绑得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