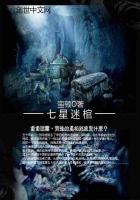我内心微疑,只静等方为雄开口。
许久,方为雄低低的,道:“凰现,凰现,天下安。天意,天意呐。”
我瞬间一震,旋即,盯向方为雄,问他:“你,是谁?”
方为雄却道:“小主,可还记得,臣之字?”
我点头:“南光。本宫记得的,一直记得。”当年,他救我,我去谢他,他亦是避了所有人,只求我,记得他的字。
方为雄道:“小主,请你永远记住,南光,是臣。”
我心头疑惑更甚,我正想问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不想,眼前一黑,耳畔只传来方为雄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小主,你必须回京,你也只能回京,原谅臣的不得不为之。”
然后,什么都听不见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中,我先是梦见了那场大火,然后,我又梦见了父亲梦见了师兄梦见了所有人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再然后,我看见了莫寻,缓缓的朝我走来,近了又近了,莫寻的面具在瞬间脱落,映出了面具后的容颜,眉如远黛眸如深泓,鼻翼挺直,笑若春风,我笑着跑过去,张开双臂紧紧的搂住莫寻,哦,不,搂住我的师兄,只是我的师兄,当世独一无二的夜朝歌。但是,就在我的双臂触及师兄时,师兄不见了,莫寻不见了,我只瞧见一缕轻烟从我臂弯间飞走,化为虚无。我张了张口,想要喊,却是怎么也喊不出口。我仓皇四顾,却看见,深深的宫殿,九层金殿,七重宝塔,金殿至高处,是幼时的烨儿站在风雪中,看着我,喊我:姑姑——。倏然的,烨儿长大了,是少年帝王站在城墙之上,一身锦绣龙袍随风飘猎,看着我,是帝王惯有的冷漠肃然。
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狼烟,模糊了我的眼,模糊的视线中,我看见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弓箭手,团团的,围住烨儿,箭矢如蝗虫,我惊悸大喊:“不,烨儿,不——”
意识模糊间,身子便是落入那般熟悉的怀抱内,耳畔传来那般熟悉但是又有些陌生的嗓音:“姑姑,烨儿在的,烨儿没事,烨儿很好——”
“姑姑,烨儿也会在你梦里么?”
“姑姑,别离开烨儿,烨儿也只有你。”
“……”
恍惚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混混沌沌的梦境,怎么也梦不完,幻影重生,光怪陆离。
不知过了多久的多久,我甚而不知,是醒着,还是继续梦着。
我只知,我真的看到了莫寻,是莫寻。
我还是在旧时伏波宫,一身蓝衫的莫寻,坐在我的榻边,只是一瞬不瞬的,看着我。而我的手,尚且被他厚实的手包裹住。
我梦幻的喃喃的问他:“莫寻,是你么?”
莫寻的眸内,便是闪过一抹疼惜笑意,点头对我道:“是的,是我。”
我看着他,紧紧的看着他,长久的沉默中,泪水便是倏然的,如决堤洪水,盈满双眸,滑落脸颊,湿了枕巾。
莫寻慌了,忙伏身来,问我:“这是怎么了?怎是哭了?是哪里疼么?哪里疼,来,快告诉我……”
泪流满面的我,反手回抱住莫寻的后背,那么紧,那么紧,仰起脸颊吻上他的唇,贴着他的唇,我问他:“莫寻,你是谁?”
莫寻的后背,在我的掌心下,有刹那僵硬。
瞬间后,是莫寻难得的主动的,回吻我。
当莫寻的舌尖,探入我的口中轻轻的扫过我的齿列,我被莫寻带动着,只觉那熟悉的酥麻感直冲脑髓,不禁更紧的搂住他。
我终究贪恋沉迷莫寻给予我的这一切温柔对待。我无法抗拒,亦是舍不得抗拒。一如,当下。明知,莫寻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回避我的疑问,却还是,忍不住的,便是沉沦沉迷。沉沦贪恋至不问今夕何夕,不问身在何处,不问周遭境遇。
只要有莫寻,只要莫寻还在我身边,那么,一切与我,便还是美好的。
可是,我不知,这是不是,另外一场梦,另外一场幻影。
我只是想着,纵然是梦,纵然能梦到如斯真实的梦,我亦是欢喜的。
我醒来了,不是身在江南千里寒冰潭,亦非身在伏波宫,睁眼扫视的空当,满鼻子的是檀香,满耳的是诵经声。我只愣了愣,待得睁眼细瞧,便是想起,这是当日承烨昏睡的相国寺偏院,而我,正平身躺在当日承烨昏睡的木榻上。
左右未见得一人侍侯于侧,待得我起身下榻,伸手推开木棂子窗,窗外秋光大好,空气甚是清爽,我满满的吸了口气,只觉神清气爽,精神分外的好。心里寻思着,这一趟昏睡,看来是有好些日子了,也不知身边事可否天翻地覆。
檀木桌上,尚且搁着那一****让小和尚搜罗来的两面小破镜子,我持着镜子,稍微理了理仪容,又盯着眉心凰记出神了半响。眼角余光里,对面的藏灰色土布幔子便是晃了晃,紧接着,进来一位与土布幔子同色儿的年轻持棍僧人,我正要问话,土布幔子又是晃了晃,只是我眨眼的功夫,一色儿的持棍僧人便是排排站的立在我檀木桌子外。五人一排,四排,整整凑了一个廿十。
我瞧他们一个个的神色警惕,内心大惑,堂堂天子脚下,京城之地,难不成,这廿十年轻僧人是要明目张胆劫持或是软禁我这帝姑?
正想着,便是听有兵戈嘈杂声,从窗外传来,愈来愈清晰,愈来愈近。
廿十僧人手中棍子便是齐齐一甩,气势甚是恢宏,我还未来得及赞叹一声,廿十僧人便是将我团团围在了中间,棍棒一致对外。
瞧这架势,哪里是软禁或劫持我,显然是护我来着。
土布幔子又是一晃,廿十持棍僧人严阵以待,我定睛一瞧,进来一位发须皆白恍若仙人的袈裟老僧,廿十持棍僧人瞧是自己人,也松了警戒,只听那先头第一个掀开土布幔子进来的年轻僧人恭声道:“寺内突来变故,惊扰神僧清修,甚是歉疚。”
老僧白眉一抬,眸光檀越,瞧向当中的我,我回以礼节一笑。老僧便是双手合十,和蔼笑道:“善哉善哉,贵人多劫,焉知非福。”
这话中“贵人”,可是说“我”?既是说“我”,这年轻僧人口中“寺庙突来变故”,岂非因我所起?
我盈然笑道:“多谢神僧吉言。”
神僧端摩我半响,半响后,直是点头,好似将我当做一物件来品评,而结论是,非常满意。
我已然能够听见兵戈打斗声中夹杂的人声,口口声声的,总归是让寺中和尚交出江南第一山庄夜氏后人来。那应答之人,正是与我有几面之缘的相国寺方丈,回道,佛门清静地,岂容尔等放肆胡为。
又是一阵打斗,檀香混杂了血腥气从敞开的窗外漂浮而来,而那血腥气是愈来愈浓烈。
我叹口气,道:“为本宫一人,枉送一众人命,实是不该。”看向老僧,“是劫是难,是福是祸,该来总归会来,让外面打斗都停了吧,本宫出去便是。”
神僧好似只等我这句话,我堪堪说完,神僧便是对那廿十持棍僧人道:“将贵人之言,一字不差去告知方丈师兄。”
那廿十持棍僧人稍有迟疑,神僧又道:“贵人这里,自有老衲护着,还有何不放心之处?”
那廿十持棍僧人便是欠了欠身子,鱼贯入外去。
人都散去,未几,窗外打斗声渐渐隐了去。
我歇了口气,看来,该是我出场之时了。
我抬步向外走,走过老僧身前时,老僧喊住我。
我停住步子,侧身回望老僧。
老僧只顿了顿,徐徐道:“贵人此番出去,当真是,是福是祸躲不过,可得想清楚了。”
是在考量我么?我笑了笑,拾步入外。
土布幔子晃了晃,我便是被老僧给提住。再待我回神,我已然身在暗道,情形像及了那一日走暗道回宫里。
我身边也只得一个老僧,在前头引路。
老僧见我不走了,便回头看我。
我道:“可是要回宫里?”
老僧点头,那檀越眸光只盯着我眉心处瞧,未曾移开视线。
老僧问我:“贵人不愿回宫?”
我笑,问他:“本宫想去何处,还由得了本宫么?”横竖是欺我不懂武,先是慕容凝,再是暗风,再后来是方为雄,现在又是这神僧,一个个的,都巴巴的,赶紧的,将我向宫里送。
神僧忽而收敛神色,道:“老衲只是受故人之托,贵人此生,惟常处深宫,方可保一世安宁。”
这话,怎是如斯耳熟?
我眉心一跳:“那故人,是先太皇太后?”我的姨母。
神僧点头,道:“她一生睿智,为皇室江山,可谓殚精竭虑。”
这一点,我亦是深信不疑。
“老衲知贵人非池中鱼,深宫大苑无法困住贵人的心。”神僧叹口气,“只因故人之托……”
还能说什么呢?横竖,现下也只得先且回宫去,再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