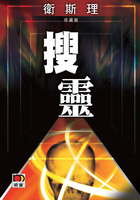据说奥立弗·吴从来不会给愚笨的人什么好脸色,而今晚他的脸色绝对和“好”沾不上边。今晚他的任务是评估哈佛的升等候选人。他审视着丹尼斯·高森档案里面的一篇文章,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像一尊埃及猫雕像。唯一移动的是厚重镜片后的深色眼睛,多年前的白内障手术迫使他戴上眼镜,镜片像玻璃可乐瓶底一样有一圈圈的波纹,使他看起来有点像猫头鹰,有种老是盯着人家看的感觉。他黑色光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上唇的髭须经过精心修剪,使他的面容更具特色。
吴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在社会学的犯罪学领域声誉卓著,尽管他从来不以“犯罪学家”自称。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犯罪学领域多半由精神病学家独领风骚,他们认为犯罪的原因在本质上是一种病态,吴和其他社会学家则强调文化和教育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
吴在犯罪学方面所受的学术训练走的是欧陆传统,他追随隆布罗索的学说,相信有一种犯罪者可以从生物或解剖学的特征中辨识出来。吴到美国之后接触了萨瑟兰(Edwin H.Sutherland)的著作,感觉就像保罗在大马士革城外受到了基督的感召一样。
萨瑟兰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犯罪学家。二十多年来,吴的著作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他追随萨瑟兰的脚步,发展自己的理论,阐述犯罪行为多面性的本质。除此之外,他还搜集了大量资料,焦点集中在犯罪行为的不同特质和方面。在吴的眼中,任何学者如果要把复杂的犯罪活动简化为单一原因,这种做法与其说值得商榷,不如说根本是愚不可及。
吴向后推开温莎椅,离开个人研究室,有目标地在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的灰色金属书架间穿梭。许多教授在自己家中都设置了宽敞甚至完善的工作室,但是吴和他们不一样,他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图书馆完成的。位于威廉·詹姆斯大楼的办公室,是他和学生及同事交流意见的场所,但他在那完全没法定下心来阅读。吴坚持认为,真正适合工作的地方,是位于图书馆深处的个人研究室。但吴偏爱图书馆的原因不仅于此,他深爱图书馆里的一切:陈旧的书香,身处洞穴般的寂静,与世隔绝的感觉。对于拥有吴这种性情的人而言,图书馆是个可以逃离外在世界喧嚣的避难所,同时也是储藏全世界知识的宝库。
十五分钟后,吴的搜寻行动结束。返回研究室的时候,他手上多了一册从书架上取下的书,颜色灰白,厚度中等。吴滑回座椅内,把书放在高森的档案旁边,档案最上面是吴在评估高森作品时所阅读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发觉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者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边沁,边沁在一百五十年前便写下了他对“罪”与“罚”的看法,他也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之父,以整体上是否能增进公众的幸福,来评断一切的法律与人类行为。依照边沁的观点,人类持续不断地在进行评估与判断。吴早就发现边沁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代表着如今早已过时、从单一面向描述人类本质的观点,这可以在课堂上作为范例。
在现代社会学暴露其限制之前,边沁对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广为接受,但在吴的社会学课堂上,学生们却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这种把人类视为“只会追求单一目标的计算器”的理论曾经盛极一时。所以吴的做法是直接引用边沁的原文,他发现这样有助于学生相信教授不是故意设计出一个假想敌,来和现代社会学做比较。
现在吴觉得最好为一月八日做好准备,带上证据证明一百五十年前就有人这么想,一百五十年后哈佛有个教授升等候选人竟然对人类本质有着同样的看法,而且还以这种早已过时的观点作为学术论证的基础。
跳过冗长的书名,吴快速地翻阅着内页,他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也知道在什么地方会找到。在第188页他找到了引文,开始在笔记上做记录:“……有谁不计算?人类都会计算,确实,有人算得比较差,有人算得比较精,但没有一个人不计算。”犯罪学家并不否认人会计算,吴之所以如此嫌恶高森的作品,是因为里面的中心思想是人类只会计算。
吴准备离开图书馆,把这篇让他看了就有气的论文放回高森的档案。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薪资差异与渎职行为》,文章不长,和一般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一样塞满了数字图表,记录着不同行业采购人员的薪资,这些人负责采购公司的进货。高森搜集了这些雇员的薪资数据,发现在拥有相同训练和教育背景的雇员中,如果公司的生意正在大幅扩张或者拥有较多流行性或季节性商品,付给采购人员的薪水大多高于较为稳定的产业。以实例来说就是,负责采购当季流行服装的采购人员,会比负责采购机床的人赚得多。
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解释或理论,围绕的主题是遏止渎职行为,并且宣称经过验证证实为真。在某些市场,采购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较难监控,例如负责采购手链或项链等现成商品的人员,雇主会基于理性的考虑付给雇员较高薪资,以确保雇员在面对特定服装厂商贿赂的诱惑时,会因为较高的薪资而依据雇主的最大利益行动,拒绝贿赂,不致买入较差的商品。而在变动较小的市场中,采购人员的渎职行为很容易被察觉,也就不需要以丰厚的薪资作为诱发员工诚实工作的报酬。依照高森的理论,不是因为诚实的员工有诚实的表现而获得更高的薪资,而是为了增加员工诚实的表现而提高薪资。就奥立弗·吴看来,这套理论十分荒谬。
吴把公文包放在他今天研究的高森和其他候选人的作品档案上,合上公文包,把研究要用的书排好,这些书他并不打算带走,然后离开了威德纳图书馆。每天傍晚七点,除非他另外打电话给车行,否则都会有辆出租车在哈佛广场等着载他回家,他的视力不允许他开车。
在准备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吴试着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只有成本和利益的世界,人们根据事物的价格而非价值行动——这正是丹尼斯·高森理论中的世界。
他走近图书馆前门的柜台。如果偷一本书带走的话呢?就他记忆所及,这个念头从来不曾出现在他的意识中。偷书的成本是什么?门口的防盗监视器可能会检测出他夹带了一本书,情况会很尴尬,但不至于太尴尬,因为他可以用心不在焉为自己开脱,服务人员也会欣然接受他的解释。不管怎么说,吴在威德纳图书馆进出了不下上百次,他被拦下来检查的机会还不到50%。但是还有良心的煎熬,他可能会因为犯罪而饱受折磨,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中,偷窃被认为是一项很严重的罪恶,他的价值观是属于老一辈那种的,如果违反了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他知道自己的悔恨绝不会只有一丁点而已。此外还有搬运厚重书册回家的成本,他并不习惯从事体力劳动。接着他又估算了收藏这本书,还要不时拿出来掸掸灰尘的成本。他陷入了苦思:成本计算到底何时才能结束?也许是在计算成本这件事的成本太昂贵的时候。
然后吴的思绪就转向了这道等式的另一端:偷书的利益是什么?似乎少得可怜。当然,可以获得书里面的知识,也许还有阅读的乐趣,但这些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利益,他可以从威德纳的藏书获得,而且并不麻烦,因为他如此勤于拜访这座他最喜爱的圣殿。他当然可以卖书换钱,但是一册盖着图书馆藏书印戳的书,在市场上是卖不到什么好价钱的,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利益。在他的决策计算中,成本显然高于利益,吴猜想高森会设定他不会偷书。
出了图书馆,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走下石阶,走进向晚时分寒冷的空气中。哈佛校本部步道上的积雪已经铲除,高高地堆在混凝土人行道两侧,吴沿着建筑物往南走向马萨诸塞州大道,过马路到对面哈佛广场约定等候车子的地方,出租车正在等着他。
“晚上好,吴博士。您今天晚上要直接回家吗?”
“是你吗,雷蒙?”吴问道,目光努力穿过厚厚的镜片,确认是常常送他回家的司机后,爬上老旧的雪佛兰后座,把公文包放在黑色塑料皮椅上。
“是的,我们直接回家吧。”他下达指令。
出租车沿着布雷托街向吴的住宅前进时,后方传来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干扰了吴的思绪。他听到前座的雷蒙一边暗自咒骂了一声,一边把车子往路边靠,好让超速的汽车通过。
逞勇斗狠的驾驶在大波士顿地区很常见,但他们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在十字路口或狭窄巷弄里卖弄惊险动作,而且就算以最宽松的标准来看,这辆超越出租车的轿车速度还是快得超乎寻常。
“那家伙是赶着参加自己的丧礼是吧?”轿车加速通过时,雷蒙说。
吴的思绪不受拘束地再度回到边沁,还有计算。边沁的信徒会主张,蓝色轿车之所以决定超速,是经过一番权衡:一端是错过约会造成的困扰,另一端是被警察逮到并且被判违法的概率,他可能会被罚款,而且如果因为超速导致伤亡,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高。两相比较之后,驾驶人决定超速而非遵守法定限速,因为净收益高于成本。吴领悟到,横冲直撞的驾驶表面看似不合理,但经过解释后却可以成为合理的行为,不过是成本利益计算的问题而已。确实,吴思索着,以高森的逻辑来看,整部刑法就是规范各种行为的价目表,就好像我们所有人、所有社会个体,面前都摊开着一本详尽的菜单:该不该并排停车?先看价格再做决定。只有在正常停车的不方便程度超过罚款金额的时候,才会并排停车。再者,除非被当场逮到才会被罚钱,而很可能不会被逮到。被逮到的概率有多大?这也要列入计算。
先前满腹牢骚的吴,现在渐渐褪去抱怨的外衣,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在这个游戏中获得乐趣。吴以戏耍的态度考虑菜单上的其他项目:谎报所得税的成本与利益,虚报学术会议旅行支出的成本与利益等。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闪过他脑海:谋杀呢?谋杀也是菜单上的一个选项吗?为什么不是?我该不该杀人?引领他走到今天卓越地位的是想要成功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智慧与持续不懈的努力。但一路走来也曾有跌落深渊的时候,而且他相信那并非出于自己的失误,而是他人的算计。
现在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并不是所有谋杀犯都会被抓。一方面,按照高森的说法,被抓的概率要按照适当的“折现”公式计算,而且就算被抓还有可能逃过判决。另一方面,要考虑的则是巨大的利益。
隐藏在沉重眼镜后方的眼睛半闭着,吴转开视线不再凝望车外交通。透过紧闭的出租车车窗,勉强可以听见远处每隔一刻钟便鸣响报时的钟声。他感到非常不安,他的思绪走上了一条意料之外的道路,这是他开始思考经济学的犯罪观时始料未及的。但不停地计算对自己有利的行为,是个太令人难以抗拒的游戏,大势已去,再也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他。在想象的世界中他突然看见他的死对头的脸,全世界他最憎恨的一个人,一连串计算急如星火地掠过他的脑海,然后又归于平静。在这个游戏中,吴已经找到了致命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