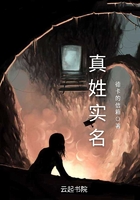方垆心刚要起身继续劈柴,听见农儒敏说:“那就可以理解你的看法了,据当年知情人在网络上的爆料,月月经历的那个惨啊,唉,没法说。”
“你知道,无论真假,说来听听。”方垆心突然饶有兴致。
农儒敏压低声音:“简单说,月月在他们公司做文秘,因为长得如此水灵漂亮,还没有过男人沾染。在一个晚上,刘广寸把她借口留在办公室,后来就被轮了。妈的,我去他妈的,但凡有机会,我也要让这几个人渣血债血偿。”
丝丝脸部抽筋一般,手紧紧捏住一根木棍:“儒敏,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罗波。”
“据当时爆料说有,但很快这个新闻就被压下去了,从网络上彻底消失,你现在上网搜索,完全没有痕迹一样。”
“你不是门门精通吗?儒敏,等我们回到城市里,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个爆料者挖出来,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你放心,一旦晓晓他们知道这个事,也会这样要求,我们都会出手一起干。”丝丝看着天空最后的颜色:“人可以不要命,但必须要脸,死活都要。”
方垆心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义愤填膺,深思着说:“我的一个长辈说:人可以活在争斗中,男儿总得英雄一回,无所谓荒唐不荒唐。只要不活在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谎言里,不要一直浸泡在污渍和恶臭的溃烂中。当能在有生之年真诚直面天地时,一切都会如云烟消散。”
在农儒敏和丝丝听来,方垆心突然来这几句,与月月的事情毫不相干,认为他又神经病了,丝丝说:“什么意思,这事就算啦?如云烟消散?”
方垆心提起斧头:“不是,我可以真诚直面天地,但做不到一切如云烟消散,我要先做到她前面的话:人可以活在争斗中,男儿总得英雄一回,无所谓荒唐不荒唐。”
说完,方垆心提着斧头,走到院坝边,狠狠地把一根老树桩劈开,那气势,犹如那个久远的传说:沉香力劈华山。
丝丝看着方垆心,淡淡地笑着,自言自语道:“但愿你再英雄一回,刀山火海,我也陪你。”
农儒敏刚要问,丝丝摆摆手指头:“记住,我丝丝姐是有规矩的。儒敏,唉,其实当年还是没人给月月出头,她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可能往祖上推八代,也还是最底层挣扎的人,没有公道啊!”
“其实,人还是自私的。丝丝姐,你说得对,如果当初月月是我们的亲人,比如,我们的妹妹,拼了命也不可能就硬生生把如此屈辱吞了。我之所以辞工,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活着,就是觉得恶心,没法和恶心并肩,更何况要为恶心服务,实在干不了啊!”
感叹着,唏嘘着,起身去捡木柴,农儒敏面色沮丧,似乎没法高兴得起来了。
丝丝马后炮似的惊叹道:“懂了,懂了,家里有电,以前应该是有电视,有手机的,后来他们全都舍弃了,是因为屈辱和无奈,如你儒敏一样,恶心了,没法再恶心一点点。”她的神情像一个神经病。
南方的春天来得早,院坝外的梨树已经披霜戴雪,枝头上白色的梨花,犹如那雪域上的圣洁飘落在温暖如春的南国,不曾融化,反而争奇斗艳。
明月懒懒散散地爬上苍穹,银色的皎洁之光跌落在梨花上,在这方近乎与世隔绝的家园,夜如此的静怡,美丽如诗。
夜,正如晏殊那句经典诗:梨花院落溶溶月。
桌凳搬在院坝里,五人围坐一起,如多年老友一般,其乐融融。
她的父亲话不多,抽水烟管不喝酒。他把家里唯一的桂圆酒拿出来,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尽兴。那些就已经尘封多年,不喝酒家里却有酒,那是为过年过节等等不寻常的日子,用来招待客人的。
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客人了,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渐渐没了客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也觉得没必要弄清楚。
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在深山,但他穷。
他是一个农民,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农民,而没得选择的成为了一个农民,这个问题他想过。因为他爸就是一个农民,据他爸说,他爸的爸也是一个农民,他也是一个农民,这就没什么好怨天尤人的了。
农民也有日子过得好的,但他的日子并不好,为何是他的日子不好,这也似乎没法计较。总有人日子不好,不是他,就会是另一个他,那么,是他也正常。
他似乎也知道自己为何穷,知道自己家为何没有了客人。在他爸给他娶婆娘那时,他们家的日子还挺好的,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
有婆娘,就该生孩子,这似乎应该是天理。不知道是不是天理难容他,他有婆娘了,但他婆娘一直没给他生孩子。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婆娘肚子不见起色,地在并且没问题,种也播了,播种还挺勤,但就是没收成,连个芽包都没冒。
五年、六年过去了,他婆娘的肚子还没反应,从前开他玩笑的人,演变成背地里咒骂他。说他家风水不好,生出处;说他祖上曾经是土匪,伤了德,到他这一辈,该绝后了;说他家的屋基以前是坟地,埋的都是饿死的孤儿五保户,住那地方,不可能怀得上……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说他其实不是男人,所以他婆娘的肚子没反应;说他的婆娘其实是石女,别说生孩子,只是看着像女人。
因为那些他认为胡说八道的话,他和村里很多人打过架,不只和男人打过,也和妇女打过,因为说那些话的很多都是妇女,不得不打。
严重的几次还被拘留过,赔过钱。严重的次数和赔钱的次数几乎是差不多的,次数一多,家里就更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