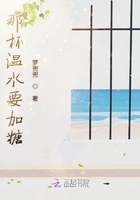新工作我很快就适应了,但要赚钱一定要沉住气,不认识人,不打好关系,永远也只是一时浪潮,要想细水长流不能急于求成。我三天时间就基本上摸透了我那班组里每个人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这让我放心很多,因为对于我来说,他们构不成什么威胁,至于这家诡异的酒吧的上层,一直是我一探究竟的地方,尽管我认为那里没有一个正常人,反正那个许经理就是,还有他周围的人,甚至这间酒吧,就好像一座藏着神秘宝藏的城堡,我已经探进去,只要找到宝藏,我马上就抽身离开这里,不能久留。
酒吧的布局也很诡异,一楼简直就是个中小型的DJ舞厅,每晚都有数不尽的人在这里狂欢,音乐的劲爆刺激着每一个人紧绷的神经,跟着音乐和酒水,在烟雾缭绕,人影重重的舞台上释放灵魂。
二楼我只去过一次,灯光暗淡,音乐蛊惑销魂,墙上有很多儿童不宜的壁画,那里有很多房间,只有一条走廊,左转右拐,像一条路的迷宫,迷宫的尽头,就是许经理的办公室,当然,他已经足够神秘了。
我们的班长主管我们,她是一个不言苟笑的女人,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她同样有许经理那样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我甚至怀疑,她到底是不是许经理的女儿。在她面前我都不会说话,哪怕她过来吩咐换班和通知的时候,我顶多“嗯。”一声,对于这些无法给我带来经济利益的人,我一般选择不理不睬,但不是说我高傲,毕竟我也只是个底层员工,还是要学会察言观色,夹着尾巴做人。很多时候还是迫不得已迎着笑脸点头哈腰。
刚来工作肯定免不了受“欺负”,这就是职场规则,新人肯定要干多点活儿,特别是脏活累活,所以,那一个九月份,我经常免费客串清洁工,打扫肮脏恶臭的厕所。跟我之前在清远的待遇差不多,非要比个较的话,那就是在清远怎么说还是自己“地盘”,在广州,发脾气到厕所去。在清远打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在广州打工已经处处为了生计,就好像一个孩子长大了,必须要去承受这一切一样。
有时候在酒吧里干活干得累了,我会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不管脸上的污秽,不管手上的脏物,我只看见我自己,曾经的自己好像被锁在了镜子里,曾经幻想给自己的梦想和美好,已经失控地走到了我的对立面,随着时间轴的不断纵长,我渐渐地看不见它的踪影。如今的我,无可奈何地走在现实的轨迹上,盼望着归宿与远方。
我没有跟李心说过这些,纵使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很少,更多的时候是在视频通话,她只有在宿舍趁着宿友都睡觉的时候才偷偷地跟我通电话,视频中的她和平时一样,说话有些逗,喜欢分享她一天下来的日常,比如谁谁谁今天睡觉又被老师发现了,被叫了起来。比如谁谁谁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放了一个屁,全班都听见了,憋笑憋了一节课,可把她憋坏了。比如有个女生为了发育,暑假都时候狂吃木瓜,结果真的逆袭了!
李心说的这些事每一件都能描绘的生动形象,龙飞凤舞。我常常视频通话的时候注视着她,好像怎么也看不够,有时候看得入神了,忘了回答她的话。她看着我已经看入神了,又咯咯笑起来。
“看够没有喔,你好傻啊哈哈哈,傻到一种叫可爱的程度。”
我吃吃地笑着,说:“一星期才能在你身边一次,现在还不趁机多看一会儿,待会儿就没得看了。”
“好嘛。”
“时候不早了,快睡觉吧,你明天还得上学。”
“不,还早呢。你快说说今天你工作怎么样了?我要听。”
我刚刚想说,同事又叫我了,5号桌又有醉汉闹事,需要我去清理现场(扫垃圾),我顾不上和李心说,便说:“我给你留言,今晚就这样吧。”然后匆匆挂了视频,大步流星地赶到现场。
好家伙!把杯子砸得满地都是玻璃碎,跟个罗汉似的倒在沙发上,袒胸露乳,打着饱嗝。
我去拿扫把和垃圾铲,谁知道那死胖子喝醉了一脚踢我,我反应不及,摔倒在地上,手掌撑在那玻璃碎上,钻心的疼痛瞬间蔓延全身,我看着鲜血直流的手掌,疼的说不出话。同事见到,马上过来询问情况,看了一下我的手,给了我一包纸巾让我到洗手间清理,剩下的他来搞定。
我拿着那包纸巾,冲到卫生间,猛的打开水龙头,颤抖地将满是玻璃碎的手伸过去。冰凉的水就好像刺激剂一样,生疼生疼的,水盆里的水很快就染红了。我另一只手死死抓着洗手盆边沿,青筋都露出来了。那些大块的玻璃碎被冲刷掉,剩下些细小的,我拿着指甲仔细地抠,一点一点地抠,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此时手正流着血,脸红红的,眼泪浸湿了睫毛,连工作的衣服都染上了血迹。真是狼狈,真是卑微。
我拿着那包纸巾止了止血,擦干眼泪,再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看着镜子说。
我回到吧台,同事j看见我,关切地问:“没事吧?”
“小事情不怕。”
他继续擦着酒杯,说:“是这样的啦,我超想上早班,早班轻松多了。人少,是非少。都是打工的,凡事都要忍啊。”
我点点头,吃力地拿起酒杯擦起来,刚刚被玻璃扎痛的手,现在好像使不起劲一样,连杯子都握不住,要借用毛巾才能继续工作。
“你这要消毒啦,不然发炎就难搞了。”j继续跟我搭话。
“下班在消吧,现在上班时间。”我淡淡地说。
j白了我一眼,说:“就那几千块钱工作,那么拼干嘛?而且你现在还是实习酒保,说白了就是不正式的,工资少,提成少,那么拼,为了啥?”
我没说话,继续专心致志的擦着酒杯,j见状也不聊了,丢下一句:“怪人。”就到别处去干活了。
“hello。”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抬头一看,徐欣芽!
“怎么?见到我很意外?”
“你怎么在这?又来买醉?来,买我的酒,帮我生意。”
徐欣芽摆摆手,点了一根烟,说:“员工与员工之间不能做生意。”
我惊了!“什么?你是这里的员工?什么时候的事情?”
徐欣芽很平静地说:“几天前就是了。”
“你来这里工作干嘛?”我有些意外,便问。
“生活啊,能干嘛?不挣钱你养我?”徐欣芽白了我一眼。
“舞女?”
“嗯。”
“多少钱?”
“3000。有提成。”
“提成多少?”
“跟你有关系么?你就一酒保。”徐欣芽轻蔑地说。
我微微一笑,说:“看来舞女就是不一样啊,都是打工的,你的确要辛苦些。”
徐欣芽眼神一定,说:“我们合作怎么样?”
“怎么合作?”我好奇地问。
徐欣芽凑过来,说:“我给你拉客源,你把你一部分酒给我,我帮你卖出去,但是你的提成我们四六分。你想想,多一个人帮你推销,你横竖都已经赚了。”
徐欣芽眯着眼睛看着我,一副吃定我的样子。
我微微一笑,说:“如果条件就是这么简单,你根本不会来找我。完全可以找其他人。”
“不,你不会跟我讨价还价,我了解你。”徐欣芽嘴角上扬。
“我考虑考虑。”
“一个月之内,我能让你做班长。”徐欣芽凑近我,嘴都要凑近我的嘴。“怎么样,我说到做到。”
“成交。”
我最终选择了钱,如果酒卖的越多,业绩越好,提成少了点也可以补回去,而且有了稳定的客源,我不愁没柴烧。生存法则,简单粗暴但又充满谋略,说到底都是利益。
酒吧准备打烊的时候,我从员工室找到了一瓶高度酒精,那灼烧在手心的感觉,再一次让我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一切处理完了之后,我再一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左手指着自己的左太阳穴,像开枪那样崩了一下。
“die young。”
右手缠着绷带,摸着镜子中自己的“脸”。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