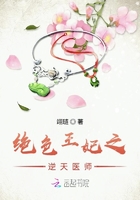越子倾一抬脚,就将卞容仇踹下床去,脸上显出因牵动后背伤口嘶疼的表情。
卞容仇乐道,“这都不承认自己是悍妇。”
越子倾这次学乖了,先单手扶腰,另一只手才去抓床头的麻布谷枕砸向卞容仇。
卞容仇稳稳接住,手舞足蹈,一副任你百般攻击,我亦岿然不倒的神气活现模样。
越子倾甩了个白眼,“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去给我把大娘请来。”
仅左脚站地的卞容仇听到这话,又看着越子倾手里握着的小玉瓶,一个重心不稳,差点随着抓着谷枕摆到左边的双手一起栽到地上。
亏得右脚力挽狂澜,率先着地,避免了惨剧发生。
卞容仇带笑凑到床前,去端杌子上的药碗。
经过刚刚羽林卫一番闹腾,药早凉透。
尤其是想到这碗药被那仗着是官,只会摆脸色的人,端过闻过,是怎么都不能再喝了。
“别人给的药哪能乱用,这样,我去看看炉上还有没有药,给你热了端过来。”
越子倾呵笑两声,“我们认识也就一天,我还怕你毒死我呢!”
“俗气,江湖儿女的情谊,怎能用结交的时间长短衡量。”
“那用什么。”
“缘分啊!你看我俩多投缘,我还是你的救命恩公。”
越子倾又是一阵假笑,而后打住,“那还请恩公不要耽误小女子伤势,速去请大娘吧!”
也不知昨夜是谁用掉了他整瓶止血散,还将他金创药连瓶摔到地上洒了。
他的这片好心,终是错付了。
卞容仇将还拿在手里的谷枕随手一扔,正好落到了床头正中间。
“到时候不管用,可别求小爷我给你买药。”
那银子还是他大哥交给他先行去丰城置办宅院的呢。
不想这跑趟明几山,什么没查到,银子倒是散出去上百两。
都说秦楼女子惯会吸人血,看来所传不假。
卞容仇看着床上那个不知啥时候又枕上麻布谷枕趴下的女子,还真的很想看看,那张皱巴男子人皮面具下,是怎样一张脸。
看那眸子,一定是极漂亮的一张脸吧!
瞎想什么呢?
卞容仇反手就抽了自己一嘴巴子。
做人哪能这么肤浅。
这人,也就比普通人看着单纯,有趣好玩几分。
是个可以被拿来逗趣,打发时间的“兄弟”。
虽然“兄弟”让他一度从大侠、恩公、卞大哥,沦为跑腿。
可男子对‘兄弟’,自是两肋插刀,哪能计较这么多。
看卞容仇一会肃然,一会灿然,对着自己的脸一会抽,又一会摸,墨迹了半天,才摇头晃脑开门出去。
越子倾觉得这人多半是病了,还病得不轻。
不过这些都不是她该考虑的事情。
她要考虑的是查细作,查杀手。
这里也并非久留之地,要是白彻察觉到不对,杀个回马枪就糟了。
越子倾打定主意,无论自己明日状态好坏,都要尽快赶回丰城。
门口传来响动,越子倾便看到大娘端着个针线笸箩走了进来。
笸箩里只放了把崭新的剪子,和一些白净细布条。
都是大娘赶夜去城里卖货买货时,卞容仇追了她三四里地,连同蜜饯一起托她买回来的。
大娘堆着笑,已坐到床边,“青舞娘子好些了吗?”
一听大娘如此问,越子倾就有点慎得慌,总感觉这大娘给她上药时格外热情。
“好多了,麻烦大娘了。”
越子倾说着,将手里的小玉瓶递了出来,“大娘将这瓶里的药粉均匀撒在伤口处便可。”
大娘接过小玉瓶,“青舞娘子客气了,出门在外,谁还不会遇到点难处。”
说话间,大娘已掀起了越子倾腰上的粗布襦子,那如白玉白皙柔滑肌肤就露了出来,胜皎月生辉。
还有那小腰,连带着让缠在那腰上后背的淡黄麻布,看着都精致华美起来。
大娘看那淡黄麻布上干干净净,一点血迹没有,高兴道,“到底是青舞娘子年轻,不过一日,这伤口就大好了。”
昨夜越子倾虽未避开飞向她的那把大刀,可她反应还算迅捷,是以伤口虽有些长,但并不算深。
大娘以为越子倾伤情严重,更多是因昨夜看着衣背的血。
还有替越子倾处理伤口时,她发出的惨叫声。
想到刚进来时,卞容仇再三恳请她下手一定要轻,大娘就觉得不好意思。
“青舞娘子,我轻一点,你要觉得痛,就告诉我一声。”
是想着就疼啊!
越子倾眉目紧皱,将那原本就不甚贴合她脸的人皮面具,挤拉的更违和了。
“青舞娘子。”见越子倾未有回应,大娘又叫了一声。
越子倾才知自己紧张的忘了反应,点了点头,“谢大娘。”
大娘这包扎纯属现学现卖,不过平日做针线,剪子使唤的倒利索。
左右一剪,越子倾微一抬身,大娘就将原先缠的那几层麻布都收拾了。
一道肉红的伤口在本白皙光洁的后背上,尤为触目。
大娘忍不住叹道,“可惜了,这么嫩的皮肤上,怕是要留疤了。”
“留疤。”越子倾喊了出来,“会留疤。”
大娘目露疑光,平日里磕着划着留个疤,再平常不过。
这么大的伤口,不留疤才奇怪吧!
“估摸是会留疤的,不过青舞娘子底子好,愈合的好,看着不显也不一定。”
越子倾欲哭无泪,满脑子只要想到会留疤,就似噩梦般。
大娘撇见越子倾那副遗憾样,多少明白了什么。
就她这男子的粗犷长相,要留住相公,多半是靠的这副身子吧。
这样一想,大娘突然有点理解越子倾过激的反应了。
“啊!”一声娇喊,将大娘拉了回来。
原是越子倾忍不住上药的刺痛感,发出的细叫声。
不得不承认,就这叫疼声,她一个妇人听了,都心疼难受啊!
“青舞娘子忍着点,我再轻些,很快就好了。”
越子倾紧紧捏着谷枕,似能听到里面的沙沙声,转移了些许注意力。
大娘见越子倾终于安静了些,手上才放松。
等上完药,让越子倾坐起缠细布条时,大娘才发现越子倾背上,还有那同样白净的脖颈上,都渗出了细汗。
昨日是她赶时间,没留意到这些吗?
还有?
“有这么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