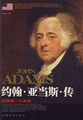?嘉靖四十年的秋冬,京师干旱异常,自入秋以来,始终未曾降下雨雪。三伏天刚过,一场大火,一连烧毁了皇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举朝惊恐,圣上连颁两道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但这过失无非是说自己敬天法祖不够虔诚,对老百姓爱护不够,对待国务多有旷废云云。在臣民心目中,真正属于当今圣上最大的过失,就是隐身西苑,崇道修玄,高深莫测,操纵朝政,忽功忽罪,专喜逢迎、堵塞言路,信任屑小、是非不明。圣上对臣僚的这些抱怨,不是不知道,但他的罪己诏一概掩过,只字不提。而就在罪己诏颁发的同时,圣上又命重修三大殿,务必早日完竣。
遥想成祖当年,迁都北京,三大殿甫修成仅仅半年,也曾被雷电击中焚毁,成祖念及工程浩大,始终未诏重修,历经仁宗、宣宗,直到英宗时,才得以重建。方今国库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久矣,却要甫毁即修,实是勉为其难。严嵩挖空心思,只得想出一个加征“木工费”的名目,向各省摊派。好不容易凑出了重修三大殿的银两,还没有过四个月,西苑又烧起了大火,把圣上居住的永寿宫,顷刻间化为灰烬。
当天夜里,徐阶把我召到家里,紧急商议对策。
我隐隐感到,政局转折之机,就在眼前了。
“目前圣上暂时安置在玉熙殿居住,玉熙殿狭小阴暗,圣上一走进殿门,即眉头紧皱,满脸不悦;明日,他一定会垂询办法,该如何应对,老夫还拿不定主意。”徐阶白天在西苑指挥善后,一脸的疲倦,说话的底气已明显不足。
“国子监里监生们议论纷纷,都说大火烧得好,正可借此机会,劝圣上返回大内。圣上以一国之君,九五之尊,不住皇宫大内,本就不合体统,作臣子的,不能在皇宫朝见圣上,列班议政,朝野早就怨声载道了。”我把听来的传闻加上自己的想法,阖盘说了出来。
“话是不错,”徐阶道,“不能把圣上劝回宫中,嘉靖一朝的臣子,都该感到羞愧。劝圣上返宫,是人心所向,洽舆情,顺常理,如此,既可节省财用,又可恢复朝仪,还可赢得舆论,一举三得。”
徐阶虽然如是说,可从他的语气和表情来看,似乎又不愿这样做。须臾,我已猜透了徐阶的心思,于是道:“以圣上的性格,舆情也罢、财用也罢,是不大能左右他的想法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圣上的心机。”
“叔大此言极是,”徐阶接言道,“圣上内心是绝对不愿意返宫的。若建白圣上返宫,必逆圣意。若说圣上此时的心思,那就是尽快重建永寿宫。然则,圣上不会直接说出来,他自己也明白若不返宫,情理上说不过去;况重建三大殿,国库已经不堪重负,再重修永寿宫,无疑雪上加霜,圣上不会说出口,他等待的是有人替他说出来。替圣上说出这个愿景的人,在圣上眼里,必是最大的忠臣。但在朝野舆论那里,就不啻是专以迎合为能事的佞臣了。”
我这才明白徐阶的苦心。其实他一切都了然,但他在权衡利弊,又忍受着良心的拷问。那么,他冀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是道义上的支持,还是谋略上的臻备?
在我的心目中,道义云云,大可忽略不计。置身官场,唯有权力才是真实的。没有权力,道义苍白无力,毫无价值。而眼下,要获得权力,就不能不迎合高高在上的皇帝,哪怕背负道义的谴责、良心的拷问。所以,我断然道:“以学生愚见,当提出建言,尽速重修永寿宫。”
徐阶看着我,似乎在说,说下去,讲点理由出来。
我稍微梳理了下思绪,说:“诚然,如此,难免会遭到非议,也难免会有任智数、用权谋之嫌疑,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能获得圣上的充分信任,推倒权奸,廓清朝纲,想来后人是能够谅解的。学生近来常常想,狄仁杰完唐全躯,若不任智数、施权谋,恐完唐不成,己躯已灭。后世论者,只颂狄公完唐之伟功,谁还复论狄公当年智数权谋之当用否?是故,学生以为,能获圣心者胜!至于不洽舆情、有悖人心,大可不必瞻前顾后,清者自清,何恤人言?”
徐阶点了点头,从他的神情看,他已经作出了选择。
本来,我和徐阶还隐隐有些担心,以严嵩一贯做派,迎合圣上的事,他是不甘人后的,一旦严嵩抢先提出重建永寿宫的建言,那么圣上对严嵩一定心存感激,旧情新爱,恐怕君臣关系,又会恢复到从前的融洽。
可是,严嵩这一次却充当了舆情的代言人。或许是他没有来得及和严世蕃研议,也许是他想以此赢得人心,也可能是他已经感到心力交瘁,不想大兴土木了?总之,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言。
这天,圣上把严嵩和徐阶召到玉熙宫,郁郁不乐地说:“这玉熙宫狭小阴暗,实非久留之地,你们研议个办法出来吧。”
“陛下,”严嵩立即答对,似乎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臣请陛下搬回大内,陛下不愿住乾清宫,离宫是一个好的住处,宽畅明亮,幽静无比,甚适宜陛下安居。”
严嵩说到大内,特别是乾清宫,这一定会触动圣上无限的伤感。十九年前,也是十一月底,一个寒冷的冬夜,当圣上夜宿曹端妃宫中的时候,宫婢杨金英竟失去理智,趁当今皇帝熟睡之机,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欲置其于死地。就在圣上即将断气的当儿,幸亏方皇后及时赶到,才救活了圣上一命。圣上被紧急抬到御榻诊治,就在这个工夫,方皇后传出懿旨,把杨金英和曹端妃一并处死了。曹端妃是圣上的最爱,圣上知道,曹端妃是冤枉的,可方皇后连申辩的机会也不给她,就把她处死了。但圣上又怎么能责怪救命的方皇后呢?他只能沉默了,把一腔的怨怒怜情,永远存于心底。从此,这乾清宫对圣上来说,就是梦魇,是血腥的回忆。严嵩劝圣上回大内,也不敢说出回乾清宫的话。所以,他提出要圣上搬去离宫。
严嵩的话音未落,圣上的脸色,当即就阴沉了下来,一向不动声色的徐阶,也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严嵩一再强调幽静宽敞,徐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严嵩的话。
这离宫确实幽静宽敞!可是,皇帝的居处,岂是一个幽静宽敞就可以的吗?要知道,这离宫是英宗皇帝被幽禁的地方啊!当年英宗误听太监王振之言,亲征鞑虏,竟被鞑虏俘获,英宗之弟代宗随即登基称帝,在位九年,后来鞑虏把英宗皇帝送回,代宗并不把皇位还于英宗,而以“太上皇”尊之,特意在大内修造了离宫,把英宗安置于此,说是静养,实为幽禁。英宗在这里度过了许多黯淡岁月。当今圣上在位已经四十多年了,作为一个皇帝,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很老了,但越是年老,对权力的留恋就越发强烈,对“太上皇”这些字眼,不能不格外敏感。所以,听了严嵩的话,圣上脸色大变,微闭双目,不发一语。
“陛下!”徐阶低声叫了一句,等待着圣上的反应。
圣上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徐阶,你是何意啊?也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