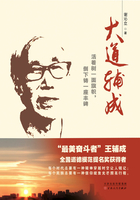1
嘉靖三十二年秋降下的第一场雪,飘如鹅毛,堪称瑞雪。这一天,是休沐的日子。但是,我猜想,严嵩一定要给圣上上贺表的,于是当即动手拟稿,并亲自送到严府,请严嵩过目。
“国常泰,年屡丰,玄机默运;外威严,内顺治,神武丕扬……”
严嵩低声吟诵着我为他代拟的《贺瑞雪表》,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颇是兴奋地说了声:“甚好!”便吩咐书办火速送往西苑。
我陪着笑脸,内心却不停地诅咒自己。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吗?天降瑞雪,表明当今皇帝修玄之效,足以使国泰民安。这岂不是荒唐透顶的混话吗?但一个最痛恨修玄的人,居然能够以华丽的辞藻、动听的话语,颂扬修玄;一个在自己心目中早已是昏君、暴君代表的人,却被自己说成外威严,内顺治,神武丕扬!
自从那年低眉俯首到严府呈上《贺少师严阁老七十寿》,表白愿捉刀代笔之后,凡是严嵩要上贺表,就由我暗中捉刀。贺喜雨、贺瑞雪、贺祥瑞、贺节日、贺圣诞等等。不就是一篇应酬文字吗?这样一想,开始时的愤懑情绪竟一扫而光,把手段看成了目的,于是便陶醉在自我欣赏中,一切就变得轻松了。
“元翁,您老人家虽是精制青词之大家,然则毕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撰写;况且元翁日理万机,军国要务都要元翁处理,精力毕竟有限,近来学生对青词颇有兴趣,故学生愿为元翁代拟词稿,不知元翁是否应允?”既然要出卖,索性就拿出最好的货色吧!我断定这是严嵩最需要的。趁严嵩高兴,便不失时机地向他表达这个愿望。
“喔?叔大是说写青词吗?”严嵩仿佛没有听清楚,一手抚耳,侧过脸来问。
“学生是说,为元翁代拟青词。”我郑重地说。
“喔,甚好!甚好!”严嵩欣然一笑,“嘉靖朝,写青词,乃忠君之举,爱国之证。以老夫看来,当今太平盛世,贤能才俊也不乏其人,然朝廷所重者,是德才兼备,而是否有德之鉴证,莫过于青词。”
听完严嵩这番话,我口中连连称是,内心却充满鄙夷。不过,更为自己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感到庆幸。
曾几何时,仇鸾倒台和徐阶入阁,一度引起京城种种猜测,似乎预示着严嵩父子的末日。然而,仅仅过了四个多月,情势却急转直下。忽然间,京城道路传闻,仇鸾是因为得罪了严嵩才被治罪的;而徐阶入阁,是严嵩极力举荐的结果;又说,徐阶以往的忠谨皆是为了向上爬,一旦入阁拜相,就原形毕露,令圣上大有徐阶“非无才,惟二心”之慨。
传闻中还有具体的例证:道士占卜说,需在邯郸建吕仙祠,方可保今上长生不老,工部奉诏修建,即将完工时,严嵩推荐徐阶前去主持,徐阶竟以要改议袱庙礼不便脱身为由,请求缓期。所谓改议袱庙礼,就是为了把圣上本不曾当过皇帝的父亲列入太庙祭祀,重新改定祭祀列祖列宗的礼仪,此事本出自圣意,徐阶以此为由推托不去邯郸,圣上也只好允准。徐阶不愿意去邯郸的苦心,外人不难理解:他甫入内阁,朝野视为正直有为之士,寄望其能多少匡正今上崇道修玄的乖张偏执之举,若去主持吕仙祠祈福斋醮仪式,则其声誉必受损;若不去,圣上必疑之。所以只能采取拖延之策。延宕多日,徐阶也不再提及去邯郸之事,圣上便改派道士陶仲文代为主持。
还有,储君之事是当今圣上的隐痛,多年来,他讳莫如深,不容臣下置喙。可是,徐阶却以为,储位一天不定,则窥测觊觎之心,一日不能杜绝;储君早立,国本早固,此乃大是大非,容不得半点含糊,于是三番五次在圣上面前为裕王争储位,惹得圣上大怒。徐阶的这些表现,在圣上的心目中,是否正好验证了徐阶“非无才,惟二心”之说呢?圣心所思,我辈固然无从知之,然则从徐阶闭门不出、专心于精制青词就可以看出,他失去了昨日的风光,处境微妙。正旦节我去给徐阶拜年,他竟发出了“风尘何扰扰,世途险且倾”的感慨。
还有那个特立独行、不买严嵩账的王世贞,虽然以文坛领袖自居,名满天下,可是,突然之间,就接到了一道任命,到山东任青州兵备副使。他不得不带着满腹的委屈,恋恋不舍地离开京城,去当那个他自己根本就看不上的官。王世贞离京前,在京的同年前去为他送行,我亲眼看到了王世贞的忿懑与无奈。“治青齐兵,其意,乃困吾以所不习故也!”临行前,王世贞仰天长叹说。我当时就暗忖,当国者的这一手,颇是高明,有朝一日得以执掌政柄,倒是可以鉴之。但是,时下,我想的更多的是,王世贞自恃名高,坚不攀附,后果已然显现。我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精制青词又如何?为严嵩代拟青词,对我个人来说,正意味着取得了权势者的青睐……
果然,严嵩听了我郑重的表白,抚掌大笑,眼睛里流露出赏识和满意的光芒。
“走,老夫请叔大观赏雪中莲花!”严嵩兴奋地说。
侍从迅即把貂皮大氅、暖耳等一副行头,替严嵩穿戴完毕。
厚厚的积雪上,落满了新吹下的银杏树叶,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灿然。我紧随严嵩身后,快步来到后花园。尽管已是深秋,但在严府规模宏大的花园里,莲花绽放,翠竹簇簇,更有少见的芝兰散发阵阵芳香。我并无心观赏,默默地想着心事。
“叔大,今日可不能光赏花,不赋诗噢!”严嵩边走边品评赏析,在一簇竹子旁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说,“就请叔大以竹、莲、芝为题,赋诗一首,何如?”说着,严嵩带我走进挂着“三瑞亭”匾额的亭子,里面早已备好了笔墨纸砚。
喝茶的功夫,我已经打好了腹稿,放下茶杯,我便提笔写下“三瑞赋”三个大字。
写下标题,我顿了顿,说:“松竹梅有岁寒三友之称,然则‘三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傲雪之莲、芝,学生以往却未曾一睹,今蒙元翁谬爱,学生得以大快目颐,真是三生有幸矣。学生以为,瑞竹、瑞莲、瑞芝,堪称三瑞。学生即以《三瑞赋》为题,班门弄斧,在元翁面前献丑。”说着,便埋头写了起来:
扶植原因造化功,
爱护似有持神明。
君不见,
秋风江畔众芳萎,
惟有此种方崴蕤。
……
“叔大立马成篇,不愧才俊!才俊啊!”严嵩连声夸奖,“来人,把张大人墨宝精裱后,悬挂于三瑞亭,以供赏析。”
严年闻声前来,正要接过诗稿,我忙阻止:“元翁,万万不可!学生涂鸦之作,岂不有污宝亭?元翁当今词坛泰斗,雅苑之中,古之大家占其一角尚属般配,今人谁敢僭越?遑论无名小卒如居正者流?”我说了一大堆理由,只是想阻止严嵩把我的诗稿挂出来。真是挂在亭中,那么我张居正私下讨好严嵩之事就会尽人皆知。
“喔,也罢,”严嵩颇是遗憾地说,“叔大过谦了,不过此稿要妥善保存,将来出一部咏苑的集子,务必要收进去。”
严嵩亲自把盏,为我续上一杯茶。我作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连连表示“不敢当”,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叔大所拟贺表祝词,清新大气,文采飞扬,圣上甚满意。叔大能为老夫分忧任劳,老夫甚慰。”严嵩洒脱地说,“况《嘉靖疏议》之刊,皆叔大之功,老夫自当礼遇。”
“元翁过奖,学生何功之有,实在是元翁为国贡献良多,理应刻刊。”我忙谦恭地说,但心里暗暗有些得意。
前不久,吏部郎中魏学曾弹劾严嵩,就在严嵩请辞在家之际,我前去看他,对他说:“学生近来屡屡听到道路传闻,对元翁说三道四,颇是不恭,学生甚感不平。其实元翁辅佐当今圣上,可谓竭诚尽忠,鞠躬尽瘁,只是坊间不明就里,故而以讹传讹。学生陋见,不如将元翁当国以来所进揭帖密札中选取可公诸于世者加以刻刊,就叫《嘉靖疏议》,以明真相而正视听,不知元翁以为妥否。”
国朝之制,阁臣除了公本上奏外,还常常就军国大事,提出个人的建言,不经正式的公文传递渠道,密奏上达,供皇帝参酌。因其是非正式公文,往往不拘形式,秉笔直书,其间不乏真知灼见。我的谋议是,外界诟病严阁老一意媚上,就选些严嵩关乎善政的奏议,以让世人了解其据首辅之位,辅佐皇上,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严嵩听了我的一番陈词,直直地看着我,目光中分明有几多嘉许甚至还有几分感激。眼下,《嘉靖疏议》编选、刻刊之事已全部告竣了。郎官以上的官员,都收到了还存留着墨香的赠书。一时间,《嘉靖疏议》的刻刊,竟成了京师官场的一件盛事。当然,没有人知道其始作俑者是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只知道是舆论强烈要求,科道连连上疏,严阁老被逼无奈,不得不刻刊此书以飨群僚。
“学生实不敢掠人之美。倘说参议,学生之同乡李幼滋实有功焉。”我谦逊地说。其实李幼滋对刻刊《嘉靖疏议》之事一无所知。
我是想借机把他人请托之事作一了结。人在官场,难免有人请托,而自己又职权不及,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目下,有两件事请托到我。一则是山东登州都指挥佥事戚继光,我做庶吉士时即与他一见如故,此后书信往来不断,他访得新任山东巡抚提督浙江军务的王忬乃我的同年王世贞之父,遂托我转圜,请调抗倭前线效命,我已和王世贞疏通,不日即可到任。其次就是同乡兼好友李幼滋了。
他和耿定向一起,连考三科才中进士。春闱得中,年纪已长,入翰林院无望,唯有等待分发。李幼滋、耿定向志在留京,不愿到地方任职,就不得不走门子、思钻谋,上下转圜。耿定向老成持重,对理学颇有钻研,已刻刊了一部著作,我在徐阶面前举荐,经徐阶施以援手,他被分发到国子监任教授,唯李幼滋尚无着落,时不时要到我家里来,商议争取留在京城的办法。
本来,合计着是想请徐阶转圜的,但经过对徐阶处境进行分析以后,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天李幼滋又找我,商议分发之事,他忧心忡忡地说:“传闻徐阁老整天如履薄冰,诚惶诚恐,对那位老人家谦抑恭敬。据说那位老人家举荐袁炜、李春芳、鄢懋卿、雷礼等人,事先征询徐阁老意见,徐阁老连说‘元翁所选得人’;内阁和科道会揖时,那位老人家向科道通报圣上特旨用人之事,科道大哗,要上疏谏诤,徐阁老好言相劝,抚慰有加,让那位老人家甚感满意。许久以来,徐阁老说话做事无不谨小慎微,除了当直,就是闭门谢客。我分发之事请他转圜,恐颇有不便。”议来议去,最后的结论是,只有请严世蕃施以援手。可是,李幼滋拿不出相应的上兑,直接找严世蕃是不可能了。我答应为李幼滋帮忙。刻下,我提及李幼滋,不仅是要给朋友一个帮衬,更重要的是,我要检验一下严嵩对我的请求作何回应。
“这李幼滋者……?”严嵩眼珠快速转动,似在搜索记忆。
我忙说:“李幼滋字义河,学生之同乡,春闱折桂,候补至今。那天在寒舍,说到魏学曾弹劾元翁之事,我辈皆忿忿不平。元翁如此有功于社稷,魏学曾之流却妄言元翁一意维持,专心迎合,实实令人愤恨。如何为我元翁鸣此不平?思来想去,便议起刻刊密札之事。”
“难得叔大有此良苦用心。”严嵩欣喜地说,“还有贵同乡叫?”
“哦,李幼滋,候补中。”我特意在“候补”一词处加重了语气。
“还在候补?”严嵩不屑地挥了挥手,“让他找世蕃,帮他过班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