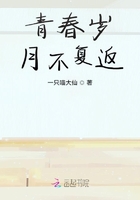深秋的傍晚,红偌朱砂的艳阳,消失在了西边的水湖面上。一下子陷入黑暗的城市,犹如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黑纱。
啪!路灯亮起,撕破黑纱。给晚归的人们带去光明。
陈一凡气喘吁吁地扶着路边的树干稍作休息,他有一点后悔刚刚为什么不叫一辆出租车赶回医院。
但他看了看拥堵的车流,就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
稍作休息的他调整好呼吸,望了望还有一段距离的医院,强打起精神向那边小跑而去。
终于跑到医院的陈一凡,靠在大门前不停的喘着气,原本应该灯火通明的保安室此刻却黑灯瞎火。
陈一凡望了望住院部的楼层,六层高的大楼却依稀亮着几盏灯火,犹如黑夜中的繁星。
不安的情绪越发激烈,陈一凡往朱大妹的住院部跑去。
一踏入漆黑的楼梯,陈一凡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应该有医务人员和病人的楼层,此刻却静的可怕。
他快步往楼上跑去,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了凌乱的脚步声。
陈一凡停下脚步,侧耳静静的倾听着声音的来源,脚步是从朱大妹所住的四楼传来。
陈一凡尽量放轻脚步,往朱大妹所住的病房慢慢挪去,靠着楼梯口的拐角探头往外看去。
一个黑色的身影,站在朱大妹房间的门口。手握着门把手,弓着腰。仿佛蓄势待发着想冲进房间。
陈一凡望了望周围,一个灭火器映入眼帘,他捏手捏脚的拎起灭火器,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之后猛的一冲,往那个黑影扑去。
朱大妹的病房,原本黑漆漆的房间,现在灯火通明。
一个掀着后背,被护士处理着伤口的男人,疼的哎呦呦的直叫。
陈一凡看着呲牙咧嘴的徐辉,有点憋不住笑。
徐辉虽然弯着腰,但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陈一凡那一脸便秘的表情,气急败坏的说:“哎~你个臭小子,还笑得出来,要不是我反应快,我这条老命就搭在你手上了。”
陈一凡连忙管理好自己的表情,略带抱歉又委屈的说:“我也没想到是你呀,这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啊。”
给处理完伤口的护士道了谢,看着关门走远的医务人员。徐辉先是望了望沉沉睡着的朱大妹,又看了看望向窗外的陈一凡。
开口说道:“在我先赶到的时候,刚进大楼,医院一下子就断电了。我感觉肯定有蹊跷,就马上往朱大妹的病房赶。”
徐辉顿了一顿,见陈一凡还是望着窗外继续说道:“之后就在楼梯上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听到这的陈一凡不再望向,窗外转头看着徐辉不解的问:“奇怪的人?”
徐辉看着陈一凡点点头继续说道:“对,那个人戴着口罩,最关键的是天都黑了居然还戴着墨镜,我感觉不对劲就开口询问了他一下。”
“没等我问他什么,他就往楼上跑,你也知道当了这么多年警察,只要一有人跑,基本上就会条件反射一样的去追。”
“追上了吗?”
徐辉摇了摇头,紧皱眉头的说:“没有,这家伙对这里好像非常的熟悉,七拐八拐的把我给绕晕了。而且乌漆嘛黑的我一下子就跟丢了。”
陈一凡毫不惊讶徐辉没能追上那个奇怪的人,按他之前的预感,这个人肯定是冲着朱大妹来的,又故意制造了医院停电的假象,那一定是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你觉得他是冲着谁来的?”徐辉突然问出了一个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的问题。
“当然是朱大妹,难不成还能是我啊~”陈一凡不假思索的说,奇怪着徐辉这个老警员怎么还问出这么没有水准的话。
“我想也是~”徐辉淡淡的说了一句,眼神里却透露着担忧,好像有点心神不宁。
陈一凡拍了拍徐辉的肩膀让他安心,之后提议两个人轮流值守,来保证朱大妹不再遇到什么危险。
说的是两人轮流值守,但疲惫的陈一凡很快的睡去,虽然早就应该到了换班的时间,但心神不宁的徐辉看着难得能睡得这么香甜的陈一凡,不忍心叫醒他,就这样带着沉重的心事守了一夜。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宣告着这一夜的黑暗到此结束。美美睡上一觉的陈一凡不好意思的和徐辉打着招呼,责怪着他为什么不把他叫醒,叮嘱着让徐辉先去睡一会儿,就起身去买两人的早餐。
守了一夜的徐辉在边上打起了鼾,在一旁的陈一凡静静的等待着朱大妹的醒来。和之前还没睡着的徐辉交代了自己的计划,之后的成败就只能全凭天意和人心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快到了中午时分,朱大妹才缓缓清醒过来。
见朱大妹醒来的陈一凡,摇醒了都快流出哈喇子的徐辉,两人简单的准备了一下,就开始了例行询问。
说明身份和来意,徐辉拿起录音笔,陈一凡捧着记录册开始了问话。
“朱阿姨,您之前说过讨债的混混把你推倒过?能详细说一下嘛?”徐辉开始了第一个问话。
朱大妹现在的身体虽然虚弱,但还是详细的思索着讲述道:“那天我刚要出门买菜,还没来得及走,就来了一伙儿小青年,嘴里嚷嚷着叫钱二宝还钱。”
“是钱二宝借了那伙小青年的钱吗?”
听到这的陈一凡插嘴提问道。
听到这个提问的朱大妹,嘴里虽然含糊不清但还是老老实实说出了实情。
“没有。。。是钱二宝向外面借了高利贷。”
徐辉和陈一凡对望一眼继续问道:“听说钱二宝借高利贷是为了赌博,有这回事吗?”
朱大妹听到徐辉的问话连忙着急地摇头解释道:“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几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家里没钱做手术。钱二宝他东拼西凑也才借到了5万块钱,可还是差3万才够手术费。”
“之后他不知道去哪儿里的赌场,用那5万块钱,赢了七。。八万,用赌来的钱给我做完手术之后,我也劝他不要再去赌博,这次是老天保佑,下次就不一定能赢钱了。”
“他嘴上答应,但尝到甜头的他还是进了那个赌场,然后就输得血本无归,还从那边借了好多的高利贷。”
“知道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后,我就偷偷的把他父亲留下来的老房子卖掉,打给了远在美国的大宝让他帮忙先保存着。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娶媳妇儿的钱,不能再让他给输掉了”
听到这的陈一凡突然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
朱大妹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他染上了赌瘾,已经听不进我这个当妈的话了。”
叹了一口气的朱大妹,望着天花板仿佛又回忆起了往事。
“其实他以前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有一次在路上看到有人撞倒了老人就跑了,也不怕惹麻烦的去扶老人起来,虽然之后用监控还了他清白,不过他也没抱怨人家,还说人家这样想也是正常,还有一次。。。。”
朱大妹回忆着钱二宝年轻时候的善举,如数家珍。照理说这些与案件无关紧要的话,应该是不需要记录的,但陈一凡和徐辉却格外的认真。
都说落红不是无情物,但这世人又怎知,树木不曾为落红潸然泪下呢?
寒风中凋落的树叶,仿佛树木脸上流下的泪珠,飘飘荡荡、洋洋洒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