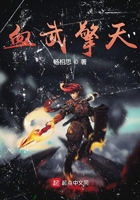尽管我这样安慰离夏,可是一直到掌灯,我仍没有想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好办法。牢房里昏暗的灯光燃起好长时间后,送饭的狱卒终于磨磨蹭蹭拎着一篮子饭菜开始逐个牢房发放。我见终于有人来,急切地冲至门边,嚷起来:“来人啊——我要见皇上!来人啊——”尖利的声音在空荡的殿宇里格外刺耳,但那狱卒似乎充耳不闻,自顾自地做着事情。
当他终于挪到我的门前,我一把揪住他的衣服:“我说我要见皇上,你听到了没有?!”
那狱卒只用眼角扫了我一眼,仍旧慢吞吞地说:“娘娘,既然来到这儿,我劝您还是消停会儿吧。”
他的态度一下子激怒了我,我死力拉他往牢门上一撞,怒吼道:“你看清楚了,我是贤妃,在皇帝没有废黜我之前,你胆敢顶撞我?”
狱卒四平八稳地慢慢把衣服从我指缝中揪出来,拿出属于我的一碗饭放在门边,嘴里念念有词:“我说娘娘,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您冲我发什么火呀?甭说贤妃了,我们这儿上至皇太后、皇后,下至皇子、公主不知关了多少,个个都说要见皇上,都要我通秉,可是皇上认识我是谁啊?!我还想见皇上呢?!”嘴里嘟囔着,他的脚步已移向了下一个牢房。
我颓然滑坐在地,茫然地四下看去。整个牢房关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几个宫女和太监,我大概是这里“级别”最高的犯人了。但那狱卒说的何尝不是事实?宫廷斗争历来都是腥风血雨、残酷无情,权力的交替更是瞬息万变。今天还是皇帝,明天也许就成了阶下囚,甚至连性命都没有了,这些我看得还少吗?赵光义弑兄夺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其实我在这里呆多久都无所谓,但是我不能不管离夏。无论如何,她都是因为我才受到了牵连。
在我绞尽脑汁仍毫无进展时,隔壁又传来了离夏低低的啜泣声。听得出来,她是在压抑着自己的哭声,怕我听了难受——刚才那一幕,她又怎么会看不见?我想过去劝她,却无论如何也迈不动步子。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能力救她,而是时间太仓促。明天她就要行刑了,可是现在赵光义正在气头上,他怎么会来见我呢?走出这个监牢,也许我是可以呼风唤雨的贤妃,可是一旦身披枷锁,即使皇帝并没有废黜我,我也什么都不是了。
我正在发愁,狱门外一阵窸窣声响,一个宫女闪进来,急急忙忙向里面奔。我定睛一看,居然是庆奴。
她看见我,还未开口,泪就“刷”地流下来。
我忙攥住她的手:“庆奴,我没事儿,不哭啊。”
庆奴点了点头,半晌,才止住悲声:“小姐,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见皇上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摇了摇头:“宫里的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可是,”庆奴咬着下唇,“小姐,我要怎么帮您呢?”
我笑了笑:“不用了,皇帝一时间生我的气,把我关进来,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对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花重金买通了狱卒,他们才放我进来跟您说几句话。”
钱!我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庆奴!”我猛然攥紧她的手,“我的确有一件事要你帮我,而且你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庆奴见我神色严肃,忙不迭地点头。
我指了指隔壁的离夏,说:“她被宋皇后陷害,明天要行刑砍去双手,你得想办法救她。”
“这……”庆奴面露难色,“小姐,我要怎么救她呢?”
“钱!庆奴,皇帝这两年的赏赐,都是你保管的,只要能救她,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宋皇后已然失了势,行刑的差役没必要为一个失势的皇后和钱过不去,所以我想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小姐,”庆奴依旧不解,“您为什么要救她呢?”
我笑着摇了摇头:“庆奴,‘千金散尽还复来’,可是人的手如果被砍,就永远没有了。”
“嗯!”庆奴使劲点了点头,“小姐,您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