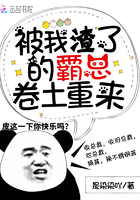江时婉被人看的烦,就不是那么沉的住气了,本来跟闫文林谈这样的话题,就难得有心平气和的时候,刚才说了那些话,闫文林没什么反应,却将她自己的说得满心浮躁。
她就像是被车辆和冷风刮起在空中浮动的尘埃,慢慢无所依,无奈又想跳脚。
顷刻,闫文林陈默了半晌之后,江时婉以为他可能又没什么好脸色,谁知道他却淡然的点了点头,“你的意见我会采纳,但是我这二三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一时让我温声细语也不可能。”
闫文林这样说,一改他平日里的凌厉严肃的风格,让江时婉彻底语塞,张了张嘴却接不下去话。
以至于江时婉看向他时,欲言又止的模样,看起来呆呆的。
见他不说话,闫文林又说:“所以你觉得我们是性格不合?”
浓黑深邃的眉眼,如同被墨汁沾染,像极了被细细勾勒出来的水墨画,清隽有锐利,深沉的眼底藏着一贯的沉稳与睿智,他刚才也是这样静静的听她说,水波不兴,一副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的样子。
江时婉没由来的心闷,斩钉截铁的接话,“不止!不论是性格还是经济状况,亦或是三观!”
她自己都说不下去了,不合就是不合,好用列什么一二三四五,又不是答政治主观题。
闫文林手随意的搭在腰上,嗤笑出声儿:“连三观都带上了,还有什么?你说。”
“你在笑什么?我说错了?”江时婉正儿八经的看向他,“三观不一致,没有什么可交流的话题,日复一日的冷淡,最终夫妻生活不协调,从而走向离婚的不归路,这都是现代社会很多夫妻离婚的主要原因。”
江时婉说的条理清晰,甚至还动用了“最终”,“从而”等连接词来据理力争。
闫文林却严肃的说:“你说错了,就算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你我的夫妻生活还是协调的,每次交换的欢的不都是你吗?你好意思枉顾我的努力,无视你的欢愉吗?”
江时婉听他波澜不惊的说起房事,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红:“流氓,你以为婚姻有性就足以?那等到年纪大了呢?如果我肌肤松弛,你对我的也没什么兴趣了,两个人就靠着日积月累起来的那么点亲情,沉默无言度过余生吗?你倒是还有更多年轻漂亮的女人供你随意挑选,而我呢?一个半老徐娘,成日守着孩子房子过是不是?这不是我对婚姻的期望,也不是我对余生的想象。”
江时婉胡乱说一通,自己都知道逻辑不通。未来有那么多的变故,谁知道事情会是怎样的走向?她却做出了最消极悲观的假设。
闫文林探究的看着她的神色说:“你小题大做了,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难道你觉得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才有激情?你既然当初提出结婚,这些问题你早就该想过,这会让才来纠结两个人是否合拍或对等,为时已晚,也无理取闹。”
江时婉听的来气,却无法反驳,睁大眼睛瞪视着他许久之后,憋出一句:“你才是无理取闹。”
闫文林还以为她要说什么长篇大论,听到这几个字之后,愣了一愣。
江时婉这话一出口,就觉得谈话已经朝着男女吵架的既定方向发展了。
而闫文林的话无疑也是揭伤疤。
人人都知道,曾经犯过的错,就像是一个污点,江时婉总是想拼命的洗掉,但是却被一而再的提起,告诉她是既成事实,铁板钉钉,怎么辩解洗白都是没用的。
江时婉把心一横,便又说:“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结了婚之后就是奔着离婚去的,其他的杂碎有什么好值得考虑的?”
闫文林脸上终于还是没了柔和,渐渐敛了笑,沉了脸。
他顶着江时婉良久,操着冷冷的嗓音,慢条斯理的说:“你也真是挺有意思的,口口声声说我态度不好,你态度什么时候好过了?不是阴阳怪气就是假情假意!你当初说结婚就结婚,你以为我砸出几个亿将你娶回来就是为了跟你离婚的?你这么那么会算呢?天下的便宜都让你捡了算了。”
夜色渐渐浓重,气温也越来越低,小区外围的绿化带里肿着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木,风一吹过,树上挂着的残叶沙沙作响,枝干抖动的厉害,抖颤着发出不安的声音。
风吹在身上,背脊都发凉,江时婉还是挺直着肩膀站在了夜色下,瘦消的身子此刻像是一只标枪,沐浴在朦胧的路灯之下,显得可怜。
闫文林的话已经彻底将江时婉的底气击的粉碎,他说的对,是她异想天开了。
江时婉的心,从刚刚不安的躁动,变成了无言的沉重。
就像是一颗落入海面的石子,不停的往下沉,一直沉到暗无天日的海底,海水四面八方的压过来,让呼吸都成了一种负重运动。
她心头堵得难受,倒不是因为自己被迫面对她不想面对现实,而是闫文林说出这些话,将她批的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就会投机取巧的女人。
更难过的是,这话一点都没说错,因为从始至终她都觉得自己是可耻的。
江时婉笑了笑,有些难看,突然说:“那你想要我怎么做呢?”她征求他的意见,声音不稳,有些飘忽。
闫文林幽然上前,轻轻捏着她的下巴,“给过你机会说出你的不满,结果你说的都是些废话。”闫文林啄了下她绯色的唇,眼神宛若深潭,语调轻柔,却带着一股子狠劲儿,“有什么不满都给我忍着,乖点,不要动不动就无理取闹。”
江时婉心神种种的一沉,这应该就叫做还债了。
就算他不爱自己又怎么样?就算她过的心里再不舒服又如何?她得了他那么多好处,有再多的不满,忍下来也不为过。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尽管她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