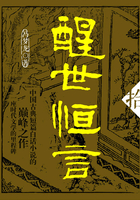我在回伦敦的途中又想了很多和思特里克兰德有关的事。我试着梳理了一下要告诉他妻子的事。这件事情我办得并不好,我可以想象,她不会满意这个结果,说实话,我自己也不满意。对于我来说,思特里克兰德像一团迷雾一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问他一开始学绘画的动机时,他也没有给我解释明白,可能他压根就不想跟我说。我完全是一头雾水。我想对这件事进行这样的解释:一种模糊的反叛意识逐渐在他迟钝的心灵中产生。可是,以上解释却被一件板上钉钉的事实给打破了:他从来没有厌烦过过去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假如他只是对无聊的生活感到厌烦,而下定决心要画画,以从无聊的牢笼中逃脱出来的话,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一个寻常人。最后,可能我还有些浪漫的想法,我想出了一个解释,虽然这个解释不太站得住脚,可是却是仅有的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那就是,某种创作的欲望可能深埋于他的灵魂中,虽然他的生活环境把这种欲望掩藏起来了,可是这种欲望却一直在无限放大,就像在有机组织中,肿瘤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控制住了他,让他没的选择,只有赶紧采取行动。杜鹃在别的鸟巢里下了蛋,当雏鸟被孵出来以后,就会赶走它的异母兄弟们,最后还要毁掉保护它的巢窝。
可是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反应不太灵敏的证券经纪人竟然会被这种创作欲望牢牢攥住,他也许会因此走向毁灭,拖累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可是相比上帝的玄旨妙义有时也会抓住人们,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些人既有身份,也有地位,可是上帝却非常小心地猛追着他们不放,直到最后完全征服他们,这时他们就要把世俗的快乐、女人的爱情舍弃掉,心甘情愿地去寺院里过清冷的生活。皈依出现的形式可以是不一样的,实现的方式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是通过一刹那的改变,就像石块在气急了的河流的作用下,一下子变成齑粉。有一些人则是通过漫长的岁月,就像水滴一样,持续不断地滴,最终滴穿石块。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不仅有盲信者的直接,也有使徒的痴迷。
可是站在实际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这种让他痴迷的热情能否结出累累硕果。当我问他在伦敦学画时的同学是如何评价他的绘画时,他笑着说:
“他们觉得我纯粹是出于好玩。”
“你到这以后,有去哪个绘画学校吗?”
“有。今天早晨,那个笨蛋还来过我住的地方——我是说那个老师,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只是挑了一下眉毛,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思特里克兰德似乎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还开心地笑了起来。别人的意见是不会影响到他的。
我在接触他时,之所以感到难堪就是因为这一点。有人也说他根本不会把别人的看法放在心上,可是这基本上是掩耳盗铃。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因为相信别人不会看穿他奇特的想法,所以才会一意孤行。最严重的也是因为得到了几个知己的支持,所以才敢置大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假如一个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其实只是站在他这一个阶层人的对立面,那么他就很容易在世人面前站在传统的对立面。他反倒会很得意。他不仅把自己的勇气彰显出来,还不用冒什么风险。可是我总觉得如果什么事都要得到别人的许可,可能是文明人类不可自拔的一种天性。一个敢于推陈出新的女人如果违背了礼规,引来别人的非议,她会快速去寻找体面的庇护。我是从来不相信那些声称他们对别人的意见毫不在意的人的。这只是一种无知的装腔作势而已。他们是想说:他们深信自己的小瑕疵不会被人发现,所以就更不用担心别人会因为这些微小的不足之处而对他们加以苛责了。
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对别人的看法完全不在意的人,所以传统礼教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如同一个全身涂满油的角力者,你只有任由他从你手中消失。这就让他拥有了一种自由,你除了气急败坏,别无他法。我记得我还对他说过:
“你听我说,假如所有人都和你一个样,那这个地球就难以正常运行了。”
“你说这样的话简直太傻。我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很满足于他们所做的普通事。”
我很想讽刺他。
“你肯定不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
“我从来没有听过,可是这简直是胡扯。”
“这是康德说的,你不知道?”
“管他是谁说的,反正是胡扯。”
对于这样一个人,你根本没办法诉诸他的良心。这就如同不在镜子的帮助下,你却想看到自己的反影一样。良心在我这里是守卫一个人心灵的卫士,必须依靠它的监督,社会为了存续所制定出的一套礼规才有用。良心在我们的心头放哨,在那里护卫,监督我们要遵纪守法。它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密探。由于人们对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太过于看重,对于舆论对他的指责太过于担心,结果引狼入室。于是,它就在那里行使监护的职责,守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但凡产生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会受到它的严厉批评。它强迫所有人都更加注重社会利益,而把个人利益放在其后,它是将个人禁锢在整体中的一条牢不可破的绳索。人们劝说自己相信个人利益低于某种利益,心甘情愿为这种利益服务,最后被这个主人奴役。他把他高高举起,最后,他也自豪于自己敏感的良心,就像宫廷里的弄臣对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大加称赞一样。对于那些想逃离出良心掌控的人来说,到了这个程度,他就会觉得如何斥责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员,他很清楚他没有力量背叛自己。当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真的漠视他的行为会带来的责骂时,我就如同看到一个怪物一样,被吓得直往后退。
那天晚上,当我和他说再见时,他最后告诉我:
“跟阿美说,不要到这儿来找我。我马上就要搬走了,她找不到我的。”
“我想说,她摆脱你也许是件好事。”我说。
“亲爱的朋友,我就希望你能帮助她意识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女人都没长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