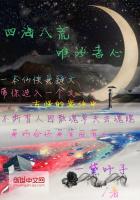楚浩因为内陆的生意和老派商人不断冲突,脱不开身。淳嘉诺熙绑在辽东,幽州便成了两人相聚的地方。
让淳嘉诺熙没有想到的是,二舅舅李前瞻真的给楚浩搞到了三艘大船,正忙里忙外筹备,只等开航试运。
船长有三十丈,宽五丈,这么大的船根本没有办法进运河:
首先太过扎眼,楚浩走过南北水路,商船没有这么大的,如果关卡盘问,无法解释。
其次,大船吃水也深、船体太、宽,运河里走不起来。
第三,大船靠划桨的话,需要大量人力,这种海船,船玄高,浆片大,一个浆需要三个人划,须花时间训练专门的划桨手,才能启动。挂帆,在风平浪静的运河,没有用武之地。
楚浩索性给李前瞻追加了三十万钱,让他负责三条船的海上运营,并派跟班杨信和杨力协助。
淳嘉诺熙不能理解,问楚浩:“这么长时间,好容易小舅舅给你弄到三条船,见好就收吧,怎么又给他钱?别人家如果有两个儿子那是后继有人,儿子一定陪着父亲征战,你看看外公,跟随外公的是外婆你知道吗?两个儿子都留在家里享清福,这样不仁不孝的儿子你见过吗?大舅舅还好些,守在家里也算安分,可是二舅舅,整天在外面瞎折腾,没有一点正形,给钱就是害他?”
楚浩搂过淳嘉诺熙耐心的解释道:“淳儿,你先别着急,我问问你,你知道买一条三丈长的内河船要多少银子吗?”
淳嘉诺熙看着楚浩认真的样子,想了想摇摇头。
“要五百两银子。一丈长的独木舟不值什么钱,但是三丈长的载货船就值成百倍的银子,为什么?那是因为很少有人能造大船,那需要很高的技术和材料。一条三丈长的内河船还要五百两银子,那一条几十丈长的大海船又要多少钱呢?”
“难不成要一万两?”淳嘉诺熙嘟嘴道。
“多少钱都买不到,因为只有朝廷和官府才能造出这么大的船,并且都是用来打仗用的,伐百济、高句丽时才造了十多艘,二舅舅居然弄到了三条海船!”
“那你花了多少银子?”
“两千!当时就给了二舅舅两千两银子啊。”
“怎么可能?”
“开始我也不相信,昨天我亲自去三会海口(天津)看了,全是几十丈的大海船!”
“真的?”
“这三艘船是在灭高句丽之前,大唐支援给新罗的,新罗用来投机,被大唐收缴,战后当地官员中饱私囊,低价卖出来的。”
“二舅舅倒是能办成这种事,好人他不认识几个,仗着外公的威名,贪官污吏认识不少。”
“内河河道我刚刚熟悉,但是对海路我一星点儿都不懂。自古以来,海上都是盗贼的天下,到我朝才略有控制,不过从高句丽之战以后,国力耗费,西线吃紧,官府对海上听之任之。若想开展海上商路,须要一个有巨大热忱又懂行的人,这个人选非二舅舅莫属,所以我又给二舅舅些周转,把梁益从营州调过来帮忙。二舅舅投机取巧,梁益有勇有谋,不愁在海上行不通。”
“二舅舅那是碰巧捡了便宜给你买了两艘船,你被别奢望他能担责任、做长久生意。”
“做海上贸易本来就是二舅舅为我出的主意,他分析的清楚透彻,讲起来眼睛放光,说明他一定对此寄予过期望、深思熟虑过,只是手上没有钱。大舅舅世袭外公的爵位,在家里安分守己,日后也可以高官厚禄;二舅舅也想有些作为,只是不是外公、外婆所期望的文生武将,便被打压而已。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给他一个机会有什么不好呢?”
淳嘉诺熙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她自小就听见外公和外婆训斥舅舅,尤其是二舅舅,她眼里的二舅舅就是外公外婆眼里的二舅舅,不想楚浩却能从一个旁观者甚至从高度看到问题,自己在这方面还真要多多跟他学习。
从突地稽归顺隋朝,为了能够站稳脚跟,舍生替隋朝四处征战,到外公李谨行为赢得本族在大唐的一席之地,屡屡冒死建立战功,再到乞乞仲象依附高句丽到被大唐强迫迁入营洲。淳嘉诺熙从小看到他们的无奈与挣扎,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只能臣服强权,随波逐流,任劳任怨,被当做肉墙骨靶。
她下定决心要让族人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如今嫁给楚浩,东西南北四处巡游,让她的视界更加开阔,更加坚定了原来的认识:把世界引进靺鞨,让靺鞨走向世界。
内地官路走多了,她也看到经济实力的重要性,官府士绅们瞧不起商人却也离不开商人,有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意味着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她尽一切可能帮助靺鞨的商贾做生意,有时甚至不惜抬出她公主的身份。
***
自秦汉以来,长安以西的商路逐渐成熟、完善,波斯人、粟特人、大食人、高昌人、于阗人等等都精于此道,而且西部高原、戈壁、沙漠、大山……重重阻隔,只能靠骆驼运输,所以楚浩在长安准备好货物,就地联系胡商做生意,极少派商队出行。
而洛阳以东,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百姓大多务农,商人割据一方,长途运输、贸易的人较少。楚浩喜欢车马、舟船运输,他开辟新思路、开发新产品,只与老派商人贸易,不跟他们重叠,以免造成冲突。
随着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大,即便东部商人的信息再不灵通,他的商队从两京到辽东来来回回从人家的地盘上过,当地的商人们也不能不警觉。但凡成了气候的商人,背后一定有政治支持,理顺、摘开这些关系,保障走通东西,着实要费些周折。
楚浩对第一次到涿州城看到的白瓷,一直耿耿于怀,找到当地烧白瓷的地方,问及技术的事情,每一个窑口的人都非常警惕,不愿意多说一句。他想要订制高质量的货物,窑口的工匠有自己的坚持,或者说温度不够,或者说挂浆有限制,具体限制在哪儿,楚浩搞不清楚。
有关温度,楚浩问了楚文和楚瀚,楚瀚说他研究过叔叔楚文烧陶器的窑,温度可以加上去,具体里面怎么摆放泥胎,需要叔叔指导。偏巧伤兵里面有个邢州人,说他在老家烧过瓷器。楚浩立刻把叔叔、楚瀚和这个叫彭行山的人集中起来,研究白瓷的烧造。
彭行山说他只熟悉老家的瓷土,在辽东看了几个地方,试过之后效果都不好。楚浩只好把他带回他的老家---邢州北三十里济渠附近,待彭行山选中一块地,买下来,建瓷窑,招收工人。楚文和楚瀚负责窑炉,彭行山负责找土、制胎,挂浆、沾釉面,楚博和楚旷负责设计造型。
这样一来二去花了不少时间,瓷窑终于烧出来第一拨瓷器,残次品很多,却有几件好的,比之涿州那些施白粉的货好上百倍,楚浩要求的光洁、满釉基本可以达到。
窑口再经过不断调整摆放位置、优化土质、精细加工、制胎逐步规整,出窑的瓷器也越来越理想。
楚瀚从烧瓷窑中学到了很多,研究冶炼技术,等瓷窑这边炉子形制确定,他便回山后郡继续研究琉璃去了。
瓷窑产销走上正轨,楚浩留下楚文帮他开设造纸坊,造纸坊选在渭水东岸。
楚文在山后郡反复研究造纸,一直失败就在于他造的纸吸水太强,墨一上去就掺开,而且太过柔软,不耐磨。后来加入捣碎的竹子和一种特殊草秆,情况才得到改善,而这种草秆只有山后郡有,到渭水,他尝试用麦秸秆代替。可麦秸秆容易发黄,晒出的纸张没有南方的洁白干净。
楚浩拿的纸样被淳嘉诺熙看见,她像是见到宝贝,说这种纸作如厕用的草纸再适合不过了,尤其是女孩用的月信纸,非常合适。
楚浩哭笑不得,只好先按草纸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开始并没有人问津;后来他想这类纸不能放在文房用品里与其他纸张一起卖,应该成捆放在小摊位上,可小摊位上卖不出好价钱;楚浩又想了一个办法:把纸裁剪整齐,用网布包起来,系上彩色的丝线,放在丝绸坊卖,这次销量非常好,价格也上去了。
楚浩又把这种销售思路用到白瓷上,极致讲究精细、高规格,在长安和洛阳的市场开一间考究的店铺,专门卖这些洁白如雪的瓷器。每个瓷器外面都套一个棉布袋,布袋的口边用彩色丝线结扎,印上口贝力的印章。店员都经过专门训练,怎么拿瓷器、怎么欣赏、怎么递给客人、怎么包装,都一一规定清楚。
不久瓷器和纸张在两京上层人士中流传开来。
这两项生产的开展,投入很大成本,一开始都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
车船从辽东运来木材、皮毛和高档山货到洛阳和长安;从洛阳和长安载上一些胡商的货物,再到板渚运江南来的茶叶、丝绸回辽东。
可惜辽东凋敝,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当地没有多少人可以消费的起,只靠几个当官的和望族不行。楚浩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当地百姓手里有钱,他才能从百姓手里赚钱,为此他不停地计划。
淳嘉诺熙瞒着楚浩在靺鞨故地安置逃亡的高句丽难民,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她无力应付,只能找楚浩接济。
辽东都护府都朝不保夕,楚浩不可能把他们全部交给辽东官府处置,于是他有了新的想法:在营洲和高句丽北部边境大量购置荒废的土地,种植稻米和小麦。
辽东膏腴之地,产量丰足,赶上河北、河南、关西旱涝,他不光给唐军供了粮食,去年秋天便把之前的投入赚了回来。
只是粮食贸易不得不跟老派商人打一场遭遇战,比谁有魄力、价格低、运货快,老派商人自然难以抵挡。
楚浩赚到钱,各个衙门走一圈,好些事儿就摆平了,让他有机会把长安、洛阳、永济渠一直连到辽东的商业路线再次巩固